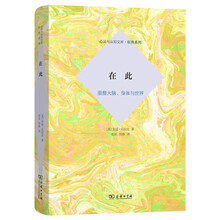不过,中央统制经济优越论目前受到了怀疑。我们的经验使我们对今天这一形式的统制经济深抱怀疑。数十年以来,一种命令经济的统制总是越来越严密,使得我们越来越深刻地看清这一经济形式的经济和社会危险,几乎已经不可能根据那种尚未落到实处的理想模式来评价经济统制。实际上只有到现在我们才真正有可能对各种经济秩序进行实事求是的评价,并用理由充分的实证知识取代流行情绪和偏见。即使承认中央计划经济的某些经济缺陷的意愿在增进,经济统制的社会优越论假设也还能作为一种几乎不容攻击的、不需进一步提出理由的信念而立足。这仿佛是最后的防御工事,在其后头,即便是一个分崩离析的强制经济(zwallgswlirtscht)也能维持这样一个权利要求,即要求把自身单独作为在一个社会思想时代惟一可能的生活方式。这一把中央统制经济与社会秩序等同的做法需要得到一种彻底的审查。我们这个时代也看到我们正好在这里面临着这样一项任务:对传统上沿袭下来的概念做出一番重新梳理和评价(1Jmwerung),并且承认我们这个时代的政治和经济生活的许多形式已经过时。受时间限制的概念和应当只按照其合乎目的的性能(Zweckdienlichkeit)来评价的经济政策工具只是过于容易成为对于它们来说不是应得(allell nicht zukommenden)的道德评价(sittliche Beweaung)的对象。如此,人们今天即使在基督教派(Konfessionen)当中也倾向于把一种集体主义的社会主义的诸种形式等同于社会美德(sittlichkeit)。不过似乎有必要的是,应使道德价值和终极的社会要求这两者深层的世俗优越性(welttlberlregenheit)摆脱时代情绪的这类缠绕。恰恰是那些把我们的经济和社会生活的道德化(Ver—sittlichung)感受为最令人关切的社会思想问题的人,会把在哪一工具性的世俗秩序里可以最好地实现一大堆最为不同的价值目标(它们应当是社会所意愿实现的)这一问题感受为某种只有经客观检验才能做出决断的东西。下文应当在此意义上尝试讨论这样一个问题:如何从社会立场出发分析阐明各种经济秩序事实的结果和未来可能的结果?<br> 不容置疑,过去几个年代最大部分的、有效的社会追求的趋势是朝着中央统制经济方向发展。中央统制经济概念恰恰可以通过把经济引离自由的市场组织形式而得到界定。社会国家的力量和最为形形色色的社会运动及社会主义运动的力量在于,某些民族力量在一旁帮助一种反市场经济的统制原则获得突破。出现了一种几乎不能把握的法律上的和事实上的市场管制融合体,其意图也许非常不同,但其特征总体上在于与市场组织形式脱钩。自由市场经济似乎是所有社会弊端的渊薮而且最终受到时代的审判。所有朝着绝对管制方向挺进的时代都同时受到社会因素的鼓动。如此,价格、工资、利息、租金管制、配额的配给、关税、投资调节、货币操纵、对外贸的操纵,直至各经济分支的完全社会化(Sozialisierung),与那些社会目标各自结合在一起,以至于这种结合毫无漏洞可觅。把社会秩序和经济统制等同就是其结果。虽然并非缺乏提出警告的声音,这些声吾警告在这一道路上存在过度紧张问题并建议社会政治家注意这些经济考虑。不过对这些警告的效果相对于以下无数次尝试来说是完全乏力的,这些尝试就是:通过临时草率创立的工资理论把工资形成解释为一种纯粹社会权力斗争事务,并以此了结那些提出警告的经济理论。即使经济困难日增,社会国家步步进逼并与之缠绕在一起,也不<br> 能发人自省。最后出现的现象是市场经济秩序总是进一步被拆除,而且人们坚信社会政策成功恰恰可以以这一拆除的极端性来衡量。<br> 当代社会力量在这一单方面的发展中只能说是过分丧失了其赖以立足的现实土壤,并且它们对在一个市场经济秩序架构下存在哪些可用于实现社会思想的建设性的可能性缺乏洞见。人们在没有进一步三思一度作出的有利于统制的选择,社会政策文献质量绝大部分下降到现有经济研究水平所要求的水准之下,人们也丧失了——这也不足为奇——与过去真正的社会思想传统的联系。在大多数教科书里可以找到的社会史画面把近代社会发展的开端定得过晚。国家社会立法开始于普鲁士1839年的条例(Rcgulativ),而且自19世纪中期开始的社会革命运动为较新的干预主义社会政策划定了时代界限,越过这一时间界线,人们只能寻觅到几处有关法国早期社会主义和古代及中世纪社会史的回忆。人们在此忽视的东西是耐人寻味的。人们至少忽视了历时一个半世纪的那种早期自由主义社会思想史及其追求史,这些思想和追求是在自由市场经济框架内发展起来的。这一与市场一致的社会政策所凭依的是那些与自由主义信念相联系的、并通过其建设性的建议寻求依循这一生活秩序的轨道发展的社会思想。<br> 为了正确评价自由市场经济时代,必要的是不仅要看到那些毋庸讳言与这一秩序相联系的社会损害,而且也要高度评价18世纪和19世纪初叶那个时代为所有阶层的人们的解放和成熟所做出的那种贡献。以下做法有失偏颇:只把阶级差别和对资产阶级阶层的依附的产生看做那个时期的社会功能,而不高度评价那种伟大的社会成就,它是在自由社会秩序架构下为了把个人从受奴役和强制状态中解放出来而在当时立下的。我在其他场合详细阐述了这一被遗忘的社会史篇章之思想源泉。在此我只回顾大量社会改进,它们源自开明的专制主义,尤其是源自有着多方面动力作用的18世纪禁欲主义教派。只是很难为这些追求寻找一个共同的称呼。它们发生在恰好存在艰难困境的地方。除了宗教和政治宽容思想之外,最早的要数改革在劳教所和监狱里的刑罚以及推行精神病院的人道化。此外,从社会角度对劳动教养的改造、把只消费不干活的穷人变成劳动者的转训以及改造整个教育体制早已从夸美纽斯(Camenius)开始。对妇女和儿童工作的保护早已产生自同样的环境,并且在英国首先得到立法。对于其后的时代,重要的是18世纪末从自由主义原则发展而来的储蓄银行这种自助机构的设立以及从教派环境中产生的合作社互助的成型,这种合作社互助在19世纪以不同的生产、消费和信用合作社形式获得了其现实意义。把农民从世袭仆从地位解放的阶段以及在19世纪初向着自由迁徙和自由从业过渡的阶段,必须评价为社会改革阶段。那些使得技术发展服务于经济上弱小和处于不利地位者的方法和思路开始于18世纪并且在19世纪通过围绕小型发动机的技术努力和信贷改革得到存续。通过改革后的教派所强制推行的奴隶解放同样也属于这些措施领域。与维希尔(Wichem)、弗里德纳(Fliedner)和凯特勒(Ketteler)这些名字一起,德国新教的慈善组织“内部使命”(Innere Mission)和德国天主教的慈善组织“博爱”(Caritas)的设立构成了其尾声。<br> 这一阶段的实际启迪是不可估量的。对于我们这一时代的社会思维来说,即使今天在何等程度上依赖于那一最初时期的好处,几乎还是不明的。也许人们可以从历史理论角度随心所欲地定义那一最初时期,但无论如何,这涉及到在所谓的市民社会(burgerliche Gesellschaft)的形成出现突破的同时发生着一场气势磅礴的社会解放运动。以工业社会对19世纪盛期提出的任务来衡量,这一社会秩序肯定过分处于萌芽状态和过分支离破碎。不过它也甚至根本就没有得到机会来按照较高的要求重新改造自己,因为新的发展与那一社会力量传统之间出现了一个断层,该断层断送了人们那种根本性的、出于社会改进之目的而服务于自由原则和市场原则的意愿,并促成了那样一些社会运动,它们最终完全拒绝了当时公认的经济组织原则,并把社会政策引入到一条集体主义的和脱离市场经济的道路。民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最终把那种实事求是的、人道一基督教的社会改革排挤到第二线。发生这一断层的原因只能猜测。在我看来,从年轻黑格尔派以来起着领导作用的受教育阶层中以及后来也在广大民众阶层中发生的基督教一人道思想的解体导致了这场大变局。它导致了人们背弃那种共同的信念基础,这种基础使早期社会发展还能与一般社会价值保持原则一致。此后,由于受到阶级斗争和历史相对主义(Geschichtsrelativismus)的煽动,似乎不再能够通过对旧有秩序的维续,而且还只能够通过砸碎这一秩序才能实现新的社会秩序。旧的社会改革因其大量思想和实际建议的涌现而令<br> 人惊奇,而在19世纪末却出现了一个过程,那就是被我在另外一个场合描述为偶像形成过程的过程。被各种社会运动所选择的、带有诸如国有化、摒弃市场经济、市场管制、自给自足之类<br> 目标的工具性秩序被提升为社会运动的一个最终目标。它接受了世俗的、非理性的供奉,这种供奉排除了任何对所选择手段的运作能力的务实评价。在被迫从干预走向干预的强制下,出现了那种对生活的全面的集体化,这种集体化最终不再被感受为一种被人们所控制的历史过程,而是被感受为一种越人而过、不为所控的历史过程,被感受为把新时代打造成社会群众运动的一个时代这一事实所不得不造成的一种牺牲品。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