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需要被信仰,否则它形同虚设。”我们需不需要信仰,该信仰什么,又该如何去信仰?伯尔曼的话只是提出了信仰对法律进路的价值支持,然而,现实的迷津横亘在我们之前的则是对信仰本体的不知所措。《法律信仰:中国语境及其意义》这本专题文集的开篇,他的忧患意识和内心呼喊清晰而又强烈,理性而又震撼。借用伯尔曼的话来说,中国法律学人们深谙“法律只在受到信仰,并且因而并不要求强制力的时候,才是有效的;依法统治者无须处处都有依赖警察。……真正能阻止犯罪的乃是守法的传统,这种传统又植根于一种深切而又热烈的信念之中,那就是,法律不仅是世俗政策的工具,而且还是生活终极目的和意义的一部分”。然而,太过深厚的中国传统将现代法律信仰的追求限制于一个极其狭隘的生存空间,在这之上又禁锢于牢牢的精神锁链,不难想象,中国法律信仰的问题其实是如此复杂的。拉兹说:“在法治的神坛上将太多的社会目标当作祭品,这有可能使法律本身变得贫乏和空虚。”其实,中国法律信仰问题的复杂性早在尚未最终完结的近代中国社会/文化转型这一时代大背景下就已经发生了。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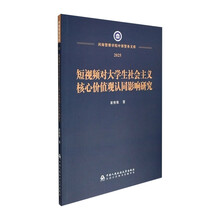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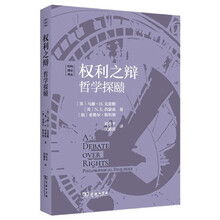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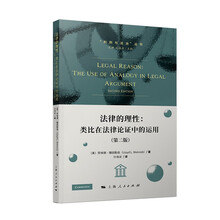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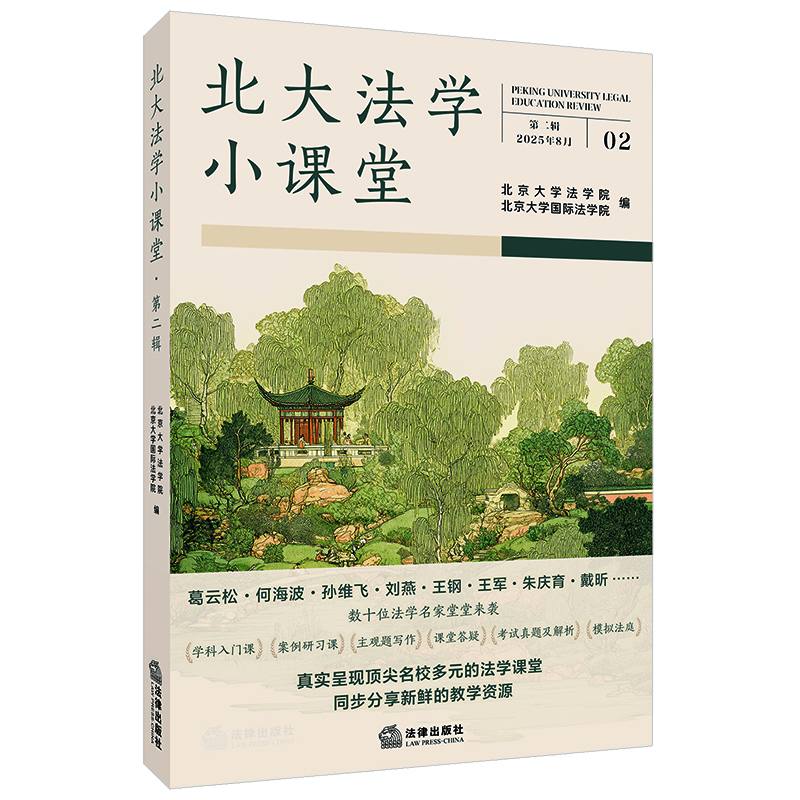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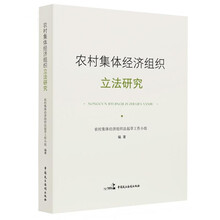
法律是一种规则体系,同时亦为一种意义体系。任何规则必涵蕴有一定的法理,载述着一定的道德关切,寄托着深切的信仰。凡此种种,一言以蔽之,曰法意,它们构成了规则的意义世界,而为法制之内在基础。
任何法制的生长与运作,必伴有相应的法意。在法律移植的情形下,甚至滥觞于相应的法意,法意因而为法制的先导。法制恒定而恒变,法意因而表现出自己的时代特征与地域色彩。反之亦然。不过,就人类迄今为止有限的历史来看,诸如公平正义、仁爱诚信、安全、自由、
平等、人权、民主与宽容等基本价值与信仰,构成所谓世道人心,关乎人的生存和尊严,却恒定而不变,万古而长青。这是人世生活本身的要求,也是合理的人间秩序的固有品质。既然一切法制和法意均源于生活本身,分别表述了生活的规则性存在和意义性存在,那么,法律之道
即生存之道,法意即生活的意义,而生活的意义主要即在此世道人心。
晚近中国对于西方法律的大规模移植,意味着对其背后的知识、学理乃至于道德和信仰因素的有选择继受,同时亦是一个将它们与中国人文善加调和的过程。此一建设现代中国法制和法意的过程,迄今而未止。百年间现实法制建设的顿挫,“有法不依”现象的普遍存在,反映
的不仅是规则的无效,同时并彰显了意义的危机、世道人心的紧张。由此,对于基本法理的阐释,关于规则的道德关切和信仰因素的追索,总之,对于法意的深入研究和进一步考问,依然是一个问题,甚至是一个更为急切的课题。
“法意丛刊”由清华大学“法治与人权研究中心”筹组,旨在庋集汉语法律学术资料,积累汉语法律思想成果,阐释法律的意义世界,对于上述问题作出现时代的回应。所收内容覆盖法哲学、比较法、宪政和人权等领域;体裁不拘,包括专著、文集、译著和选辑。经此劳心劳力,盼能涓滴汇流,聚沙成塔,增益中国文明的法律智慧,建设中国现代法制,最终塑育中国人理想而惬意的人世生活与人间秩序。或许,这也是当下法意的意蕴之一,而为编者馨香祝祷者!
许章润
2003年6月30日
于清华明理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