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经由调整我们的审视角度,从社会学的视角做一番研究,即对部落结构的特征,而不只是林林总总韵部落活动,逐个进行研究,或可表明,特罗布里恩的整个社会结构都是建立在法律身份(le-gal status)原则之上的。基此,鄙意以为,酋长对于平民、丈夫对于妻子、家长对于子女的要求,以及后者对于前者的要求,都不是任意面为和单方面的,而是根据确定的规则,融于互惠性的对等提供劳务的链条之中。
头领的地位是世袭的,建立在古老而令人肃然起敬的神话传说基础之上,环绕着半神化的灵光,并因表示分寸、谦卑的庄严典仪和严格的禁忌而进一步强化。头领握驭赫赫权力、财富和实施手段,即便如此,他也必须遵循严格的规则,接受“法锁”(legal fetters)的约束。当他意欲宜布战争、组织尸次探险或欢庆节日时,他必须发布正式的号召,公开宣布他的愿望,与贤:达之士进行缜密的磋商,并按礼仪形式接受他的百姓们的财物、劳役和支持,最后,他对此按照一定的份额予以回报。①这里,只要提一下笔者以前有关婚姻、夫妻关系和姻亲间的身份的社会学意义的阐释就够了。①举凡崇拜同一图腾的各氏族,或地区性和村社性的亚氏族,其根本特性均在于互惠地对等提供劳务和义务的体制,各集团在此体制下,上演着予、取游戏。
此类社会关系的法律性质的最显著之处,或许就在于作为予、取原则的互惠性,它不仅适用于氏族内部至高无上的统治者,而且盛行于最亲密的亲属集团间。正如我们已然看到,舅舅与外甥间的
关系、兄弟间的关系,即便兄弟与姐妹间最无私慷慨的关系,也是全然建立在双向互惠和对等偿报劳务的基础之上的。职是之故,这一切总是被指称为“原始共产主义”。在初民法学中,氏族常常被描述成惟一的法人,一个组织和实体。“这个单位不是一个个体,而是具有亲属关系的一群人的集合体。个体不过是这个集合体的一部分。”辛得尼·哈特兰如是说。要是想想作为社会生活一部分的亲属集团——崇拜同一图腾的氏族、氏族中由数个崇奉同一图腾的亚氏族组成的族外通婚单位、部落分支或者阶层——在与相应集团的交往中玩的互惠游戏,可以说信哉斯言。但是,氏族内部绝对的团结一致又是怎么回事呢?这里,有人给我们提供的一个通用的答案是,“如果不是合群本能,那么一定是弥漫着的集团情感使然”,据说这种本能或情感在我们现在所研究的世界的这一块地方特别地盛行,那里居住着“一群受到如此情感支配并以此激励自己的美拉尼西亚人”(理弗斯)。我们知道,这是一个绝对错误的观点。在最亲近的亲属集团内部的纷争、倾轧中,奉行的还是最彻底的利己主义,这种利己主义决定着亲属关系的全部发展可能。为了申说此点,笔者现在必须回过头来,提出更多的事实,并就此进行更为翔实的阐释,以最终戳穿亲属关系“共产主义”,和因着直接的血缘关系而使得氏族内部团结一致、休戚与共的神话,一个最近由理弗斯博士复兴,因而有谬种流传危险的神话。
这样,揭示出为我们的论辩提供佐证的一系列事实,其实也就表明了法涵盖和调节着初民的全部文化和整个部落结构,为此,让我们以与此协调的方式,系统地提出和阐释我们的结论。
十、对于习俗规则的定义和分类
本书第一节开篇就列举了当今主张初民系自发自愿奉守法律的一些观点。如今,基此假设而衍生出一些更为具体的命题,它们是人类学中极其流行的思潮,但在初民法学研究中却命运不济。
首先,如果说初民之奉守习俗规则只是因为他们完全无力违犯规则,那么,就无法对法律做出定义,也无法对法律规则、道德、礼仪风俗和其他习惯做出区别。因为我们据以将行为规则分门别类的惟一途径,是考察它们之被奉守的动因和保障其执行的手段,因此,因着预设初民乃自发自愿奉守法律这一假设,人类学必得放弃任何探明事实的固有秩序及其类型的努力,而这是科学的第一任务。
我们已经看到,辛德尼·哈特兰先生认为,在所有的初民社会中,无论是在初民自己看来,抑或如社会生活现实本身所昭示的那样,艺术、医术、社会组织、民生以及其他无法明确归类的事物的诸般规则,都是混缠无别、浑然一体的。他在好几处着意强调这一观点:“初民对于相似性的体认与我们大不一样。在我们看来,他是在毫无共同之处的事物间看到了相似性。”对于初民来说……部落的政策是一整体,不可分割……对于以上帝名义颁布,在我们看来具
有严格的法律效力的一部法典,却统涉典仪、道德、农业和医术,(初民)对此并不觉得有什么奇怪或扦格不入……我们可能把宗教与巫术、巫术与医术严予分别,而此社会中的人们却无此区别。”
在所有这些论述中,辛德尼·哈特兰先生对于有关“原始的前逻辑心智”、“初民淆乱不堪的类型划分”以及初期文化的普遍稚陋等现时流行的观点,都发表了自己清晰而稳健的高见。不过,这些见解只道出了事务的一面,说出的不过是一半真理一一至于此处所引他对于法律的看法,则是绝然错误的。初民专有一类义务性规则,既未曾赋予其任何神秘性,也不是以“上帝的名义”颁行,更不依恃超自然的制裁手段,而是依靠纯粹的社会连带义务的约束力来推
行。
如果我们将所有这些规则、惯例和行为模式均认做习俗的综合体,那么,毫无疑问,初民对它们均极怀敬意,其之所行,不外他人所行,且人人赞许之举;而且,如果他的爱好或兴趣不曾将他导诱或驱人歧途,他将会秉承习俗行事,绝不走人他端。习俗的约束、对于传统的敬畏及其情感的依恋,以及取悦公意的愿望——所有这一切使得习俗只是因为它是习俗才被奉守无违。就此而言,“初民”与特定区域内自我圆成的其他社会并无严格的差别,不管这是一个东欧的犹太人聚居区、牛津大学的——个学院,还是原教旨主义的美国中西部地区。但是,西班牙的贵族、初民、农奴,或德国容克们对于传统的热爱,对于习俗的遵顺习性和习俗本身的支配力,其于他们对于各项规则的遵从来说,都只有部分的说明力。
让我们将讨论重新严格限定在初民问题上。在特罗布里恩,有许多教导手艺人如何做生意的传统规则。这些规则之被毫无保留地遵奉无违,原因在于我们或可称之为普遍的“初民的遵顺习性”。但是,这些规则之被遵从的主要原因,还是在于它们具有被理性所认识并被经验所验证的实际功效。而且,其他调节如何处理与朋友、亲属、尊长、同辈各色人等关系的准则之被遵奉,是因为倘若违犯,则其人必感到或看出,在他人看来,自己乃一介粗卑无礼、乖戾愚顽之徒。这些都是淳良礼仪和风俗的戒律,盛行于美拉尼西亚并被最为严格地奉守无违。还有一些调整竞技、体育、娱乐和节日程序的规则,这些规则构成了娱乐或竞技的灵魂与实质,它们之所以被遵守,是因为人们感到并奉认,任何有违“游戏”规则的行为,都是在践踏竞技活动本身———也就是说,比赛就是比赛。必须指出,在所有这些活动中,并无对于个人嗜好或私利甚至习性的精神强力,此种强力与一切规则相忤,并使对于规则的遵奉成为一种重负。违背规则像遵奉规则一样地容易,而一旦你投身于一项体育运动或愉快的游戏时,只有服从一切规则,才能真正乐在其中,而不论这些规则是有关艺术、礼仪风俗的,还是有关竞技的。
还有一些规则关涉巫术的典仪、丧葬的规则与仪式等诸如此类的神圣而重要的事项。这些规则主要得到了超自然的制裁和认为不得亵渎神圣事物的强烈情感的有力支持。调整对于近亲属、家人和感受到深厚友情、忠诚与奉献精神的其他人的个人行为的规则,也受到了同样强烈的道德力的维护,而这些情感保证了此一社会性法典的效力。
以上对于各类规则的简要举列,其意不在对其进行分类,而旨在清楚地说明,在初民社会中,除了法律规则之外,还存在着其他几类由内在动因或外在强力,而主要是靠心理动因或强力维护的规范和传统的戒律,它们无论在哪一方面都与具有法律性质的规则迥然不同。因此,虽然本人研察的注意力自然主要集中在法律机制上,但鄙意并非证明所有的社会规则都是法律性的,恰恰相反,我要揭示的是,法律形式的规则不过作为类型之一,已然完全消融于习俗的统一体中。识的社会学家,其中洛伊博士掌握着初民的第一手材料,其研究初民社会司法制度的杰出著作,也似乎流同于这一普遍的偏见。
在我们自己的研究中,迄今为止,我们所看到的都是些积极的实在性的戒律,违犯戒律即被惩罚,然而不是刑罚惩罚,使惩罚得以实现所凭恃的不是纯然暴力性的强制方法,其实现机制超出了一般意义上各自独立的民法或刑法的范畴。如果我们必须用一些现代的,因而势必是不恰当的标签,来描述若干论著中已然刻画的初民规则,那么,它们就必得被称做特罗布里恩岛民的“民法”。
“民法”,这一实在法统治着部落生活的一切,构成了在一方看来是权利,而在另一方则认做义务,而由他们社会结构中世传的互惠性与公开性这一特殊机制保证施行的具有约束力的责任。这些民法规则相当灵活,葆有一定的伸缩幅度。它们不仅规定了对于违犯规则者的刑罚,而且奖励积极履行义务者。它们的效力因初民对于因果关系的理性认同而得到了保障,并与抱负、虚荣、自豪、公开炫耀的自我欣赏的愿望,以及依恋、友谊、奉献和忠诚等诸如此类的
社会性与个人性的情感休戚相关。
似乎无须再重申一遍,正如我们已经发现、描述和定义的美拉尼西亚人的生活,“法律”和“法律现象”并不存在于什么绝然独立的制度中。毋宁说,法律是他们部落生活的一部分,是他们的部落生活结构的一方面,而不是什么独立的、自我圆成的自治的社会制度。法律不是借诸什么预见定义违反规则的可能形式,并予以相应的预防和纠正的某种特定的法令体系中,法律表征为是否履行责任的特定结果,而使得初民不可能逃避责任却不付任何代价。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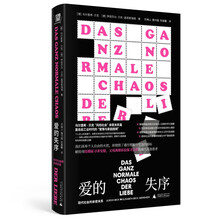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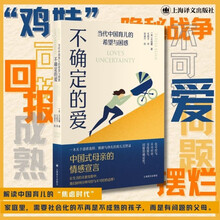






现代人类学的探索者,经过全面的理论训练踏入这一领域,面临着诸多的问题,怀着兴趣,或许还有些先入之见,既不能够,也不会执意将其视域局限于具体琐碎的事实和林林总总、千头万绪的资料。他念兹在兹地对一些基本课题阐幽发微,解决自己的根本困难,将许多尚待确证的论点提升为具有普适性的一般原理。例如,他孜孜于获得的结论是,初民的心灵是绝然迥异于我们,还是与我们几乎无二;初民们是恒久不变地生活于超自然力和危险、恐惧的世界,还是恰恰相反,如吾辈中的任一位常有的那样,亦有其清明澄澈的安详时光;氏族的和谐团结究属一种绝对而普遍的约束强力,抑或如任何基督徒那样,懵然未开的异教初民们同样自私自利,追求自我的享乐。
在写出他的研究结果时,现代人类学家自然极欲将他丰富却多少有些杂乱无章、铺陈枝蔓的个人经历,沉积、附着于对于特定事实的描述中;陈述与通常的初民文化理论正相抵牾的习俗、信仰和组织的具体事实。这本小书即为一个田野工作者本着此一意图耕耘的收获。为了减轻此一意图的过错——如果算是过错的话——我想强调指出强化人类学法学理论的急迫性,尤其欲指出理论应源自与初民的实际接触过程中。我还想指出,在这部作品中,我的观点和一般性的结论均寓于描述性的段落而清晰浮现。最后,但并非无关紧要的是,我想申明,我的理论不是来自于猜测或基于假设的推论,而只是尝试对此问题做一系统的表述,将有关精确的范畴和清晰的定义引入这一领域。
职是之故,本文遂以现在的形式致力于此。本文材料的准备和结论的提出,起初系应大不列颠皇家协会之邀而作,此前并于1925年2月13日,一个星期五的晚上,作为论文宣读过(题为“一个初民社会法的效力与秩序”)。如同常有的情形那样,我发现自己手头的材料尚多,较诸一个小时演说的容量,其能涵括的结论会更多。其中一些我特地发表在《自然》杂志(见附录,1926年2月6日和1925年8月15日的论文)。这本小书则系上述论文合集后的完整的版本。
在此,向皇家协会委员会慨允使用原有版式并允重印本书的美意善心,谨致谢忱。《自然》杂志编辑理查德·格雷戈里爵士慨允重印上述论文,笔者亦感激不尽。而且,在我工作之初,即蒙爵士的帮助和鼓励,其嘉惠笔者厚矣!
本文准备过程中,现在伦敦经济学院文化人类学系从事研究工作的格蒙德·弗思先生多予协助,由于劳拉·斯佩尔曼·洛克菲勒纪念基金会的资助,我得以确保获得他的帮助。作为对于整个社会科学发展的关注的一部分,该资金委员会近来特别注重推进人类学的发展。对于正在迅速消失的初民部落的研究,是我们这些文明——现正遭到毁灭至今仍不幸为人们所忽视的初民的生活——的一项职责。这一任务不仅具有极高的科学和文化意义,亦不乏相当的实际价值,有助于白人在统治、剥削和“改善”土著时减少对后者造成惨恶的后果。劳拉·斯佩尔曼·洛克菲勒纪念基金会对社会研究分域的人类学的雅意,将获得现在和将来的人文学者们的深挚谢意,他们的劳动才是对这位高贵女性的永恒纪念,而在人们的胸中筑起一座心碑。
布·马林诺夫斯基
1926年3月
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