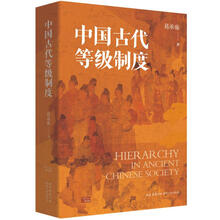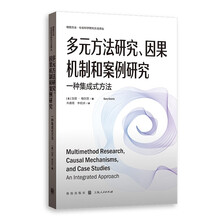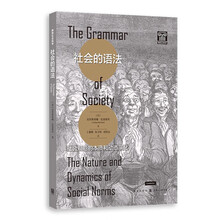在农业对GDP的贡献率不到15%(今年国家统计局修改了第一、二、三产业的划分类别,把直接为农业服务的一些产业划归农业,农业的比重也许会有些提高),农业产值的年增长率越
来越低于第二、三产业的年增长率的情况下,农业还是不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哪种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具有基础地位,也许在别的国家(例如人口不多,或者其他资源如石油特别丰富等国家)可以根据一种产业在GDP中的比重,但在我国却必须根据基本国情:我国是人口大国,占世界人口总数的1/4,但人均耕地却只相当于美国的1/9。现在,我们的吃饭问题基本解决,靠的仍然是占人口总数70%的农业人口养活占人口总数30%的非农业入口。就以从业人数计,农业从业者也占一半。即使将来农业从业人数进一步减少了,农业在CDP中的比例进一步下降了,只要人地矛盾不能从根本上缓解,只要人口总数设有相当幅度地下降,农业的基础地位就不可能改变。前几年,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的布朗所长提出问题:谁来养活中国人?遭到了我国一大批有识之士的坚决驳斥。当然是中国人养活中国人。我们解决了“中国人可以养活中国人”的问题,但却无法改变“中国人只能靠自己养活自己”的问题。13亿人口,将来是15亿—16亿人口,一旦粮食出了问题,谁都救不了我们,谁都可以来卡我们。那时候,战略武器用不着导弹、原子弹,粮食就是最好的战略武器。中国几千年,治国经验的最高总结就是“民以食为天”,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半个多世纪以来的重要治国经验就是“手里有粮,心里不慌”。
如今老百姓意见最大的恐怕是医疗问题了。20世纪末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国家和地区的排序中,在健康服务的公平性方面中同居然在191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在倒数第4位,中国的医疗卫
生事业在“可及性”(这是一个卫生经济学的概念,也称“可获得性”,即指老百姓得到医疗卫生服务的权利的实现)方面的表现使我们蒙羞。而在另一方面,医疗部门挣钱的热情始终不减,在西南某大城市,政府办的二大“非营利”医院一年赢利4亿多元已经成为老百姓茶余饭后“摆龙门阵”的谈资。近来,“非典”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战斗在“非典”防治第一线的医护人员也以他们忘我的职业精柿和辛勤劳动乃至壮烈牺牲得到全国人民的崇敬。但是,我们还是听到了一些不和谐音。虽然中央三申五令,医院不得以任何借口拒收“非典”病人或疑似“非典”病人。但据报载,西部某城市的一家医院还是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拒收7名有明显“非典”症状的已去世的疑似“非典”病人的亲属,原因是他们一时拿不出2000元住院押金。记者晓之以理:“上级明文规定对‘非典’和疑似病人要先治疗再说,大政策管你的小政策,小道理应服从大道理。”有位主任竟说:“谁说的谁来干。我们也有家人、孩子,我们也得为他们考虑……”
7名已故“非典”病人的疑似病人亲属被扔在急救室6个小时得不到医治的后果无疑是严重的,从以上对话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事实,忽视普通老百姓的健康权,在一些医疗部门中已经习以为常,医德的丢失不是偶然的,而是政府在公共服务领域的长期缺位造成的不良后果。现在即使是政府政策有了根本的改变,但是医疗部门已经养成了的习惯自有其惯性,但愿出现在西部某城市这家医院的事情只是绝无仅有的“个别”案例。
20世纪末汹涌而来的下岗、失业浪潮,更凸显出公共服务领域政府缺位的尴尬。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以百万、千万计的城镇居民陷入贫困的泥淖,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政府却
因为“没有钱”而在采取更为积极的对策方面迟疑不决。先是仅仅采取“年节慰问”的传统方式,继而把建立最低生活保障的责任“下放”给地方。经过6年的努力,1999年在全国所有的城市和县镇都建立起这项制度以后,得到这项制度庇护的只有280万人。在21世纪,又经过了一番努力,终于统一了思想,中央财政在2001年拨出了23亿元,政府总的财政投入达到将近亿元;2002年又翻了一番,中央财政达到46亿元,总的盘子是105亿元,救助对象的规模扩大到2000万人左右,这才使这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不可少的社会保障制度走上了正常发展的道路。
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10年历程以及其间的变化构成的轨迹,大致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和政府的财政收入的变化的轨迹重合,其转折点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据《2002年中国数字
黄皮书》记载:1994年全国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下降到谷底,仅有11%;其后,中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国家财政收入一改不断下降的颓势,重新呈现出稳步上升的
趋势,到2001年又恢复到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7%,2002年增加到18.5%。因为国内生产总值的规模与90年代中期相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同时政府税收征管的力度加大,加上近年来市场物价基本平稳,所以实际增长是十分可观的。1995年,国内生产总值是58478亿元,政府财政是6242亿元,中央财政是1995亿元;进入21世纪,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政府的财政收入也大
幅增加:2000年,国内生产总值为88190亿元,政府财政是13395亿元,中央财政是6989亿元;2001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到95933亿元,政府财政是16386亿元.中央财政是9772亿元。2002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到102398亿元,政府财政是18914亿元,中央财政已达11020亿元。
第三,统一的规则在实施过程中可能只关照到一部分人,因为所制定的一致标准是需要一定条件才可以达到的。现在农村处理集体资产所采取的拍卖和竞标的方式对很多农民来说是不公平的,因为竞争任何一份集体资产都意味着自己要有比较好的经济基础,要有比较好的经验和动员资源的能力。有了这些潜在的要求以后,尽管招投标是公开透明的,在表面上,机会对所有村民都是开放的,但实际上游戏规则本身已经将许多人排除在游戏之外了。几乎所有的人刘森林的拍卖都有兴趣,但是真正能够参与竞标的人很少,而真正能够出比较高价格竞争的就更少。
农村集体企业的改制大都采取了类似的做法,能够参与游戏的人很少,大多数社区成员都被排斥在参与企业竞标的游戏之外,很多集体企业的拍卖最终只能拍卖给原来企业的经营者。尽管人们可以从效率的角度为这种现象辩护,认为能够投标到最高价格的人应该是最适合经营企业的人,也是给集体带来最大收益的人。但是从社区公平的角度看,这就很有问题了,在集体企业时期,这些经营者就已经比一般的农民获得了更多的利益,一些集体企业因为经营不善而被拍卖也是这些经营者的原因,而最终他们又以较低的价格获得了这些企业,这对于一般的社区成员来说无疑是不公平的。
集体资产在社区中承扣着很多职能,如维持社区的福利、创造社区内就业,而在村庄集体资产被拍卖以后,社区就完全失去了这些职能,从而使相当多的人的利益受到损失。实际上多数的农民都可能意识到这种现象后面所隐含的不公平,但是农民无法对抗统一的规则,甚至他们也要承认这种规则是公平的,因此他们转而去对付具体的事件。
事实上,统一的制度对于解决农村具体问题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农村原有的制度安排往往是在多种因素的长期互动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这些具体的制度安排保持了农村社会的大致平衡。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是农村的人口进出和妇女的土地权力问题,国家的制度安排要求男性和女性的平等,同样享有土地和居住的权力,但是对于社区来说,他们必然面对人口进出的动态平衡问题.特别是在婚嫁过程中,一些人要离开社区,不再享有社区的权利,而另外一部分人进入社区,这样才能保持社区内的人口平,衡。尽管国家法律要求保障妇女的土地权利,但却无法解决一个社区人口进出平衡的问题。
将统一的制度和原则纳入到地方社会是国家向农村社区延伸过程的一部分,随着国家制度的建立和在农村取得统泊地位,农村原有的制度和规则就开始被认为是落后的而失去其合法性。外来的制度携带着国家的权力迅速取代农村社会原有的制度,这些制度是农民所不熟悉的,但却是农民表达利益所需要的;而农民所熟悉的制度已经不能作为根据,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农民表达的能力,因为他们不得不依赖他们所不熟悉的语言和逻辑,而这些语言和逻辑与他们的日常生活又相去甚远。在这种规则面前,农民比以往更加弱小。所以我们在当今的农村社会中听到太多无奈的声音,他们觉得自己不会得到帮助,因而受到委屈以后也可能根本不去试图表达不满。
从解决途径和机制来看,要把政策调整、组织重构与制度改革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分步骤、分阶段地实现以上的国民待遇目标。当前国家在陆续调整一些政策,试图缓解“三农”问题,其中有不少涉及农村流动人口。最近的国务院有关政策把农村人口外出务工经商看成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一种有效的办法,要求各泥人地政府积极解决农村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问题,切实保障农民上的各种权益等,尤疑表明中央政府正在努力消除一些国民待遇方面的不平等、不公正问题。但是,政策的调整如果没有制度的改革和组织的重构,那么其效力就会受到影响,甚至难以发挥作用。我们看到,这些新政策确实旨在更好地保护农村流动人口的权益,但是在实施过程中还没有完全取得预期的效果,原因就在于制度改革和组织重构没有跟上,没有进行配套改革。比如,2003年国务院办公厅发文要求各流人地政府解决好农村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问题,但是在实施中却碰上了齐种各样的消极敷衍,关键问题在于没有建构相应的制度来贯彻这样的政策,比如现在的财政体制是地方政府主要负责国民义务教育,仅仅从政策上主张给农村流动人口子女受教育机会,但是财政制度、政府官员政绩考核制度等都没有进行相应的改革。结果,政策的调整没有很好的效果,不少流人地政府依然我行我素,取缔外来打工者子弟学校、驱赶农村流动人口等,千方百计找借口来限制农村流动人口子女在城市接受教育的现象依然存在。而组织的作用前面已经做了详细的分析,主要在于在农村流动人口中组建党团、工会组织及行业协会等,从而能够与相关的管理部门进行对话、交流和协商。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