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各样的改革究竟产生了什么结果,这显然是最为重要的问题。但它决不是个简单的问题。“结果”这张标签可以贴到许多东西上面去,而且可能包含各种概念。正如布伦森所说,商谈、决策与实际行动一样都可以被认作重要的结果。此外,它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由谁来评价,对谁评价以及为什么评价。因此,对“结果”进行全面的讨论就包括“结果针对谁、结果由谁规定、结果指向何种目标?”这些广泛的问题。
在关于改革的政治言论中,有些具有明显的乌托邦特征——特别在英国和北美。公民们将在天堂里享受高质量、低成本、很容易得到并且负责任的服务。他们对政府将感到更加满意。公务员也将接受一种新的文化,这种文化的价值观是节约、效率、有效和为顾客服务。公民将拥有权力,公务员将受到政治家和公民同样的信任,政治家则将提供“领导”和战略指导。如果这些都能实现该有多好!然而,这也许能够——很多政府好像都雄心勃勃地要输出它们的改革产品:“公民宪章是有史以来最完整的方案,它将提高质量、增加选择、保证更好的价值、并且扩展责任性。我们相信它将树立一种模式,这种模式不仅适用于英国,而且可以作为世界各国的模式:”(Prime Minister,1991)既然期望值被提得这么高,那么内部评价和报告就很难不把它说成结果良好。“在最完美的世界上,万物必有最好的归宿”(伏尔泰,《老实人》)。毫不奇怪,当英国公民宪章启动两年半之后,主管部长就报告说,表现令人鼓舞——任何贬损的话都可能带来极大的政治代价。
要形成一幅更平衡的画面并不容易。然而,相比之部长和其他与会者的重要谈话,有些材料就不是这样过分热情,而是更加谨慎。有些主要是作为内部使用的基层部门的报告(Employment Service,1994:Ministry of Finance,1997),有些试图作出学术评价(e.g.Aucoin and Savoie,1998;Peters,1998a;Pollitt,1995,1998a),有些是相对独立的公共委员会或专家的报告(e.g.Schick,1996;TaskForce on Management lmprovement,1992),还有由国家审计机构进行的业绩审计(e.g.Auditor General of Canada,1993,1997;National Audit Office,1995)。把这些材料都合在一起仍然有很大的距离,但这已经足够勾画一个大致的轮廓:这个轮廓的第一条信息是——很不幸——根本不存在明确的“根据对清晰经验的简单、完整的研究循环而作出的合理修改”(Olsen and Peters,1996a)。相反,我们具有的通常是矛盾的信息以及不清晰的、变化的现实。
虽说这种情况对理性主义者(或者对我们每人身上的理性主义因素)来说是令人沮丧的,但它(正如布伦森所说)也许同样有一些积极的好处。从政治观点看,它可能使高度(但有时则有点冲突的)理想化的论坛即便在具体行动的可能性非常有限的情况下也得以保留下来:
我们很少把高尚的价值观反映在行动中,而且因为它们不现实的高度和内在的不一致,我们最好的价值观不可能充分地反映在行动中。保持高尚的价值总与罪恶有关,这就是说,在价值观和行动之间有背离。如果要提倡一些并没有或不能据以行动的规范,那就需要一些虚伪。罪恶和虚伪对于高尚道德的创造和保存是必需的。没有罪恶和虚伪的人是那些追求可以实现的目标,却以他们的道德作为交换的人(Brunsson,1989)。
本章其余部分分为7节,每一节再分几个小节。在第一个大节(第二节)里,我们会区分好几个可以规定和评价结果的不同层次。随后的4节里,我们检查在这些层次上可以得到的典型证据,我们还要考虑(很多)解释的问题(从第3到第6节),最后(第7节)我们试图对公共管理改革的结果的已知和未知进行总结。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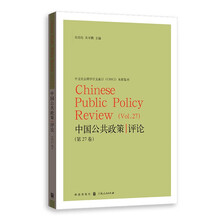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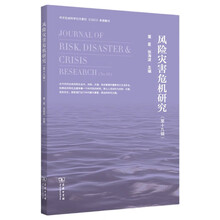





这是一本对西方十国的公共管理改革进行比较研究的学术著作。作者研究的切入点是公共管理改革,研究的时间跨度是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20年,选择的国家是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芬兰、瑞典、加拿大和荷兰这l0个最具有代表性的西方国家。但我们可以从中得到的,却并非仅仅各国在公共管理改革中采用的具体措施。作为一个在大学工作
的学术工作者,我更感兴趣的是对于公共管理的解读。
一
就公共管理这门学科而言,20世纪80年代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正是在这个时期,发生了对于公共管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两件大事。其一是英国的撒切尔政府和美国的里根政府在公共管理领域掀起的大规模改革运动;另一件则是在美国掀起的新公共管理运动(NPM)。从此开始,公共管理改革的运动在世界范围此起彼伏,方兴未艾,一直持续了二十多年,至今未见消退的迹象。也正是从这个时期开始,公共管理这门学科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革,从而彻底改变了该学科的性质。这两件大事,一件发生在政府部门,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实际工作;另一件则是学术界的事情,发生在象牙塔内。然而,两件彼此性质相差甚远的事情,却相互配合得丝丝入扣,不仅在时间上基本同步,而且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对于公共管理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影响。这一点,正是我们这些有志于从事公共管理事业的学者应该特别注意的。
西方十国的公共管理改革源于两个基本问题。
首先,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速,各国政府面临越来越大的经济压力或者说财政压力。人们普遍相信,政治系统必须减少被行政系统和法律系统消耗的资源数量,或至少要减缓其增长的速度。否则,经济系统就会遇到问题,选民就会变得越来越不支持。因此,节约就成为需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由此而来的第二个问题是政治系统在公民眼中是否具有合法性的问题。西方各国政府的“合法率”正在下降。由此导致的问题有:政治家的权威受到削弱;选民的忠诚度和投票者的稳定性不断减少;公众对于政治过程作为解决社会问题有效手段的信任度下降;蔑视和逃避法律的行为可能会开始增加。
这两个问题要求政治系统的领导作出战略性反应。因为他们需要节约资金(或给人以正在作这种努力的印象),同时还要增强他们的合法性。于是,对行政系统进行改革就成为他们唯一的选择。
各国政府对于行政系统的改革采取了四种战略,由于它们都用英文字母M打头,所以可以简称为“四M”战略:
第一个M是“保持”(Maintenance)。所谓保持,指的是加强传统控制,限制支出,冻结招收新员工,发动反对浪费和腐败的运动,全面“挤压”行政和法律系统。
第二个M是“现代化”(Modernization)。就是使行政系统现代化,引进更快、更灵活的方法来造预算、管理、会计、为用户提供服务。这些新的做法中,有些可能是从市场方面借用的。然而,这样的改变同样可能要求对政治系统作出相应的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