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星移民之梦
20世纪50年代,一位叫欧文·A·德布兰克的天主教高级神职人员强烈反对“一个时常挂在嘴边的看法,即节育是解决世界人口增长过快引发的问题的唯一方案”。为了在抑制人口增长之外另找出路,德布兰克说,我们应当欢迎人口增长并制定计划将过剩人口运往其他地方。这样我们能继续人类的千年传统,即在把老家弄得一团糟之后搬一个新家:
我们承认德布兰克的意图是好的。这符合他的价值体系:他是全国天主教福利委员会家庭生活局局长。该组织致力于鼓励大家庭。他们公开宣传的东西主要针对罗马天主教徒。
一些天主教徒赞成太空移民,因为教会统治集团反对人工节育。但是我们不应忘记,科学本身已经成为千百万人的某种宗教。技术的奇迹已经使许多人对一尊被称为“进步”的神不加
批判地顶礼膜拜,而这位“神”有时又被等同于永不停息的增长。如果控制人口增长是不道德的,那就意味着只有向其他星球移民才能矫正地球上的人口过剩。这样,有神的和无神的宗教就能够在概念的交点相会。
1958年,NASA(国家航空航天局)成立后4年,其国会监护人即科学和宇航委员会支持将太空移民作为“人口爆炸”问题最终解决办法的观点。受雇于NASA的技术人员无疑没有充分考虑德布兰克等人的建议,但是,如果一个机构在为其高薪职位的空间而战斗的时候,它的局长们完全不必急急忙忙地去纠正那些增加其预算规模的谈论。
适宜居住的行星有几个?这些星球对于我们这些地球人来说真的是可居住的吗?20世纪初,曾有人认为火星和金星是人类生活的可能之地。但NASA成立后不久发现,环绕太阳的其他行星都不适合我们这种生命生存已是无可辩驳的事实。现在我们知道,一个在金星表面的人将不得不在足以将铅融化的温度下生活,他呼吸的是二氧化碳含量为96%的空气,在相当于我们的洋面1/2英里以下水压的大气压下劳作。(据推测,金星已经遭受了毁灭性的“温室效应”,而这正困扰着地球上的人类。
至于火星,这个科幻小说中的常客,在这颗红色的行星上生活就像住在两倍于珠穆朗玛峰的高度上。火星的空气中仅含有极少量的水分,其大气压力只是地球海平面大气压的1%;无论白天还是夜晚,温度都在华氏0度以下。因此,当谈起天体间的移民时,其实我们考虑的只是恒星间的迁移,移向太阳以外的其他恒星——假设它们有自己的行星。进一步的假设是,在这些假想的行星中,有几个也许像地球一样适宜于生命。(我们对发现另外的金星或火星没有兴趣。)
“坏运气”和系统稳定性
环绕着复利机构的沉默的阴谋是易于理解的。为了鼓励工人的忠诚,那些掌管着认可社会经济系统的人感到,他们必须宣称这个系统是绝对稳定的。并且,如我们所知,一些银行家甚至有勇气将“永久”一词体现在他们机构的名称中。(人们很容易想象出,对于一个背负着“麻烦到来前的永久国家银行”这个最诚实的名字的机构,会发生什么。)残酷而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在一个物质资源有限的世界上——它是我们可获得的唯一世界,夏利本身造成了内在不稳定的系统。
关于高利贷,是到了知道我们已经走到何处、未来我们可以项见什么的时候了。亚里士多德完整地表述了古人的主要看法:
有两类获取财富的方式:一种是家庭管理的一部分,另一种是零售贸易。前者是必要的,并且是光荣的,而那些构成交易的东西应当受到审查;由于它是不自然的,以及一个人从另一个人身上获利的模式。有最充分的理由认为令人最痛恨的财富获取方式是高利贷,它从货币本身中获利,而不是从其自然的对象中。由于货币的目的是用于交易,而不是用于增加利息的。这个意味着钱生钱的术语“利息”,被用于繁殖货币,因为后代与父辈相似。在所有获取财富
的模式中,这是最自然的。
16个世纪之后,我们发现奥雷姆对同类问题有诸多论述:“一个不结果实的东西会繁殖,这是荒诞而王常的,诸如金钱这样明确不孕的东西会结出果实并自我增殖.这也是荒诞而反常的。”
对于高利贷本质上是反常而邪恶的这一古老观念,奥雷姆是最后一位支持者。在奥雷姆之后,有限的高利贷(被重新命名为“合理的利息率”>受到基督教的支持,后来又得到占压倒性多数的经济学家的支持。
欧洲世界进人现代繁荣的进步会受到高利贷的极大阻挠的例子俯拾即是。高利贷以其结果证明自己是正当的:指数增长的债务奇迹般地刺激债务人去发现新的开发自然的途径。对高利贷的历史辩护可被归纳为铭刻于建筑师克里斯托福·雷恩纪念碑上的话语:Si monumentum requiris,circumspice——“如果你寻找(高利贷的)纪念碑,环顾左右。”将高利贷已经实践了8个世纪的西方世界的财富和大量的物质基础设施,与高利贷尚未系统进行的大多数国家的贫穷进行比较。大街上的人视高利贷为家常便饭,而视通货膨胀、银行破产、债务拒付、充公税等现象为反常而大声责难。但是,正是只有通过“不利”的持久才能使带来利息的“有利”持久存在。
在这方面,如同在其他方面,经济学家凯恩斯作为他那一行的例外特别醒目。1930年,他不仅在一项预备提议的系统工作中,而且在一篇提出“我们孙辈的经济可能性”纲要的类似论文中,阐述了对高利贷的反对意见。他指出,有一天我们也许,
回归到某些最确定无疑的宗教原则和传统美德——贪婪是一种罪恶,榨取高利贷是一种不轨行为,对金钱的爱恋是可憎的……但是小心!所有这些时刻尚未到来。至少在下一个100年,我们必须对自己以及每个人假称公平是邪恶的,并且邪恶是公平的。因为邪恶是有用的,而公平却不是。贪婪和高利贷以及谨慎在有点儿长的时间内,必须是我们的上帝。
“下一个100年”已经过去大半,高利贷依然持续。凯恩斯聪明的孙辈逐渐掌权。孙辈的孙辈将终止高利贷吗?对于那些寻求个人成功和社会普遍繁荣的人,也许,最好的建议是沿着高
利贷之路——冒险地走一小会儿。
当变化发生时,它也许很突然、很痛苦,因为它将要求传统价值的倒转。一个后高利贷社会将强调:
1.高利贷是反常的(并且,也许会被称为“邪恶的”);
2.通货膨胀、银行破产、债务拒付、充公税是一个要求稳定的高利贷社会中必要的矫正措施;并且
3.由于公平的原因,高利贷的实行必须受到共同体的严格管制,并且在许多情况下是禁止的。
6个世纪以来,“明达的观点”将利息的无限支付视为正常且总体上是合意的。人们毫无疑问地假设物质财富能够永远以指数增长。现在,我们必须承认只有债务能永远以指数增长:一条无限上扬的指数曲线在现实世界毫无用处;并且,诸如通货膨胀和债务拒付这样令人不快的事件是一个以高利贷为基础的社会系统的必需的矫正之法。理性革命所需要的是一项艰巨的挑战——如果不是对我们就是对我们的孩子。
人类是理性的吗?
人类的事务当然比其他动物的事务更为复杂。人类行为明显缺乏一致性造成了每一项已提出的理论都会遭受难以对付的夹道攻击c甚至在马尔萨斯含蓄地提出种群数量调节器之前,有几个观察者已注意到了后来会被引用来对马尔萨斯的解释内容提出质疑的相反行为。远在马尔萨斯之前,亚当·斯密要求注意一些贫穷的苏格兰母亲的巨大生育力(方框16—2)。但是注意,他将研究推向深入,指出一个生殖力非常旺盛的母亲也许可能特别没有生育能力——也就是可能没有留下几个在下一代能成为父母的子孙。被引用的章节清楚地描述了在福利国家之前的岁月里的马尔萨斯种群数量调节器。伴随着福利国家的出现,对智人这一准例外者物种的同情引出了新问题。(如果同情引起向失败投资,非人类的动物的遗传家系将持续多久?)
无疑,人类的行为的确产生了问题。博斯韦尔的约翰森博士几乎没有对什么人类行为未下判断。他谈及导致人类生育的动机。在1769年10月26日(当时马尔萨斯只有3岁)的一次谈话中,约翰森指出:“人类结婚不是出于理性和精明,而是爱好。如果一个男人是穷人,他想,‘我不能变得更糟糕,因此我要娶佩吉。”
这个评论要求注意这样的事实,即马尔萨斯的种群数量调节器假定人类是理性的。当维持生存极为艰难时,一个理性的人会通过承担一项使另一个人(婴儿)存活的义务,从而使他(或
她)的状况变得更糟吗?当然不会,然而,约翰森博士说人们有时就是以这种方式行事的。任何一个有一般经验的人都能举出确证的例子。或者是人们有时行动非理性(这引起人们对种群数量调节器的解释力的怀疑),或者是存在着没有包括在图16—1中的抽象图解的其他人类动机。
相形之下,在非人类的世界,许多例子是已知的。在那里,谨慎的动物准确地使其家庭所承担的义务与未来环境的可能条件相匹配。例如,通常,在寒冷的天气里,鸟类所产的卵比食物更充足时所产的卵少。也许那些如此热烈地为人类豁免主义教
义辩护的人将满足于这样的结论,即人类与次要的物种不同,对非理性行为的非难具有独一无二的敏感?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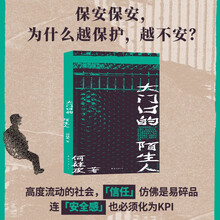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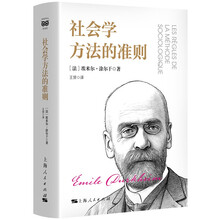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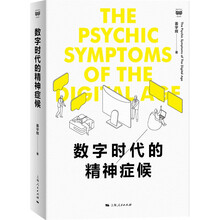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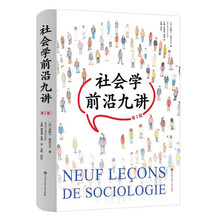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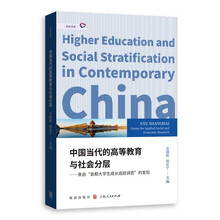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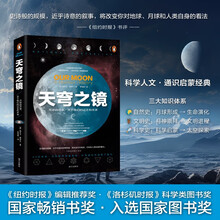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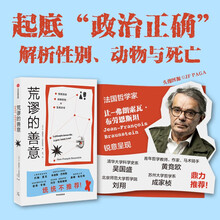

一片草原上生活着一群聪明的牧人,他们各自勤奋工作,增加着自己的牛羊。畜群不断扩
大,终于达到了这片草原可以承受的极限,每再增加一头牛羊,都会给草原带来损害。但每个牧人的聪明都足以使他明白,如果他再增加一头牛羊,由此带来的收益全部归他自己,而由此造成的损失则由全体牧人分担。于是,大家不懈努力,继续繁殖各自的畜群。最终,这片草原毁灭了。
讲述这一则现代寓言的,就是本书的作者哈丁。1968年,他发表在美国《科学》杂志上的题为“公地的悲剧”的论文,深刻地剖析了当今世界环境恶化的原因。他的思想,以其对人性弱点和制度缺陷的洞察,可以说使整个世界受到震撼。这也是哈丁其他作品的特点,通晓古今,涉猎哲学、经济学和生态学等多个学科,分析问题时透彻无情,阐发观点时尖锐活泼,能够使每个读者,无论同意还是不同意他的观点,都无法阻挡其思想的冲击力。哈丁的出现,可以说是环境与生态保护运动的幸运。
本书的主题,是否定一切现实生活中的指数增长。无论人口增长、经济增长,还是银行的利息增长,哈丁都认为是不可持续的。他的逻辑是简单而有力的:只要我们承认这个世界是有
限的,那么,一切指数增长终将是虚幻,是泡沫,总会有烟消云散的一天。为了证明这一点,哈丁动员了他的所有学识,从土地生产力谈到外星,从千年以前谈到未来,从经济学谈到核物理。在他的笔下,千百年来有关指数增长的论战跌宕起伏,论述之精彩,可以说是一场思想的盛筵。
本书的现实意义同样不可忽视。虽然人们赞美清醒,但清醒是不容易的。总的来说,我们更为常见的现象是,泡沫虽然有害,但社会往往喜欢泡沫。堆砌泡沫的人会受到追捧,而刺破泡沫的会惹人生厌。就是在我们的国家,虽然过度的人口增长已被认识到是不好的,但有谁会质疑“持续经济增长”?甚至“持续高速增长”也会受到许多人的笃信。在美国,社会氛围也同样如此,增长总是好的。在全世界,从马尔萨斯到《增长的极限》,都受到学术界强烈而持久的抨击,而鼓吹增长的学者则很少受到同样的待遇。在这样的气候条件下,哈丁的这本书矛头直指增长本身,对所谓“增长教义”进行彻底的批判,对于“增长热”中的世界确实是—帖清醒剂。
需要说明的是,哈丁的某些观点是其西方中心主义的反映,例如,他认为除信息以外,发达国家不应该向贫困国家提供帮助;他主张西方国家之间进行贸易,而将发展中国家排除在外。这些观点表明他对这个世界以及他全身心投入的环境保护事业的认识有着很强的局限性。对此,读者自可明鉴。但无论如何,本书值得一读,哈丁值得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