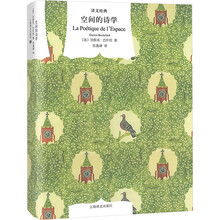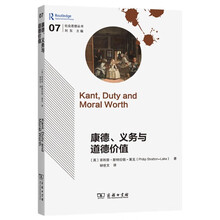斯宾诺莎的生活和活动时期——17世纪,可以说是从封建专制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重要世纪。这个时期的最鲜明标志,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西欧,特别是在西欧最先进的国家——英国和斯宾诺莎的祖国荷兰取得了胜利。
靳宾诺莎的第一批哲学著作问世,是在17世纪后半叶初期。在此之前,欧洲已经发生了两次初期的资产阶级革命:1525年德国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结果由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不成熟而遭到失败;1566—1609年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这是一场以尼德兰的资产阶级为主体的全民族反抗西斑牙封建君主专制和争取民族独立的爱国战争,结果产生了欧洲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尼德主联邦,或称荷兰。斯宾诺莎生活和哲学活动的时期,正是1640—1689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发展到高潮时期,这次革命,正如马克思听说的,乃是“欧洲范围的革命”,它“在更大得多的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整个世界的要求”。
因此我们可以说,斯宾诺莎的一生正是处于欧洲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的伟大历史进程中,特别是他的祖国荷兰在经历了资产阶级革命后发展成为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依照马克思的说法,也就是“标准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一历史进程无疑会对斯宾诺莎的哲学思想的形成有决定性的影响。
在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方面,我们首先要提到法学理论家雨果·格劳修斯(1583—1645),他是国际法和航海法的奠基人,最早提出资产阶级自然法权和道德观点的代表人物。戏剧家和诗人冯代尔(1587—1679)从圣经和民族史中选取主题,写了大量脍炙人口的颂歌和讽刺作品。一代绘画大师伦勃朗(1606—1669)以他那明暗对照的光线效果和普普通通的现实题材为17世纪欧洲绘画开辟了一个崭新境界。
17世纪的荷兰是当时欧洲的科学文化中心。欧洲第一所新教大学——莱登大学创立于1575年,在整个17世纪一直是欧洲人文主义思潮的诞生地。在它提倡学术自由和信仰自由的影响下,欧洲其他国家的一些科学家和哲学家都来到这里从事科学研究,荷兰已成为欧洲所有酷爱自由的学者所向往的中心。英国哲学家霍布斯曾这样写道:“伦敦这个城市以及其他大的商业城市,由于赞美低地国家(指荷兰)在摆脱他们的君主西班牙国王统治之后的繁荣昌盛,都倾向于认为如果这里作类似的政权变动,也会对他们产生同样的繁荣昌盛。”霍布斯本人曾经到过阿姆斯特丹,并在那里出版了他的一些英国检查官拒绝出版的著作。同样,笛卡尔这位法国哲学开创者的科学和哲学活动差不多全是在荷兰进行的,他曾经在给池朋友巴尔扎克的信中这样写道:“请选择阿姆斯特丹为足下的避难所,……这样完全自由的乐上,在哪个国家能找到呢!”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也到这里作过短期学术访问。甚至在17世纪末,法国哲学家培尔的启蒙活动和政论活动也是在这里展开;最伟大的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洛克亦曾在这里侨居数年,并在这里完成了他最有名的著作《人类理智论》。
1656年7月26日,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的犹太教堂里吹响了一种名叫“沼法”的山羊角,人们带着紧张而沉重的心情聚集到教堂周围,惶恐不安地等待一桩可怕的事件的发生。终于这个时刻来到了,身着黑色法衣的威严不可一世的犹大拉比们来到了大庭中央的讲台,以他们那种阴森可怖的语言,宣判将一位摩西律法的轻蔑者永远逐出教门。当时谁能预料,他们这种残酷而愚昧的判决将在人类历史上永远留下了可耻的一页,而他们所宣判驱逐的离经叛道者将是全世界人民永远怀念和尊敬的伟大哲学家、战斗无神论者和杰出的自由思想战士!
在《神、人及冀幸福简论》里,斯宾诺莎一开始就给出神存在的两种证明方式:第一种是所谓先天的证明:“凡我们清楚而且明晰地知道是属于一个事物本性的东西,那么我们也就能真实地肯定它属于该事物,现在我们能清楚而且明晰地知道存在是属于神的本性,所以(存在属于神,或神必然存在)。”按照斯宾诺莎在注释中的解释,这个论证的大前提是明显正确的,因为所谓一物的本性,“即由于它,事物才成为其事物,同时在没有毁灭孩事物时,它决不会离开该事物,比如,属于山岳的本质的东西就是它应当具有溪谷,或者说,山岳的本质就在于它有漠谷,这是真正永恒的和不变的,并且必须一直包含在山岳的概念里,即使这样的山岳从未存在过,或者现在并不存在”。现在既然我们清楚而且明晰地知道存在是属于神的本性,所以神必然存在。这种把必然存在看成神的无限本性之一、并以此证明神的存在的方式,从形式上看,显然笛卡你的第一个证明的再述,即单独考察神的本性就能知道神必然存在,其典型的论证方式可以用笛卡尔在《哲学原理》里的活来说:“人心在复检其具有的各种观念时,它发现了一个极其主要的观念——一个全知、全能、全善的神的观念。他看到,在这个观念中,不仅含有可能的偶然的存在(如他在他所明白知觉到的其它一切事物的观念中那样),而且含有绝对必然的、永恒的存在。例如在三角形的观念中,必然含有‘三角形三内角等于两直角’这个观念,因此人心就坚决相信,三角形三内角是等于两直角的,现在他既然看到至极完美的神的观念中含有必然的永恒的存在,因此他显然断言,这个至极完美的神就存在着。”很清楚,这种证明实际上就是安瑟伦的本体论证明,不过它采取了更为精致的形式。斯宾诺莎给出的第二种证明就是所谓后天的证明,即“假如人具有神的观念,那么神必然有其形式的存在,现在人具有神的观念,所以(神必然有其形式的存在)”回。这一证明按照斯宾诺莎的解释,是“假如有神的观念,那么这个观念的原因必然有其形式的存在,并且在其自身中包含着该观念客观地所具有的一切”。从形式上看,这个证明也显然是笛卡尔的第二种证明,即从神的观念的客观存在推出其形式存在,其论证的根据就是利用中世纪经院哲学的所谓形式本质和客观本质的理论。斯宾诺莎说:“人的观念的原因并不是他的想象,而是某种使他不得不理解一个事物先于另一个事物的外在原因,这种外在原因不外乎是:由于在人的理智中有其客观本质的事物是形式地存在着,并比其它事物更接近于人。因此,假如人具有神的观念,那么显然神一定是形式地存在着,虽然不是卓越地存在着,因为在神之旁或在神之外没有更真实或更超越的东西。”为了加强这一论证,斯宾诺莎在注释里区分了三类理念,一类观念其本性是矛盾的,因而其对象是不可能存在的,例如一个既是鸟又是马的动物的观念,这种动物是不可能在自然中出现
的;另一类观念其本质虽然是必然的,但其对象却是可能存在的,例如三角形的本质,即三内角之和等于两直角,虽然是必然的,但三角形的存在却不是必然的,而是可能的,也就是说在自然中可能有三角形存在,也可能没有三角形存在;再有一类观念其本质是必然的,而其对象也是必然存在的,斯宾诺莎认为这种观念只能 有一个,这就是神,神的本质和存在都是同样必然的。这里斯宾诺莎似乎比笛卡尔的论证还深入一层,光根据形式本质和客观本质的统一原则,我们可能推出观念的对象的可能存在来,而不能论正该对象必然存在,因此我们还需要分清观念的种类,只有当我们确切地认识到我们的神的观念是属于第三类观念,即其本质是必然的,而其对象的存在也同样是必然的,我们才能证明神必然存在。现在既然我们的神的观念不可能属于第一类和第二类观念,所以我们就能证明神必然存在。不过,如果我们翻看一下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集》里关于上帝存在的几何学证明,斯宾诺莎这一补充显然也是根据笛卡尔的公理十,即“每个东西的观念或概念里都包含着存在性……然而不同的是,在一个有限的东西的概念里,仅仅包含着可能的或偶然的存在性,而在—个至上完满的存在体的概念里,却包含着完满的、必然的存在性。”正是根据这一公理,笛卡尔在他的第—个证明里论证必然存在性是在上帝里。所以我们完全有根据说,斯宾诺莎在《神、人及其幸福简论》里给出的关于神存在的第二个证明基本上是笛卡尔的证明的继续。
由此可见,斯宾诺莎在《神、人及其幸福简论》一书中关于神存在给出的两个证明乃是综合了安瑟伦和笛卡尔的证明,他自己似乎并没有什么新的创造,这里明显反映了他当时仍是处于笛卡尔的强大影响之下,尚未完全建立自己独特的哲学观点。不过,有一点重要区别值得我们注意,即斯宾诺莎这时已明确感觉到了第一种证明即先天的证明比第二种证明即后天的证明更好,并且坚决反对托马斯·阿奎那认为神不能先天被证明的观点,他说:“由上述一切清楚可见:我们既能先天地同时又能后天地证明神的存在。固然,先天的证明更好,因为用后一种方式被证明的种种事物必须通过它们的外因才能得到证明,在这两种方式之中,它显然是不完善的,因为事物不能通过它自身来认识自己,而仅能通过外在的原因。然而,神因为它是万物的第一因,并且也是其自身的原因(自因),故神能通过它自己来认识自己。因此人们无需太注重托马斯·阿奎那的主张,即认为神不能先天地被证明,因为神的确是没有原因的。”
这里蕴涵了斯宾诺莎关于神存在的证明将有一个重大的转折,即他不愿像他以前的哲学家和神学家那样仅外在地证明神的存在,而要内在地、即从神自身来证明神的存在。外在地证明神的存在,只能把神看成是万物的外因,而不能看成万物的内因,同时也可能引导出神是一个超自然的存在的荒唐结论。所以他认为神存在的先天证明“比通常仅依赖于种种外因的后天的证明还更有决定性”。在他看来,托马斯·阿奎那那种后天的证明最多只适合于有限的事物,而不能适用于无限的事物,西为无限的事物的存在是不依赖于任何外因的,其自身就是自身存在的原因,我们根据其自身就足以证明它的存在。正是这种考虑,他发展了“自因”(causa sui)这一概念,认为神既是万物的第一因,同时也是其自身的原因,因此我们通过神自身就足以认识神的存在。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