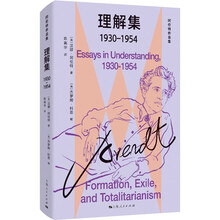应该承认,缺乏明晰性正是早期学说的特点。国家一方面作为没有民族区别的单位,另一方面又作为带着不同利益的不同社会阶级所组成的混合体,换言之,就是国家和社会,在概念上还没有得到明确的区分。但是,在现实里这种差别却在不断扩大;从重商主义时期一直到今天,它们仍旧能够让人们更深切地感受到现实生活的矛盾,尽管还有许许多多理论概念仍旧与霍布斯保持着联系。当代哲学对源于实在的自明性的轻视,主要是在许多现象学流派中产生的,但这仍旧可以在上述问题的背景里加以考察。即使国家与社会已经不再有可能实现真正的统一,人们也得承认这种社会形式是一种原始本质。人们在观念(der Idee)里,总有一种不核证事实就接受“真理”的倾向,一种对源于观念、却又无法提供否定论据的“初步事实”横加蔑视的倾向。当然,我们还得要进一步弄清楚国家与社会的相互差别。社会并不是统一的,它内部有着分化;国家的作用总是取决于在特定情况下它客观上所代表的那个社会群体。
霍布斯明确宣称,专制政体是所有幸福的前提。但他不愿意为能够直截了当地探讨这种政体提供基本依据,这最充分地表现出了他的天真幼稚。然而,他相信专制政体肯定会在自然法的基础上、尤其是在社会契约责任的基础上推断出自己的地位。就本质而言,霍布斯用自然法替代了中世纪的神圣戒律。这种发源于十八世纪近代哲学的要素,竭力通过自然和理性将新的秩序合法化,同时又通过未曾中断过的宗教虔诚将旧的秩序神圣化。这种神圣化不仅对哲学家的听众、而且对哲学家本人来说,都是极为重要的;这不是有意识的苦思冥想所能带来的结果,而是可操作的社会心理机制所带来的结果。贯穿于从霍布斯到启蒙运动时期的哲学争论,其中心问题就是国家制度究竟是由上帝确立的、还是由自然理性确立的。即使后一种假设在当时具有着更进步的意义,但这两种假定实际上都是虚幻的,都没有揭明国家产生的真实原因。以自然法形式和社会契约形式奠定的国家包含着这样一种遮遮掩掩的观点:即国家是人类的自然利益和生命利益的产物。但实际上两种利益并不是相互一致的,而是分散多变的,因而国家也可以从作为一种客观普遍利益的体现转变为特殊利益的体现——这一深刻的洞见最终被契约的神话遮盖掉了。马基雅弗利有关国家形式的变化和腐化、革命既是犯罪又是历史必然的学说,与霍布斯及其后继者论证严密的自然权利的学说相比较起来,显得更加综合一些,协调一些,而后者则忽视了深层社会生活的转变;更有甚者,它在国家哲学理论家的极力鼓吹下,仍旧坚守着国家事务代代永存的信念(这一信念自那时起变得更加强烈)。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