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如此,为了消除“命名”的实指性定义同“使用”的不相干距离,维特根斯坦作了两步论证。第一步指出命名是为了词的使用,或叫做“对词的使用作准备”。第二步指出为了能够问一个事物的名称,我们必须已经知道或能够知道某些事情。只有在已经知道了如何用一个东西来做一些事之后,问它的名字才是有意义的。总之,命名或叫出名称,不仅是使用名称的准备,而且归根到底,命名所以能够命名是已经有物出来照面、相遇、上手,即使用了。
维特根斯坦的这个思路,同海德格尔的语言观、真理观极为亲近,海氏反对传统形而上学的真理定义:认识与本质相符。本质有如帽子盖住的手表,认识只须揭去帽子就能发现手表在那儿自在着,于是认识与本质相符,认识获得了真理性。这种真理观是把真理当作一个先于认识而固有的定在或在者,认识仅仅从本不相干的外面走近它,再伸手握取它。至于各自独立互不同质的东西如何相符、同一,这个为逻辑所不容的致命跳跃如何可能,要么无意识,要么胡编造。海德格尔把这一切叫做人为的迷误。
其实,不同在者本然地就共在于在中,都引源于在的生成可能性,只因其在的空间性而各不相同,因其在的时间性而相互渗透,呈现出是其所不是,不是其所是的复杂局面。尽管如此,首先都是从其在中所在出者,根本不存在先于生成或先于存在的本质。也就是说,在世的共在中,作为人的此在与其他在者相符,那必定以此在与他的在者在世中共同生成、相遇、上手为前提。只有在者在与此在的共在中生成出来、显现出来,然后才有可能相符,才谈得上相符。所谓相符论的真理观应是以生成论的真理观为其本源的。命名亦作如是观。“这是什么”的“是”,已经出示名词的意义纯系由动词引伸归结,即由“是”展现、成形、集结的。
这就是命名的语言游戏同其他使用的语言游戏的原初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命名也是一种使用或使用的准备,因为它们都置根于存在的生成性中。
再反过来,词义可以来自命名的实指性定义,也可以来自各种各样的使用中,能不能因上述的分析进一步得出结论:任何词的词义只存在于该词的使用中呢?当然是正确的使用,因为不正确的使用碰到了钉子,不是别人,正是被使用的语词独立于使用的词义阁下。该词义不容许不属于自己的使用规则。如“邪恶应受惩罚”。“邪恶”是抽象的共相,打屁股的板子打得到它?受惩罚的是“邪恶者”,不是“邪恶”。句子的主词其实是一个表语表达,式:“……是有恶行的……”或“有恶行的……”所以,“邪恶应受惩罚”,其使用规则相对“邪恶”而言,犯了双重的错误,既是似是而非的科学本体论错误(把共相当作实在),又是似是而非的柏拉图主义错误(把共相当作本质)。如果“邪恶”的词义不坚持自身而由人使用,只在使用中取得自己的意义,那么,这一个陈述句就已在哲学史上造成了两千多年的混乱,其共相既实体化了又本质化了。可见,使用决定词义只要成为迷信,混乱立即发生,须知,词项在含义上的确定是相对的,不确定是绝对的,没有一个绝对理想的、惟一正确的划界的方法。词项含义本身就有两类评定证据:一类是可归纳可验证的“事实证据”,一类是非归纳非验证的“标准证据”。只有后者是语法上的约定问题,不是事实上的真假问题,虽然二者各有其独立性,并不相容使用,但是,标准规则最初总受经验的启发,而且事实上,后者常常由前者转化而来。这也证明,词项含义的根源主要不在单纯的语法上的使用规则或语言游戏,而在作为它们背景的此在之在的生成性中。或者说,语言本是生成性的,语言才是在的直接性。海德格尔为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提供了“存在生成论”。
“人是什么?”这个揽天地以自问的千古不衰的老问题,为什么在它的任何一个肯定回答里总是包含着或伴随着“人不是什么”的否定回答,且语调冷漠而怪诞,仿佛舍此不足以表达人的绝望与虚无的根底。
这样的游戏还在进行,像生与死的轮回。尽管理性的逻辑一再强调,否定式不能构成定义,但人们还是在“人不是什么”的否定中发现了某种理性所不愿和不能的存在意义。例如,从理性的道德目的引伸出压抑和屈从,原来理性所伸张的“道德的自我完成”不过是人类的救赎行为由伪装转移而达成的自我欺瞒,特别是在一个“我给,为了你给”的教化社会中。从理性的科学手段引伸出非升华的满足,直到目前为止,科学把人和自然的关系主要变成生产和原料的关系,因此人在自然的必然中获得的自由就只能是一种非升华的满足——自由无非是自愿让必然领着走。这种以必然为绝对内容的自由乃是理性对人的双重遮蔽。所谓人道主义,其实是人对自然的利已主义即人类中心主义,因而人道主义无法根除专制,这才是自然的自然报复,还不用说生态平衡的破坏所造成的更深刻的压抑。所以,人的解放和自然的解放是一个互为中介的过程。换句话说,人的存在必须看护着宇宙万物的自在。
但是,理性需要的是“理一分殊”的统摄,即知其必然的自由。尽管道德目的与科学手段在历史上常常相悖,挑动着人们“各引一端,崇其所善”,然“理性的狡计”也正在这里:世界不管展现出怎样多元的目的得失与手段冲突,只要是现实的,一切手段所导致的非升华满足同时就是这满足的特殊目的的丧失。得即失成为理性的悖论,从而造成了压抑和屈从的潜在倾向。于是,理性的终极目的便永远是高悬着的至善,就象太阳君临于普遍的沉沦之上,然而,沉沦的人哪,太阳与海市蜃楼不都是你心目中理性的饥渴吗?
人类已经习惯于理性的生活了,自亚里士多德把人定义为“理性的动物”以来,谁能说自己没有理性,丧失理性成了不可救药的罪渎。
不管是道德领域,还是科学领域,它们灌注着理性精神无一不是超然终有一死之人的永恒的普遍性,因此才有完善与不朽像生命的十字架立在人的面前。主g阿,除了战战兢兢的赎救、贡奉,哪里有一滴“我的血”!
可惜,人终究是一个被死亡追逐着的怀疑的生物。笛卡尔把怀疑当作理性的逻辑起点,黑格尔把怀疑当作理性自我实现的中介环节。不管他们怎样安顿怀疑,归根结蒂,怀疑是超越理性的理性,即是理性自身终有一死的否定。正是这一致命的否定才使理性不忘返归诞生它的肉体——大地,而成为真正人的理性。可是,理性自欺欺人,它要成为完善小朽的上帝,从而造成对人的存在的遮蔽与遗忘。我所论及的仅是阁下,
如前所述,人的“原初直观”告诉他,除了死是不可逃脱的惟一绝对的在,一切此在都必须从走向的死亡中索取在的意义。然而在的意义在哪儿?理性的完善与不朽在在看来仅仅是对虚妄不实的来世的许诺,像宗教一样。而永恒的普遍性不过是诗所唤出、开启的尺度的尺度化,是对人类生存根基的虚无的一个到底有限而暂时的确定。也就是说,确定者是不确定的。把确定的尺度普遍化已是一个遮蔽,而把普遍化当作朗照四海的澄明之光视若神灵,就更是遮蔽着遮蔽即双重遮蔽了。尽管它是交接着的真理界面,那恰恰是预示着要以拒斥、敞开普遍性的双重遮蔽为前提的。
所以,尼采喊出“上帝死了”,无非是他开始怀疑,理性是人的存在吗?理性能够解释存在的意义、提供存在的根据吗?
罗斯莫,退职牧师,其家族姓氏属本地显贵,举足轻重。
妻碧爱特,传统教化并维护传统的淑女,但有不孕之症。
妻兄克罗尔,本地校长,反对改革、维护传统的代表人物。
吕贝克,由克罗尔引荐的女管家,思想激进,意志坚强。她看出,要想在改革中有所作为,必须争取德高望重的罗斯莫,但要争取罗斯奠,首先又必须打破传统,把罗斯莫从死气沉沉的家庭中解放出来。为此,吕贝克利用碧爱特的不孕,给她有关书籍看,使她意识到自己的不孕乃是对这个传统家族的最大不忠。 同时又让罗斯莫接触自由思想,与之亲密交谈,借此暗示碧爱特,她跟罗斯莫志同道合。一段时间过后,吕贝克突然向碧爱特提出辞职,理由也是暗示性的,即为了不让一件有损罗斯莫及其家族的事态发生,诱使碧爱特作出错误判断,以为吕贝克同罗斯莫有了私情并怀孕在身。碧爱特为了家族的荣誉和传统的继承,跳进车水沟自杀。
剧本就是从碧爱特自杀后开始的。
读完剧本,感觉朦胧。过了许久,偶然看到弗洛伊德的评论,为之震惊,便写了专题笔记如下。
我已经不能忍受弗洛伊德的彻底性了。他抓住了索福克勒斯的《俄底浦斯》,抓住了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又抓住了易卜生的《罗斯莫庄》。他抓住历史,抓住男女,抓住光明,更抓住黑暗。如果他毫无道理,人们尽可以不去理睬,像中国人这样。但是又不,他总有道理,即使“一爪落网”,也会“全身被缚”。理性已经够可怕了,经院哲学的逻辑是可以逃避的吗?透过现象看本质。我看见的正是我能够看见的或需要看见的。你在想什么?你看你的眼神,你看你的手、你的脚?这都是可以用逻辑推导出来的。“人是要死的,张三是人,所以张三是要死的”——一个三段论足以构造出整个世界,乃至“一粒微尘破坏了,整个宇宙都会崩溃”。
于是,人们需要在黑暗中生活,需要在黑暗中性交,在黑暗中做梦,需要一点理性之外的某些东西。可是弗洛伊德却把他的理性之光投射到黑暗中来,性力决定一切——还是一决定一切,这是多么恼人的事,多么恼人的恐惧!
例如,《罗斯莫庄》,使吕贝克最伤心的一点:恰好在人生的幸福快要到手的时候,究竟是她乱佗的历史挡住了她的路,还是现实的手段毁坏了她的目的?
且先耐心看看弗洛伊德的分析。
吕贝克有两次拒绝罗斯莫的求婚。第一次在第二幕。碧爱特的哥哥克罗尔,被罗斯莫公开宣布叛逆宗教传统、主张自由解放的启蒙思想所激怒,决心同吕贝克较量一番,夺回罗斯莫以服从他对抗改革的政治需要。他首先看准罗斯莫的软弱,或不如说深信扎在他身上的传统之根,挑起罗斯莫掩盖在自我欺瞒下的疑团,即碧爱特自杀的真正原因是什么?是她自己的精神错乱,还是别人“把她的精神病激起疯狂症”?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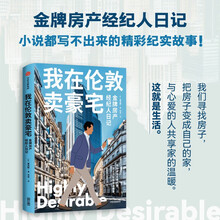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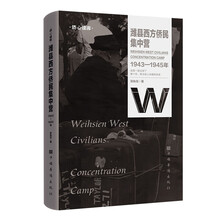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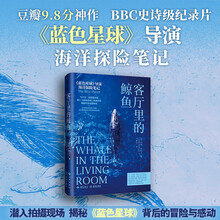
如果在这个充满语言的世界,人们彼此发现了三种面具:“主述者”、“受听者”、“指涉物”,那么,我好像即使在主述的时候也脱不下“受听者”的面具。不,它对我简直就是一种心理残缺,一种令我不堪其扰的奴性。
例如,“我说”,别提我说前的战栗——那真是一种发抖:“我要说了”,“我能说吗”,“我说什么”,“凭什么说”……直到我冲出口,仍是一面抗争地说,一面还恐惧地听:听我说,听我说的言说,听受听者尢言的心声,听世界窒息的沉默或漫不经心的喧哗,听上帝的笑……
更不能忍受的,是听另一个我在一旁本没有什么可说的冷视,
可我还是说了,要说,像是报复,又像是逃匿。
我实在没有这样的奢望……至少在说时没有这样明确的动机……不,我在撒谎,我早就听出我说的那官语,即使不敢自立门户,也紧张得像被追逼的兔子,慌不迭投一家之门,眼巴巴登堂入室,以争一席之地……只是,每每落了空。
别误会,别以为葡萄对我是酸的,我总也够不着,才不得其门而入,别抬举我了。
都怪我的奴性,如果它弱一点,让我只管说去,要在这大千世界的众多门庭中,传一衣钵,俨然大方之家,实在不是难事。
可是我说了,我怎么也摆脱不了听的奴性,而且是那样一种最谦卑的奴性——能听出我的残缺;听出那企图在持存中支撑本体的主体的残缺;甚至听出那试图作为残缺尺度的完满的残缺。有哪一家子门户不在我的听中发现我的缺席?
我无门可入,漂泊无根。
据说,说难免叙事,即使科学的实证,到头来,也终有一叙,否则何以陈述我的发现?我不能枯坐内室重复几个行家听惯了的术语公式,我要面对大庭广众,面对世界历史,于是,总得对我的发现作出事后的陈述,即使以成果的眼光看,略去发现过程中纯属个人的偶然投机,包括个人不得不使用的有限手段,突出强调其史诗般的探寻和必然性的揭示,只有因此而建立了同一性的实体根据,才保证得了个人与国家的权威性,从而沟通世界性的认同基础。
所以,说的叙事性,至少把三个主要特征锲入了意识形态,再说得俏皮一点,锲入了普遍意识的前理解结构。
(1)取时间之后而得逻辑之先;
(2)去偶然的差异性而存必然的同一性,以建立逻辑自明的本体根据;
(3)由此同一性本体转升为权威性价值以昭示天下,认同共识。
好像迄今为止,绝大部分门户虽亭台楼阁有异,但登堂入室的幽径,几乎没有不这么勾连的。
但是,惟命是听——叙事后设的同一性本体是谁许诺的?
时间之后怎么就逻辑之先了?
事实上自休谟以来,时间之后根本就归回不到逻辑之先,这“致命的一跃”是致命的!悬崖下堆满了本体论的残骸:“存在”、“原子”、“理念”、“上帝”、“自我”、“精神”、“意志”、“原欲”、“意识”、“此在”、“语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