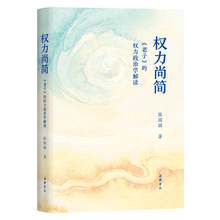其实,先民对于“语言”的思考在所谓的“哲学突破”之前,恐。陷并非如同后世“工具”观点下的看法,而应该具有“神圣性”的性质,正如罗素(B.Russell)在《人类的知识》一书所提的:“语言也像呼吸、血液、性别和闪电等其他带有神秘性质的事物,从人类能够记录思想开始,人们就一直用迷信的眼光来看待它。”罗素的说法表明“语言”在初民的认识中应该分享着那不可测、不可知的伟大力量的性质,这样的观点在许多宗教的经验中,迄今仍然保留着。唐君毅论述古代中国思想的“语言”观时,也注意到有种“咒语”所表现的神秘性质,是具有一些神秘力量。当然,唐先生所谈的“咒语”问题,未必即是本文所论的另一种“语言”观。因为原始语言的神圣性或神秘性的表现形式是纷然而多端的,其主要特征(主体与客体无分)只要能被彰显出来,均可属于原始语言,而未必以咒语的表现方式方可算是。
经由上述的说明,我们可以发现在古代中国的“语言”主张,应该存在着一种颇为特殊的“语言”形态。不过,这种特殊的“语言”形态是否真如唐君毅所言“语言崇拜”的宗教意涵而已呢?其中是否有更多未被抉发的意义呢?以及在哲学突破的理性化浪潮中,这类型的语言观以何种方式保存于后世?或是变形?或是彻底地被抛弃?这些都值得我们深加研究。
当然,从我们将“语言”作为一种“达意”的工具时,便已预设了一个认知主体与认知对象的分别,因为意之被达必先经由我们的感觉能力,行使接物的工作,收摄于主体的统合之后,再命之以某名、-或出之以某言,“意”才有被“达”的可能。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