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决不存在无缘无故的事物。事物之所以能够存在,必有其内在的理由。世界上不可能存在无理之物(“理”即理由)。按照王弼的说法就是:“物无妄然,必由其理”。有些事物固然可以设想,但却不可能存在。因为并不是所有的事物都有其存在的理由,并非一切都是可能的。例如,“永动机”、“方形的圆”之类的“事物”就缺乏内在的理由,从而无法获得自身的存在。或许这正是人们为什么总是喜欢追问事物理由的原因。
人们为什么可以制造一辆汽车,却不可能制造一个永动机?永动机之所以无法被制造出来,就是因为它违背了能量转化与守衡定律,从而不具备存在的内在理由。尽管人类很早以前就对“永动机”感兴趣,且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加以研制,但却始终未能如愿以偿。“永动机”之所以不能被研制出来,其原因不在于研究的不充分,而在于它原本就不具备存在的可能性,即不符合能量转化与守恒定律。人们无法制造“永动机”,但却能够制造出“汽车”以及其他一切可能的能量转化装置,是因为“汽车”及其他一切可能的能量转化装置都符合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从而具备自己的存在理由。由于不符合逻辑规则,“方形的圆”之类也不可能存在。但“方形”的事物和“圆形”的事物却能够存在。因为它们符合逻辑要求。由此可见,一个事物的存在之所以可能,就在于它具有自身的内在理由。
如果说每一个可能的事物作为在者都有其相应的理由,那么一切可能的在者(包括所有“曾在”、“已在”、“正在”和“将在”的事物)所构成的总体何以能够存在?其内在州山何在?换言之,一切可能的“在者”所构成的世界为什么能够存在?它无疑也需要给出一种理由。这同样是一个问题,而且是一个更具始源性和本根性的问题。追问“在者”之“在”,就使我们山“在者”过渡到了“在”本身。
只有“人”才能发出这种“追问”。“人”无疑也是一种“在者”,但却是一个特殊的“在者”。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作为“在者”,人就是“此在”。“此在”的“人”,乃是宇宙中唯一能够追问“在者”之“在”的“在者”,而且他把这种追问本身就当作自身的存在方式。所以,海德格尔说:“对‘在’的领悟本身就是‘亲在’(即Dasein,又译为‘此在’——引者注)的‘在’的规定。这个‘亲在’在‘在者状态’上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乃本体论地‘在’。”在这个意义上,人可以说就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动物;或者说,哲学乃是人的宿命。因为“只消我们存在,我们就总是已经处于形而上学中的”。除非人不复存在,除非人不再是以“人”的方式存在。就此而言,哲学与人的存在之间就发生着一种原罪般的本然的联系。这种联系表明,“人”以“此在”的方式彰显“在”,而非以科学探究的方式诠释“在”。
对此,中国古代的先哲有着同样的领悟。孟子曰:“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庄子也说过:“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哲学家们当然不会天真地相信整个世界的万事万物在实有层上都取决于“我”,而只是说一切可能的在者的存在理由只有通过“我”才能得到澄明。因为只有人才能追问在者之在的问题。以往我们总是把孟子或庄子的这类说法看成是所谓的主观唯心主义,其实这是一种严重的误读。孟子和庄子的说法实际上是想表明只有“我”(即作为“此在”的“人”),才能追问万物存在的理由;换言之,万物存在的理山只能由“我”给出。陆九渊说:“宇宙即吾心,吾心即宇宙”。这当然不是说整个宇宙都装在了“我”的“心脏”里了,因为这里所谓的“心不是一块血肉”。没有哪位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家竟会愚蠢到如此地步。陆九渊的意思只不过是说宇宙万物赖以存在的内在理由因“吾心”才得以彰显、才得以澄明。陆九渊说得很清楚:“万物森然于方寸之中,满心而发,充塞宇宙,无非此理。”王阳明说:“盖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其发窍之最精处,是人心一点灵明。”按《传习录》的记载,“先生曰:‘你看这个天地中间,甚么是天地的心?’对曰:‘尝闻人是天地的心。’曰:‘人又甚么叫做心?’对曰:‘只是一个灵明。可知充天塞地中间,只有这个灵明。人只为形体自间隔了。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天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仰他高?地没有我的灵明,谁支俯他深?鬼神没有我的灵明,谁去辨他吉凶灾祥?天地鬼神
万物离却我的娄明,便没有天地鬼神万物了。我的灵明离却天地鬼神万物,亦没有我的灵明。如此便是一气流通的,如何与他间隔得?’又问:‘天地鬼神万物千古见在,何没了我的灵明,便俱无了?’曰:‘今看死的人,他这些精灵游散了,他的天地万物尚在何处?”’显然,中国先哲的思想同海德格尔的是完全相通和默契的。在海德格尔看来,此在以其在着的方式昭示和召唤着在者,从而使在者之在得以澄明;或者毋宁说此在之在本身乃是在者之在的敞开和彰显。
佛教中有所谓“有宗”与“空宗”之分野。这一分野意味着什么?熊十力先生曰:“佛家宗派虽多,总其大别,不外空有两轮。诸小宗谈空者纷然矣,至龙树、提婆谈空究竟,是为大乘空宗。诸小宗谈有者纷然矣,至无着、世亲谈有善巧,是为大乘有宗”。熊十力先生认为,在对待“空”的问题上;有两种偏颇:“凡情迷执万有皆实,而不悟空(凡者,凡俗)。少数智人或观—切皆空,复堕空见”。执着于万物之表象,而无法领悟超越万物之实有层的无规定性者,属于“不悟空”。它没有达到由“有”向“空”的提升。如果仅仅是进入“空”之境界,却不能复归于“有”者,即是所谓“堕空见”,亦即堕入“顽空”和“断灭空”。如果说“不悟空”滞留于“正题”,那么?堕空见”则只是满足于“反题”,它们都没有达到“合题”’从而未能进人哲学的至境。正如熊氏所说:“本无有众生缘实用而构画的种种物,如瓶、如山、如马等等相(相者,相状),故应说牢(瓶与山、马等等物相本来无有,故说空)。然复须知,瓶、山、马等等相虽空,毕竟不可说宇宙只是空空洞洞无所有。宇宙实相恒自尔故(尔,犹然也。言宇宙实相恒自保任其本然之相而独存),故应说有”。因此,这就需要两重工夫:“证有,则廓然任真(人生发扬其天然之真性,无有迷妄,曰任真),悟空,则荡然无执(执者,迷惑坚执,如蚕作茧自锢也。无执,即大解脱),人生与大宇宙浑然为一矣”。显然,只有借助于“悟空”和“证有”这两重工夫和两个步骤,才能够最终完成哲学境界的建构和开显。
关于“空”与“无”之不同,成中英认为:“若撇开‘空’与‘无’两字的同义部分不谈,玄学与佛学之最大不同乃在:‘无’为本源,为发生之起点;‘空’则为本体所显之实相。谈‘无’不能离‘化’,谈‘空’则不能离‘缘起’。‘化’与‘缘起’乃是根本不同之观念。”究竟应当如何恰当地看待“无”与“空”的异同呢?其实,如果从细微处着眼固然可以辨别出许多差异,但是如果从大处着眼,就应当观其大同处,这样才能有助于洞察出实质所在和问题的究竟。佛教在中国化过程中的“格义”就把“空”与“无”作等价的诠解,尽管其中有牵强处,但毕竟为我们融会佛道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清初学者颜元在《四存编》中对佛老进行抨击:“佛不能使天五日月,不能使地无山川,不能使人无耳目,安在其能空乎?道不能使日月不照临,不能使山川不流峙,不能使耳目不视听,安在其能静乎?”其实,颜元的这种诘难并不具有挑战性。因为它实际上是把佛老所谓的“空”、“无”作了一种直观的理解,把它们看作实有层上的规定了。形而上学只是一种境界而已。从一定意义上说,它并不改变事物的外观,而仅仅是改变人们看待事物的方式。
佛教哲学中关于“有”与“空”的思想是认识论吗?吕潋先生认为:“释迦学说没有接触到本体论”。印度学者谭中也认为:“佛家关于‘有’、‘空’、‘非有’、‘非空’的讨论是一种分析矛盾的认识论。这种认识论本身就是对宇宙人类的观察和解释”。这种观点未能揭示出佛教及其“空”“有”之辩的本体论性质,因此是不确的。因为不沿着本体论的立场和角度去领会,就根本无法把握“空”“有”之辩的真谛。吕澈先生之所以得出他的结论,或许是由于他对本体论所作的独特理解所致,但谭中明确把佛学的“空’’“有”之辩说成是认识论,就明显不妥了。
《坛经》曰:“何名‘摩诃’?‘摩诃’者是‘大’。心量广大,犹如虚空,若空心坐,即落无记空。虚空能含日月星辰、大地山河、一切草木、恶人善人、恶法善法、天堂地狱,尽在空中;世人性空,亦复如是”。郭朋先生认为,“世人性空”中所谓的“性空”,与般若“性空”含义不同。他认为般若“性空”是一种全称否定:无论是此岸之“妄”或彼岸之“真”,“一切皆空”——自“性”本“空”,谓之“性空”。而这里(以及整个禅宗)所谓“性空”,则只是一种特称否定:只“空”虚妄,不“空”真实——真如、佛性。真如、佛性(“本性”、“自性”),则是“真有”,而不是“空”。真“性”无妄,谓之“性空”。在逻辑范畴
上,决不可混淆般若与禅宗的根本区别。其实,郭朋先生过分拘泥于二者的差别,而忽视了它们在义理上的深层相通。即使从《坛经》的这段文字看,慧能所谓的“空”本身就是“真如”,就是“佛性”。它相当于黑格尔所说的“无”。黑格尔在淡到东方哲学的时候曾纤指出:“在道家以及中国的佛教徒看来,绝对的原则,一切事物的起源、最后者、最高者乃是‘无’……。而这本来不过是说,统一在这里是完全无规定的,是自在之有,因此表现在‘无’的方式里。这种‘无’并不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无或无物,而乃是被认作远离一切观念、一切对象,——也就是单纯的、自身统一的、无规定的、抽象的统一。因此这‘无’同时也是肯定的;这就是我们所叫做的本质。”他还指出:“那起源的东西事实上是‘无’。但‘无’如果不扬弃一切规定,它就没有意义。”显然,慧能所谓的“虚空”,是没有任何特定规定性的,因此它才能包含一切可能的规定性,正因此它才能消解和超越一切有关真假、善恶、美丑之间的相对性,而展开为绝对。
作为整个人类文化的母体,原始文化带有明显的总体性质。原始文化是高度融合的,它表现为一种直接的同一性。也就是说真善美直接融为一体,并通过文化成员的个体表现出来。这就意味着,在人类文化的早期阶段,人是全面发展的。例如,澳大利亚内陆沙漠干旱地带及约克半岛上的土著居民不仅具有必要的生存能力,而且有着复杂的社会组织。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他们都具有丰富的想象力和艺术表现能力,几乎人人都能绘画雕刻。原始文化的总体性及其在人的个体上的表现,构成了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的文化人类学根据。因为马克思的社会理想就是人的本质在更高的历史基础上的复归。当然,这种复归不是在原有基础上的重复,而是经过否定之否定而实现的扬弃。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早期阶段,“单个人显得比较全面”,这是人的本质的“原始的丰富”。
原始宗教作为一个“全息元”,浓缩并积淀着整个文化系统的全部信息,是文化总体的一个缩影;而文化的每一层面、每一部分也无不具有浓厚的宗教意味。在原始文化尚以直接同一性的方式存在并表现自身的总体性质之时,宗教是一咱涵盖并希奇漫于整个文化系统的内在要素。当原始宗教(自发宗教)闪它所代表的文化系统解体而蜕变为人为宗教之后,它便不再承担文化整合的功能,而是变成与其他文化形态并列和对等的一种特殊的和狭义的文化形态。人为宗教只是担当着文化中的信仰功能。从生命史的演化历史看,从生命的发生到生命的发展,直到人类的诞生,都是一系列分化的结果。恩格斯指出,在生命演化的早期阶段,“完全没有结构的蛋白质执行着生命的一切主要机能:消化、排泄、运动、收缩、对刺激的反应、繁殖”等等。而“人也是由分化产生的。不仅从个体方面来说是如此——从一个单独的卵细胞分化为自然界所产生的最复杂的有机体,而且从历史方面来说也是如此”。其实,原始宗教就像恩格斯所说的这种“完全没有结构的蛋白质”。那么,人类文化的发生和发展也在某种意义上重演着这样一个过程。它也是通过一系列的分化来实现的。正如“性”本身是分化的产物一样,基于“性”而衍生的人类文化的发展又在次生态的意义上重演了这一分化过程。后来人的原始创造力所固有的发散的性质,内在地要求文化沿着不同的方向、不同的进路展开自身。由于创造乃是从“无”到“有”的“生成”(becoming),它必然以多元取向为其本质特征。文化分工(我把真、善、美之间的分野称做“文化分工”)的发达,使真善美不同维度逐步职能化、部门化,为人们的职业化、专业化提供了可能。这也是文化有机体走向成熟的不可避免的过程,是文化成熟的重要标志和表现。从历史上看,这一过程主要表现为文化母体的解体和升华,即发散和收敛之间的两极互动及其所形成的必要张力对文化发展的推进。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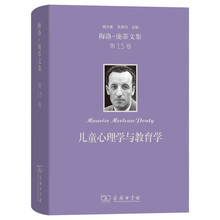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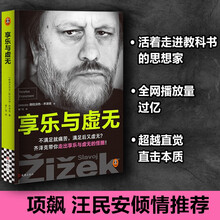


谁要是想让哲学家出丑,最有效的办法莫过于问他“什么是哲学”这个问题了。的确,这大概是哲学上的一个最难回答的问题。当然,人们可以很容易地从哲学词典或哲学教科书上找出有关“哲学”的定义和界说,但当你对哲学有了相当深入的了解和领悟之后,就会感到在这个问题上最好是保持沉默。因为你一旦进入哲学,就会发现它原本是无法谈论的,正如老子所言:“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①维特根斯坦也说过:“对于不可说的东西我们必须保持沉默。”②然而,古今中外的哲学家仍然在那里喋喋不休地大谈何为哲学,这是不是缺乏智慧的表现呢?是不是徒劳无益的呢?当然不是。因为哲学的全部尴尬集中到一点,就是必
须“说”“不可说”。倘若考虑到这一点,我似乎就有了一种“谈论”“哲学”的勇气。它足以使我在进入哲学话题的时候,能够获得某种自我辩护,从而变得心安理得。
严格地说,哲学不是一种知识。尽管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指出若干“哲学知识”,如哲学家们所说的那些东西,以及历史上哲学思想的积累等等。但从根本上说,哲学是不能够被当作一种“知识”来“看待”和“学习”的。因为在一定意义上,哲学不过是一种运思方式而已。据说康德当年就曾告诫他的听众:学生应该学的只是去进行哲学式的思考。就此而言,哲学是“做”而非“说”。因此,哲学是既不能“教”也无法“学”的,它只能参与,亦即在参与“思”的历程中领悟“思”的方式本身。雅斯贝尔斯说得好:“哲学是不能教的,只能靠自身的悟性去参悟人生与世界。”这实际上意味着哲学不能或不应被设置成一个对象性的规定,然后以一种知识论的态度去对其进行把握和揭示。因此,我的这本谈论“哲学”的书,必须时刻保持高度的警惕,以免对于哲学采取一种纯粹“旁观者”的姿态。
麻烦的是,从历史上看,有汗牛充栋的哲学著作,有为数不少的哲学家,而无论是著作还是哲学家个人,都不是一种抽象的符号,而是具体的存在,是一个社会学事实。而且哲学的确也对社会生活和历史进程发生着或多或少的实际影响。这就使得我们有可能捕捉到哲学在长时段中表达出来的效果历史。既然如此,那么哲学作为一种社会事实和社会建制,的确有其可被旁观的可能性。从这个角度说,哲学又能够而且应该被设置为一个对象,供我们去描述,去谈论,去研究。我们可以“禅外说禅”式地对它加以解释和把握。只是我们在这样做的同时需要自觉地意识到这种外在性质,因为这样才能足以避免对于哲学的内省式领悟的妨碍和伤害。
按照以上分析,我们发现,对于哲学就有理由分别从“内”与“外”两个方面着眼进行把握。从外在的方面说,哲学可以被作为一个事实.例如有那么些被称为哲学家的人所从事的沉思默想的活动、他们写的被叫做哲学著作的书、他们的思想对社会生活发生的实际影响及其客观后果……等等。从内在的方面说,哲学又是无法通过旁观而被捕捉到的,它只有通过人们进入它的内部,才能被领悟和体会。因此,本书打算一方面通过实际的哲学思考本身来内在地昭示出哲学的合法性及哲学如何可能,另一方面则通过对象性的描述和诠释来外在地揭示出哲学作为社会事实和文化事实所具有的存在方式及其特征。这两个方面应当形成一种互补的关系,以便共同凸显“哲学究竟是什么”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