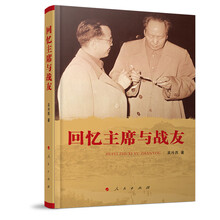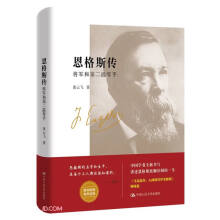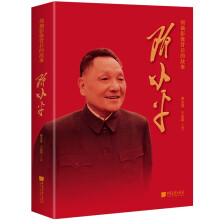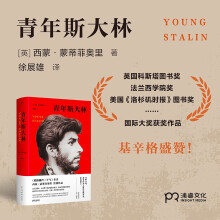毛泽东是一座渡桥,他连接着此岸与彼岸,这边与那边。
毛泽东是一面镜子,他映照出了千姿百态的形象和图案。
时间是一个奇妙无穷的放大镜,一个生前伟大的人,死后不仅更加伟大,而且对于每一个活着的人都构成一种影像。
背影,一个伟岸、厚重的背影,别离人们而去,渐行渐远。
灵魂,一个崇高、神秘的灵魂,在中华大地之上,在人们心灵的天空上徘徊,回旋,飘扬……
于是,人们带着各自不同的视角和心态,呼唤、寻觅毛泽东,渴望重新打量和解读毛泽东。
完全可以这么说:毛泽东即使平生连一首诗也没有写过,也定然是一个深层意义上的大诗人,因为他的生命历程即是一首回肠荡气、千古风流的好诗、大诗。
细究起来,诗不能算作是毛泽东的生命,也不是他赖以存在的生活方式。然而,毛泽东是那种用生命来写诗的大诗人,诗是联结着他个人生命历程的一个不容忽略的纽带。
是的,毛泽东是用心血与生命写诗的人。在所有的诗人之中,只有这样的诗人才可以被称为真正的诗人,才有可能成为伟大的诗人,才能得到人们最高的景仰。
写诗作词是毛泽东个人的一种生命状态,这种生命状态呈现着灿烂辉煌的光影,就从他留存于世的诗词上看,无论是思想境界,还是其达到的艺术成就,都是令人叹为观止的。
人们有理由这么说:毛泽东的诗词绝大部分是杰作,脍炙人口,万人咏唱,如黄钟大吕,震撼着人们的心灵,回荡于诗界的天空,这无论是从中国诗史以及文学史,还是从当代世界文学史上看,都是一种相当罕见的文学景观。
毛泽东的诗词必然地成为中华民族文学宝库中无可替代的珍品,占据着一席特殊的位置。
大家知道,与爱好风雅作诗的乾隆皇帝的“一万多首”诗相比,毛泽东的诗并不为多,但乾隆的诗几乎一首也没能广为流传,而毛泽东那近百首诗却万人传诵,流传海内外。
诗,贵在精,而不在多。
毛泽东之所以被人们称为一个伟大的诗人,并不仅仅是他个人在政治、思想上的地位所衬托、所决定的,而是基于他写下了那么多首精美绝伦的辉煌诗篇。
高位只能显赫一时,好诗才能流芳百世。
对于毛泽东这个极富于创造性的伟大诗人来说,写诗并不单单是一种诗性的冲动,也不仅仅是由于兴趣和爱好,而是他的生命状态,是与他的革命生涯相随相伴的一种形影,即革命实践的行为方式。在这里,诗歌不是艺术创作的一个分支,而是构成毛泽东个人生命的有机材料。
毛泽东在漫漫人生旅途中,始终都与诗作伴。在他一生的各个重要阶段,或于转战千里的马背上,或于千里冰封的雪原上,或于咆哮翻腾的江海边,或于风口浪尖的历史关头,毛泽东都用饱满的生命和如椽的大笔下了不朽的诗篇。他给人世间留下的一首首诗词,犹如一排排战国编钟,铸录着血与火、剑戟与旗帜、风雨与云烟、暗夜与光明交织的历史……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的诗与他个人的生命,与民族的命运,与革命者的道路,都是联系在一起的。正如美国人特里尔先生所认为的那样,毛泽东的诗词不仅代表了毛泽东本人,也代表了中国。
用心血与生命去写诗,诗所写下的是一种民族和个人生命的历程,这是诗人毛泽东及其诗作的一种鲜明的特色。
人写诗的时候,诗也在写入。我们也应该如此去看毛泽东这个伟大的诗人和他那光辉灿烂的诗篇。
历史可以作证,杨开慧是毛泽东真正挚爱也永生难忘的一个了不起的女性。杨开慧英勇就义后,毛泽东痛惜不已,哀悼说“开慧之死,百身莫赎”。(他和后来的妻子贺子珍则是一种更加革命化的战斗情谊,他从未给贺子珍写过一首诗词。至于和江青的故事,毛泽东则自认为是个人感情生活上的一个莫大的失误。为此,毛泽东长久地后悔而无奈。虽然他给李进—江青写过一首诗《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但那只是毛泽东的一种自画像,而不见两人之间的情感踪影)直到1957年,他还为友人李淑一写下了一首流传更为广泛的怀念爱妻杨开慧的词—“蝶恋花”,这首以浪漫主义的神话幻想色彩为基调的“悼亡”词,既是怀念自己的爱妻“骄杨”,又是对亲友英灵的安慰。这里,诗人毛泽东没有像唐明皇那样“升天入地求之遍。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地寻寻觅觅,而是将自己对爱人的怀念思恋凝成这么一句话“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
实质上,这充分寄托了诗人对爱人最深、最高的爱意和敬意。至于“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不是直跨时空、生死界限告诉亡妻,此时可以“重比翼,和云翥”了吗?杨开慧泉下有知,一定会为有毛泽东这样的盖世英雄、这样情深如海的丈夫而欣慰的。
毛泽东对杨开慧的情感是十分深厚而且绵长的。杨开慧生前,他挚爱着她;杨开慧死后,他一直怀念着她。毛泽东对杨开慧的那种特殊的情感与怀念,老而弥笃,愈来愈浓。而他怀念她的一个显著方式,就是时常吟诵、修改为她而作的这首《贺新郎》,并且多次抄录它以赠亲友,寄寓自己的情感。
关于这种“此恨绵绵无绝期”的情感,毛泽东自己曾这样说:“人对自己……过去的伴侣,感情总是很深的,很难忘的,到老年就更容易回忆、怀念这些”。(引自《在毛主席身边读书》,见1978年12月2日《光明日报》)所以,他在1961年写的《答友人》一诗中以描绘身披红霞的帝子形象,寄寓了自己对杨开慧的深切怀念之情。
毛泽东对爱妻杨开慧的深情挚爱己成为流传人世间的爱情佳话,而诗人毛泽东为杨开慧写下的儿首诗词更成为爱情诗中的绝唱。
纵观毛泽东诗词,可以鲜明地感受到,他的诗具有如高山似江河的气势,而诗人毛泽东的形象也如山一样地坚定挺拔,巍然雄壮,如大海一样气象万千,奔放不羁。
“山”“河”的气象,就是毛泽东诗词的气象;诗人毛泽东的形象,就是山河的形象。
当然,从诗人毛泽东的个人生命和艺术创作之中可以看出,他对“山”“水”爱恋得太深,太专注了,其中甚至有着某种或隐或显的自恋倾向。 而自恋,应该看作是诗人的一种自然现象。其实“自恋”也并没有什么不好,只是要看这个“你”值不值得自恋了。
有时候自恋也是一种大自信、大自知。没有自恋也就没有自信,没有自信就不可能有“自我”,就没有这个大写的“我”—诗人毛泽东。
而且,从一个人所爱恋的对象上,就可以窥探出他的形象和精神世界来,不是这样么?
恬淡隐逸的陶渊明爱“菊”;
孤高遁世的林和靖喜“梅”;
狂放不羁的李太白诗中常有“酒”;
杀敌抗金的辛弃疾的词里多有“剑”光……
而诗人毛泽东爱“山”,恋“水:,写“山”,状“水”,这不是一种偶然涉笔为之。当今天的人们和下一代、下下代的人们,读念毛泽东的这些“山水诗”的时候,眼前和心中能不耸立起一个如高山大河一样令人崇敬和赞美的形象么?
诗人毛泽东—一个“挥手从兹去”的“江湖客”,一个“别梦依稀”望家乡的大地漫游者。
“家”与“乡”,无论对谁来说都是令人心情激动的词语,不管你是从哪种角度和心态上来理解它们,体味它们。
对于情感丰富而复杂、人情味浓重的诗人毛泽东来说,“家”与“乡”更是一种令他惆怅难言的所在和象征。
毛泽东作为一个大地卜的漫游者,一个浪漫主义诗人,一个职业革命家,似乎一直都没有为自己“构筑”一个完整的、安稳的“家”,“乡关”又是别离经年,一去而难返。在他那永无安歇的生命征程中,“家”与“乡”的位置表面上是排不上号的,虽然他也有自己的妻子儿女。可在他那颗坚强而柔韧的心灵里,何尝不是也像常人一样渴望“家”的温热、“乡”的真实呢?
然而,为了他心中的那个“家”,那个更大的“家”,毛泽东却毅然离家别乡,投身革命即为家了。
最后,他找到了自己心中的那个“家”了么?
有家而不安居,寻求另外一种意义上的家园,这不是诗人的心理事实和生命行为么?
应该说,诗人毛泽东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离家出走者”。与此同时,也是一个更高层次上的梦家望乡者。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