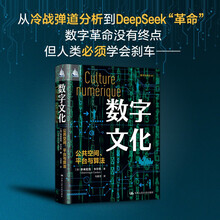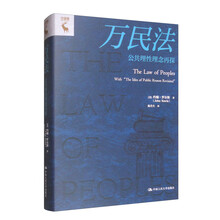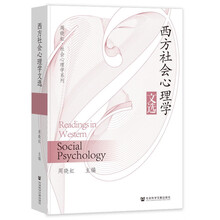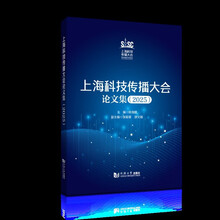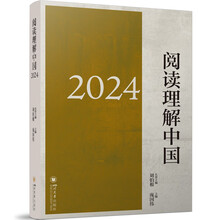回忆与期待:上山随想
蒋乐平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跨湖桥文化和上山文化主要发现者、发掘者。
考古人书写历史的自豪感是由衷的。有句话通俗易懂:一部人类历史,百分之九十九是由考古人写就。
对于无限追求精神生活的人类而言,时间无疑是生存维度中的重要一维。推开历史的窗口向远古凝视,恰如登上礁石眺望无垠大海,那是思想放飞所需要的空间。
上山遗址发现于浦阳江流域的考古专题调查中。故事要从2000年9月21日说起。
那天,我乘坐从诸暨开往浦江的公交车,在浦郑公路一个叫李源的地方下车,与时任浦江县博物馆馆长芮顺淦会合。之前,芮顺淦在电话中介绍了□(特殊字)塘山背遗址的位置,我们相约于此。步行约一千五百米,我们来到黄宅镇渠南村。
村南头的道路边立着一块“□(特殊字)塘山背新石器时代遗址”保护石碑。我第一次见识这个奇怪的“□(特殊字)”字——字典上找不到,浦江乡音近“括”,意为“不直”。村子中间,有几个水塘,弯弯曲曲,似连非连,因称“□(特殊字)塘”。
在地图上查看,这里正处在一个地瓜状小盆地的中心位置。浦阳江发源于西境的天灵岩,在龙门山脉的北山和南山之间从西南向东北穿过,沿途有大小支流汇入,形成半封闭的浦江盆地。盆地之中分布着一些低矮起伏的土丘。这些土丘由下蜀黄土、网纹红土堆积而成,属风成土,在数万年前的晚更新世,由遥远的黄土高原“吹”到这里。随着全新世的到来,不断升高的气温融化了龙门山脉的冰雪。冲决而出的溪流,在不断冲刷两岸土地的同时,也重塑了浦江盆地的地貌。因水土下切而彼此分割的土丘,造就了地质学家眼中的二级台地。冠名为“宅”的一个个大小村落,就坐落在这些二级台地上。恣肆于台地两侧的大小溪流,在无约束的泛滥改道和人类的活动过程中,大多废湮淤塞。□(特殊字)塘,正是这一变迁中的遗迹。
考古调查从□(特殊字)塘开始,可谓找准了历史的脉络。正是这条行将消失的古河道,引导我们走向了上山的万年之路。
2000年9月22日,我带着技工张海真和胡少波正式进驻渠南村。在浦江县博物馆老方的协调下,住在村支书周求水家。工作的第一步,是在遗址保护碑南侧的葡萄园进行探掘,但并未有所发现。第二个试掘坑转移到村口的道路边,我们终于发现了文化层。出土陶片虽然十分破碎,但还是能够辨认出鱼鳍形鼎足,具有良渚文化特征。由于遗址被村庄所占,没有进一步工作的余地,对这一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原定位置的调查也告结束。接着,考古调查队按既定的方案,在遗址的周边展开调查。
□(特殊字)塘的西边有一群为耕地的土丘,约四五亩,高出周边的水田一米多。时值秋季,土丘上生长着油菜、萝卜、甘蔗、番薯、荞麦等植物。我们向村民赔偿了青苗费,就在中部位置布了一个一平方米的小探坑。
两天后,张海真打来电话,告知在探坑里发现了一件完整的陶鼎。我怀疑有墓葬,就赶紧从诸暨赶到现场。经过小心清理,除陶鼎外,我们又陆续发现了陶罐、陶豆等器物,均具有良渚文化特征。由于探坑太小,我们无法确定墓葬的边界,就当即进行扩方发掘,终于确认了一座长方形的墓穴。
这一发现让人又惊又喜:区区一平方米范围内居然“网”到了一座墓葬,是否表明这里存在着一个密集的埋葬区?当时浙江考古界对良渚文化的范围是否过钱塘江尚有争论,如果在这里找到了良渚文化时期的墓地,不就可以有助于解答这个问题?
这可是个重要发现!
一时间,我把考古调查队主要人马都调到了□(特殊字)塘山背,扩大面积探掘,不久又发现了十座墓葬,确定这里有一个良渚文化时期的墓地。从分布看,遗址区在□(特殊字)塘的东边,墓葬区在□(特殊字)塘的西边。如果这就是当初的布局,那么,□(特殊字)塘所属的古河道,至少在距今四千年前就已经存在。良渚时期的先民们临水而居,将墓地营筑在水的另一方,呈现一种有特色的聚落模式。
墓地的发现让我们信心大增。由于类似土丘在周边还有分布,我们决定扩大调查范围。第一目标即村庄北部的一个土丘。 在土丘西侧,我们简单布了一个小探坑,居然又挖到了新石器文化遗存。2000年11月15日,负责探掘的郑建明在探坑里将一片夹炭红衣陶片递给我看,陶片特征与□(特殊字)塘山背随葬陶器完全不同,勉强可以与同样存在夹炭陶器的河姆渡文化相比较。遗址的年代,也就暂定为距今六七千年。
日记里,我一度将这个遗址称为“山背遗址”。后来明白靠近遗址的自然村不是山背村,才觉不妥——这就是后来改名的“上山遗址”。
P2-5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