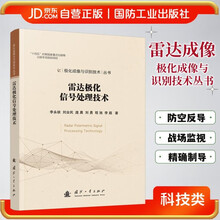第1章绪论
在外界条件(如温度、压强、电磁场等)作用下,物质可呈现出不同的原子(分子)结合状态、不同的结构形式(如晶体结构)、不同的化学成分,并表现出不同的力学性能、物理和化学性质。当外界条件发生变化时,物相之间会发生转变,该过程即为相变。相变过程既博大到系统内、晶粒间的宏观输运,又细微至界面处、原子/分子间的跃迁,属于典型的宏–微观多尺度问题[1]。相变调控决定金属材料的组织和性能,热力学和动力学是指导相变调控的关键理论。因此,相变热–动力学旨在利用非平衡态热力学实现“将热力学应用于非平衡动力学过程”的目标,属于从普适性角度来研究宏观过程的共性。
相变包括扩散型和切变型,即原子的长程和短程运动,甚至是小于一个原子间距的整体位移;金属材料的变形大多涉及位错或孪生,是原子在层面间几个原子间距或小于一个原子间距的切变[2]。可见,相变和变形属于不同级别的原子运动,可统一为热力学驱动力驱动下的动力学行为。变形中的位错热–动力学表明,流变应力的提高对应位错自由运动能垒的降低,也就是说,加工硬化中位错所承受局部载荷的提高导致其继续开动所需的驱动力增大,体现为强度或流变应力的提高;与此同时,位错自由运动能垒降低导致位错密度快速增加,林位错增多,位错进一步演化的阻碍增强,*终体现为塑性较小时材料断裂。这就是位错理论框架下金属材料强度和塑性的“互斥”现象。本书认为,强塑性互斥源于热–动力学的协同或热–动力学互斥,因此可通过设计形成微观组织的加工过程来实现微观组织变形时强塑性的定量设计。
根据塑性变形中的**位错理论,微观组织决定力学性能。通常,强度和塑性满足如下关系: σε = αGb2ρ1/2ρml (1-1)
式中,σ为流变应力,随位错密度提升满足σ = MαGbρ1/2[3],M为泰勒系数;G为剪切模量;b为Burgers矢量;ρ为总体位错密度;ε为塑性应变,随可动位错密度变化满足ε =ρmbl/M[4];ρm为可动位错密度;l为位错平均自由程;α为与σ相关的经验常数。
宏观力学性能的强塑性互斥是否反映位错演化的热–动力学协同,也就是说,体现大强度–大塑性组合的位错演化是否对应大热力学驱动力–大动力学能垒组合的相变,这一问题值得深入思考。为了回答上述问题,*先,需要澄清如何定义即ΔG和Q,两者依赖于相变调控必需的热力学和动力学,并且决定相变/变形的发生与发展。其次,需要阐明热力学稳定性的概念,即相变突破基体的结构稳定性而决定微观组织,位错突破基体的机械稳定性而反映强塑性。迄今为止,热力学和动力学,相变、变形和热力学稳定性,这些概念被人为割裂并相对*立地进行研究,将其集成的科学意义和潜在应用被忽视,这从根本上源自对热–动力学协同概念的认知不足。
简单近平衡条件下,传统理论认为热力学和动力学相对*立。为适应现代工业生产高效率、高性能要求,工艺趋于复杂化和极端化,导致热–动力学相互关联。因此,基于热–动力学相对*立的传统理论已无法处理复杂非平衡相变。为开展复杂非平衡条件下的精确相变调控,必须阐明热–动力学的协同或耦合作用[5-9]。例如,钢铁热机械加工过程(thermo-mechanical control process, TMCP)中,通过变形量和析出相的协同,可在增大再结晶驱动力的同时提高晶粒长大的动力学能垒,进而优化晶粒细化效果[10-13];铝合金薄板连铸所产生的非平衡凝固效应(即大热力学驱动力–小动力学能垒组合)会贯通至后续固态相变,进而提高固溶与时效的效率[14];激光3D打印近共晶Al-Si合金中*特的亚稳胞状组织便是扩散控制生长机制(即小热力学驱动力–大动力学能垒组合)向碰撞控制生长机制(即大热力学驱动力–小动力学能垒组合)转变的必然结果[15]。
根据热–动力学协同的基本理念[5-8],稳定性堪称联系热力学驱动力和后续形核/生长的枢纽。热力学驱动力突破稳定性后,紧接着便是相应的形核/生长动力学机制。随着相变进行,“热力学驱动力-稳定性-形核/生长动力学”这一链条循环重复,直到相变结束。那么,相变如何结束?稳定性的不同体现于不同热力学驱动力下的相或结构竞争,形核/生长体现于动力学机制的选择,相变演化则体现于转变过程中热力学驱动力的变化及相应形核/生长动力学机制的综合贡献,这就是所谓的“热–动力学多样性”。热力学第二定律衍生出的“普里高津”学派认为,体系总是趋于尽可能快地耗散其自由能而结束相变的旅程。世间万物,要么尽可能快地趋于更稳定,要么尽可能快地走向更不稳定。快如前者,如第二相析出和晶粒长大,“小驱动力–大能垒”是梦寐以求的佳境;快如后者,如马氏体相变和块体转变,“大驱动力–小能垒”是屡试不爽的结果。为了更稳定,可以选择小驱动力–大能垒;为了更不稳定或者为了获得亚稳相,可以选择大驱动力–小能垒,这就是所谓的“热–动力学相关性”。相关性从相变贯通至塑性变形中则演生出“强塑性互斥”的基本规律,引出所谓的“热–动力学贯通性”。
图1-1给出了本书的主要内容及其相关性。第2章旨在阐述控制一阶相变的热力学和动力学基础理论,即不可逆热力学基础[1,15-18]、统计理论基础[19,20],以及形核、生长、界面过程的热力学和动力学基础[21-23]。在此基础上,针对金属材料加工过程中常见的非平衡凝固和固态相变,对其热力学状态和动力学过程进行建模,定义相变热–动力学的研究范畴及其特点:相变中热力学驱动力和动力学能垒各自的变化,即热–动力学多样性(diversity of thermodynamics and kinetics, thermo-kinetic diversity);热力学驱动力和动力学能垒的关联,即热–动力学相关性(correlation between thermodynamics and kinetics, thermo-kinetic correlation),以及连续相变或变形间的热–动力学贯通性(connectivity of thermodynamics and kinetics, thermo-kinetic connectivity)。
图1-1本书主要内容及其相关性
第3章旨在阐明热–动力学多样性。一方面,热–动力学多样性紧密连接不同非平衡条件下相变产物的尺寸、结构和形态选择的稳定性;另一方面,热–动力学多样性涉及形核和生长的热力学驱动力和动力学能垒,以及形核和生长模式。为了展示热–动力学多样性,业界开展了大量实验和理论研究[24-43],这也引出一个普遍问题:面向目标设计,什么样的热–动力学组合是相变的本征行为。
为回答上述问题,第4章阐明相变和变形中本征存在的热力学驱动力和动力学能垒呈现互斥的热–动力学相关性。当前,几乎所有的材料设计研究均在于挖掘相变热力学、动力学同微观组织的定性关联,以期实现面向目标组织的成分和工艺设计。如果上述关联可以被数学解析化展示,此间的热–动力学相关性就可以被定量展示,定量设计材料也就可以实现。基于此,业界开展了借助加工参量同相 变热–动力学函数间定量关联的相变调控,这直接产生了具体应用中,基于大热力学驱动力–大动力学能垒组合和小热力学驱动力–小动力学能垒组合的材料设计策略[44-54]。与此同时,一个问题也应运而生:形成微观组织的材料加工过程涉及的热–动力学相关性是否与微观组织变形体现的强塑性互斥。
为回答上述问题,第5章阐明连续发生的相变/变形中存在的热–动力学贯通性,进而澄清相变中界面迁移和变形中位错演化的**热力学稳定性概念及其理论基础,并提出综合考虑热–动力学的广义稳定性概念,为成分和加工工艺设计提供新的思路。究其根本,热–动力学贯通性取决于如何将连续过程间不同的热–动力学组合进行定量关联,并阐明前后过程间的热–动力学遗传特性,进而选择不同热–动力学协同的*佳组合,即面向目标强韧化机制的相变设计[55-60]。这引出一个新的问题:如何获得贯通成分/工艺–组织–性能的普遍理论或规律,来实现金属结构材料的定量化设计。
第6章总结全书内容并进行展望,热–动力学协同旨在利用热–动力学多样性相关性和贯通性来发展金属材料非平衡相变理论,展示微观组织的形成机制和控制原理,进而突破相变调控的技术瓶颈。同时,提出未来相变热–动力学关注的重点科学问题,并给出了本领域的发展目标和重点研究方向。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