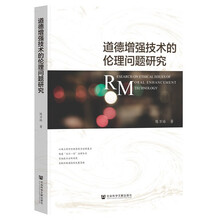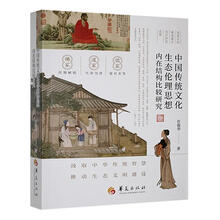引言:一位哲学家和一位生物学家走进一家酒吧
无论什么动物,只要被赋予了明显的社会本能,包括父母和子女的感情,一旦它的智力变得像人类一样发达,或者几乎像人类一样发达,就不可避免地获得某种道德感或良心。——查尔斯 达尔文,《人类的由来》(Charles Darwin,The Descent of Man)
1975年,哈佛大学的昆虫学家、社会生物学之父威尔逊(E. O. Wilson)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观点:“科学家和人文主义学者应该共同考虑这样一种可能性,即伦理学从哲学家的手中被移除,并被生物学化(biologicized)的时机已经到来。”(Wilson,1975:520)显然,哲学家们已经做了工作,但他们的努力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现在,那些全面了解人类进化的生物学家们已经做好准备,尝试解释大多数人类的特征:是非之心。尽管威尔逊和他的同事充满热忱,但他们未能明确有力地展现出“生物学化”(biologicization)的含义。威尔逊的建议给人留下了印象,但很快(哲学家们)就指出,生物学可以发挥作用,而且已经发挥了作用,并且是在道德理论中发挥了各种各样的作用,其中有些没有争议,有些则极具争议。
首先这意味着,真正的问题不在于生物学在道德的解释过程中是否发挥了一些作用(当然,它发挥了一些作用)。真正的问题是,生物学在对道德的解释过程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换句话说,人类进化的故事应当如何影响我们对自己道德生活的思考,包括我们的道德判断、道德情感、道德分歧,
我们避免不道德行为的倾向,我们对自我牺牲的赞赏,我们对不道德行为者2的敌意,等等。概略地说,这个问题是我们认为的进化伦理学的核心。想要理解生物学何以可能以多种方式影响道德理论,首先可以参考菲利普 基切尔(Kitcher,1985)提出的下列选项单:
(1)解释我们的道德心理。关于我们人类这个物种如何获得道德观念并做出道德判断,生物学可以提供(至少是部分提供)一种进化的解释。生物学或许可以解释,我们祖先所处的环境(例如,社会或者道德的特征)如何反复出现,使我们的一些祖先从道德的角度思考问题。
(2)限制或扩展我们的道德原则。生物学可以为人类的本性提供新的洞见,这可能会限制或扩展我们原本已经接受的道德原则。例如,正如我们所知,生物学家倾向于对一些伦理学家之前没有意识到的实践进行评价;这可能又反过来扩大了应该受到道德保护的实践的范畴。
(3)决定道德属性的形而上学地位。生物学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道德的客观性问题。例如,有些人认为,进化“愚弄”了我们,让我们相信某些行为确实是错误的(在现实中,没有什么是错误的),因为相信会促进合作,而这反过来又会提高我们祖先的生物适应性。
(4)从进化中获得新的道德原则。只有生物学可以告诉我们,我们的道德义务是什么。例如,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认为,由于我们祖先的生存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促进“社会和谐”,因此我们负有某种道德义务去促进社会和谐。
正如你所看到的,“生物学化”(biologicizing)的伦理学对不同人来说有着不同的含义。这一点的哲学意义不能被夸大:对一项事业的承诺并不一定意味着必须对任何其他事业的承诺。例如,有人可能认为人类进化的故事部分地解释了我们何以能够拥有我们所具有的道德心理[上文的选项(1)],但否认道德义务的性质是由这一(或任何其他)生物事实决定的[选项(3)]。为了理解这是为什么,我们可以参考一个类比。心理学家试图通过研究视觉系统(这一系统的结构经过了数千生物代际的改进)来理解视觉感知的本质,3以及它们如何处理外部刺激,比如一只猫。心理学家期望了解(并已经了解)的部分是关于视觉处理的,他们并不关注猫的本质。这一点一旦被认定便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你想知道是什么让猫成为猫,那就去问动物学家,而不是心理学家。同样,有人可能会认为,道德心理学家期望了解关于道德和社会“信息”处理的方面,他们并不指望了解关于道德自身本质的方面。如果你想知道是什么导致了错误的行为,那就去问道德哲学家,而不是心理学家。至少有些人是这样认为的。
再举一个例子,有人认为生物学确实揭示了人类本质的事实,它承载着我们的道德义务[选项(2)],但否认我们的道德义务来自这些(或任何)生物学事实[选项(4)]。考虑另一个类比。一些进化心理学家推论,由于我们的早期祖先反复面临着如何从他们所吃的食物中摄取足够热量的问题,一种具有适应性的解决方案是培养对高脂肪食物的先天渴望(如果你来自另一个星球,你会怀疑我们是否有这样的渴望,但人类学家确实观察到了这种跨文化的倾向)。然而,关键是这样的:即使我们的进化史已经让我们渴望并且在任何时候都喜欢吃高脂肪食物,那么我们应该在任何时候都渴望吃高脂肪食物的结论是否是正确的呢?肯定不是!如果2004年的电影《超大码的我》(Super Size Me)(记录了一个男人可悲地试图仅仅依靠汉堡和可乐来维持生活)证明了什么的话,那就是我们应该抵制对高脂肪食物的渴望和消费。但这与生物学在道德理论中的作用有什么关系呢?
假设人类倾向于排斥外来者是事实(正如人类学家所指出的),相较于自己亲近的人,我们似乎不太不可能帮助陌生人。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应该排斥外来者?让我们来检验这种观点。假设你去另一个国家旅游,不幸掉进了一个浅浅的池塘里。因为你不会游泳,所以你的生命突然受到了威胁。现在,看到这一切的当地人是否有理由把他脚边的救生圈投掷给你呢?我有一种预感,你会说(带着自信)“是的”。为什么?因为(你可能会说)你是作为外来者的事实与当地人帮助你的理由在道德上是无关的。事实上,我们可能会更进一步,坚持认为我们应该抵制我们基于生物学的基础来排斥外来者的倾向。但如果这是正当的,那么我们就必须摒弃这样一种观点,即我们的道德义务来自我们生物学上赋予的倾向。至少有些人这样认为。
然而,*重要的一点值得再三强调:支持伦理学的“生物化”几乎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我们的进化史与理解我们现在的道德体验(moral experience)之间是相关的(至少在世俗的道德传统中),但这也揭示了这种关系的确切属性。因此,我们的任务是仔细研究细节,无论是从生物学上还是从哲学上。这就是我们在本书中要做的。
本书分为相对独立的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探索了进化塑造我们的道德心理的可能方式。我们将在进化心理学、人类学、灵长类动物学,甚至神经生物学方面探讨一些当代的工作。我们将尽可能地把关于道德自身的本质的问题放在一边,转而更多关注自然选择的进化过程是如何产生人类这样的生物的,这些生物不仅帮助别人,而且经常这样做,因为正如达尔文所指出的那样,我们“不过被正义或责任的深刻感知所驱使”。
在第二部分中,我们将视野转向规范或评价领域,我们会问:如果有的话,什么样的行动或实践被我们的进化史所证明?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甚至一些当代哲学家)认为,我们的生物学过去是心理学说明和道德规范的来源。也就是说,进化不仅告诉我们事物是怎样的(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说),还告诉我们事物应当如何(从道德的角度来说)。这种从描述性事实中推导出规范的努力遇到了一些标准的反对意见(我们之前讨论过其中之一),因此我们将探讨这些观点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经受住这些反对意见。
我们还将在第二部分中讨论道德的客观性问题。当代道德哲学中一些*令人兴奋和*具煽动性的观点认为,一旦我们对道德心理学的起源有了一个完整的描述性解释,相信“道德事实”就不合理了。根据一些人的说法,理由是进化解释了所有需要解释的东西。我们的感觉,即我们事实上的想法,有些行为在客观上是错误的,基于的理由是我们祖先之间需要合作。那么,这应该会削弱任何孤立的理由,认为道德属性,比如不正直,确实存在。我们也将会看到针对这些观点的一些反对意见,同时考察实在论(realist)[或准实在论(quasi-realist)]之于反实在论(anti-realist)观点的取舍。
然而需要强调的是,尽管书中某部分的讨论可能会对其他部分产生影响,但后面段落提出的意见会提醒我们不要仓促做出推论。在逻辑空间中有一系列令人印象深刻的组合。我们不应该预先判断哪种组合是*合理的。
*后,我要承认,有人可能期望在一本关于进化伦理学的书中讨论某些书中不会关注的问题。首先,存在着一种普遍的(令人遗憾的是有些人可能会这么说)的诱惑,试图将进化的讨论与无神论以及无神论与不道德联系起来。因此,人们可能会认为“进化伦理学”的概念是矛盾的。因为:①进化论排除了上帝在人类事务中的作用;②作为持无神论的人类缺乏任何道德的理由,所以选择进化论或伦理学,但它们不能同时使用。尽管这种推理很有诱惑力,但这存在很严重的问题。①和②都不是很明了,而努力使它们变得清晰将会涉及相当多的论证,这将引导我们深入遥远的哲学领域。无论如何,那将不是一本关于进化伦理学的书,而是一本关于宗教哲学和世俗伦理理论的书。也就是说,从我们的讨论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我们会假设人类通过进化的力量拥有许多特征(包括一些心理特征)。但是接受这个假设并不意味着接受无神论或道德虚无主义。
人们可能会从一本关于进化伦理学的书中期待到的第二点,也许是更微妙的讨论,是关于生物或基因决定论的讨论。正如我所理解的,所关注的问题如下:因为①我们的进化史决定了我们的个体基因组成,②在一个恰当且强烈的意义上,我们的基因组成决定了我们的行为,并且③我们不能对决定性的行为负有道德责任,我们的进化史会破坏道德责任。这个论点和之前的一样,可能有一些*初的吸引力,但我决定不把它囊括在这里的原因是,通过反思,它几乎每一次都被证明是错误的。我们在接下来的章节中会看到,①和②是由于对进化理论的混淆。正如任何一位生物学家都会告诉你的那样,先天遗传本身几乎什么都决定不了,就像后天培养本身几乎也无法决定任何事情一样。这两种主张不是竞争对手,而是相互呼应的。即使你的基因构成与任何其他人的没有什么区别(事实上是这样的),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环境差异将把你与其他人区别开来,但即使撇开这些不说,基因也代表不了命运。虽然进化(可能)已经使你具有特定的情绪或偏好倾向,但是你仍然有能力选择是否按照这些偏好行事。1你可以对自己说:“我多想把这份工作交给我的儿子,但我必须公平对待所有的申请人,所以我*好不要这样做。”即使③也不能免于批评(不过我将把这个问题留到下次讨论)。
不幸的是,基因决定论的问题已经成为困扰进化论和人类本性讨论的可怕话题。2虽然我可以在如大山般的批评中再添一块石头,但我更愿意让那座大山为自己说话。因此,读者对这个问题一直心存疑虑,我(也)没有什么可继续主张的。3有足够多的争论要进行梳理,而并不需要重新审视那个已经长期休眠的争议。正如我所说的那样,关于人性的进化的新见解正在得到揭示,但是道德理论的步伐还需努力跟上。正如我们刚才所看到的那样,问题的部分原因在于生物学可能以多种方式影响道德理论。既然我们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就可以开始缩小我们之于生物学的理解和之于道德的理解之间的差距。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