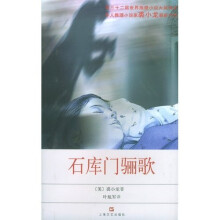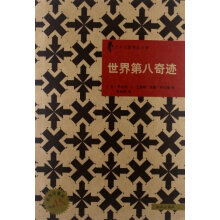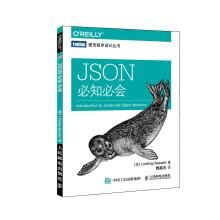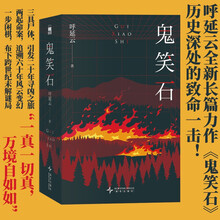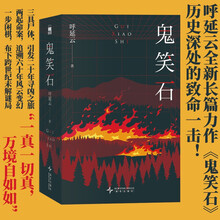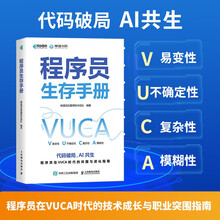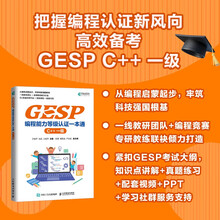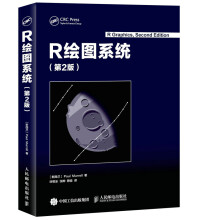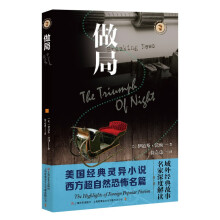《东寻西找:吴冠中的思想与艺术》:
在这个过程中,美术的两个相互联系的作用被突出。其一是对于图像功能性的认识。虽然在此之前,中国传统美术也带有一定的政治或社会含义,除去佛教、道教等宗教画外,在士大夫心中基本还只是限于所谓“明劝诫,著升沉”“成教化,助人伦”的讽喻劝谏功能,真正对意识形态起到广泛作用的工具主要是文字而非图像。特别是文人画的兴起和普泛化以后,注重个人内心修为与写意精神的取向,使得绘画更加疏离了政治功能。但这种偏向在“美术革命”中遭到了强烈批判,传统上文入画的那种审美情趣被强调写实性的视觉经验所替代。在这种情况下,美术再也不是个体内省式的心理活动的结果,而更多地指向社会与革命实践的功用。利用图像来引导、控制社会信仰是西方基督教文化一以贯之的传统。在18世纪法国大革命前后,艺术与世俗政治关联愈加紧密,艺术与理想社会、艺术与社会变革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在此后的历史发展当中,艺术更是被视为社会变革当中的一种主导力量。如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就曾指出:“艺术的力量最为直接迅捷,每当我们期望在人群中传播新思想时,我们就把它们铭刻在大理石上或印在画布上。我们以这种优于一切的方式施展振聋发聩的成功影响。”随着西画东输,中国社会自近代以来出现了大量的时事画、漫画和报刊插图,随着商业的发展其受众群体也扩散到社会的各个层面。最为典型的就是1889年在上海创办的《点石斋画报》,当时这本周刊就曾以其西式风格的版画插图吸引了大批的读者。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家们显然意识到了图像所具有的这种巨大潜力。为“美术革命”要选择写实主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认识到视觉艺术对于塑造人们的意识形态和世界观起到的速成和催化的作用,写实主义那种直白明确的方式,更能够清晰地表达思想,更易于在社会各个阶层传递。
其二是写实主义与大众文化的关联。自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发展以来,“走向民众”便成为改革者思考与实践的核心问题之一。由胡适、陈独秀发起的“文学革命”坚持以白话文改革中国文学,原因即在于他们认为那才是属于全体群众的生动语言,只有借此媒介,新文学中所要传达的革新理想才能触及民众,进而起到改造社会的作用。文学的革命是如此,其他的新文化运动也莫不做此思考。虽然在新文化运动中,“美术革命”是由少数精英喊出的口号,但它最终还是将中国传统自娱的文人艺术引导向艺术大众化的方向。当中国艺术在试图从文人墨客的书斋中面向一个广大的受众群体的时候,也就不得不正视和思考艺术作品对于普通大众的可传达性或可理解性。在这个过程中,写实绘画被看作是最贴近于五四精神、最具有民主性和科学性的艺术形式,并赋予了传达革命理念、重新打造人们的思想意识形态的意义。
“走向民众”在创作思考上来说是要求作者消除作品与一般民众的障碍,甚至要以一般观众的需求为创作的动机,放弃以作者为主体的思考模式。这种作者与观者关系的重新定义,便是对“为谁而作”和“为何而作”两个问题的思考。这自然引发了此后美术界关于“为艺术而艺术”和“为人生而艺术”的讨论。如俞寄凡作为“为艺术而艺术”的辩护者,就曾宣称“艺术有独立的目的,独立的活动,决不能把艺术当作改进政治经济宗教道德等的计划和器械”,反对将艺术建立在功利性的基础之上。而在此期间,以模仿、学习西方现代艺术流派的“新画派”也在中国逐渐滋生。所谓“新派画”主要指倾向于野兽派、立体派、超现实主义等当时前卫风格的绘画,以区别于以写实为主的西方古典绘画。作为中国第一个现代艺术团体的决澜社,在其成立《宣言》中就宣称:“我们以为绘画不是宗教的奴隶,也不是文学的说明,我们要自由地、综合地构成纯造型的世界。”从这里可以看到现代派对写实主义的不满,他们要求更能表现自我的绘画语言。这种艺术观的分歧在徐志摩与徐悲鸿的著名论战中暴露无遗。徐志摩希望在艺术领地中为现代艺术留有一席之地,而坚持写实主义的徐悲鸿则对在民族危亡之际仍有人坚持“为艺术而艺术”表示“惑”而不解,认为现时代的艺术标准就是社会认知。美术界的这种流派纷呈的局面因1937年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而基本结束,战争与革命决定了美术只能作为救亡的工具,也由此成就了写实主义的艺术道路。徐悲鸿就曾对此言道:“吾国因抗战而使写实主义抬头,战争兼能扫荡艺魔,诚为可喜。”战争并不必然导致被徐悲鸿骂为“艺魔”的现代主义的终结,恰恰相反,欧洲在两次世界大战前后发展出了现代主义艺术,而传统的写实主义绘画在此期间却日渐式微。写实主义绘画在中国的繁荣发展,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五四时期对于西方艺术先入为主的观点。在新文化运动倡导的“美术革命”中,无论是作为保守派的康有为、梁启超,还是作为激进派的陈独秀和持中的蔡元培,都主张用西方的写实主义去拯救中国颓废的文入画,而西方的现代主义则被视为和传统文人画同样颓废的堕落艺术。之所以会有这样先入为主的观点,是因为写实主义一经进入中国就必然地指向了自由主义、民族解放等方面,由此被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新文化的思想者们之所以这么急切地呼唤写实主义,是因为“美术革命”所负载的不仅是美学形态上去旧更新的需求,它更重要的任务是对国民的启蒙。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