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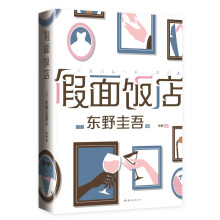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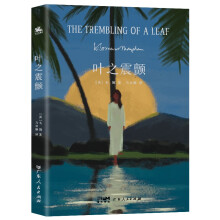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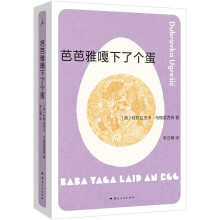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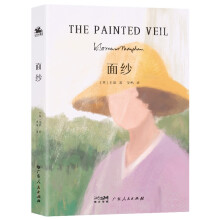
◆国际IMPAC都柏林文学奖获得者佩尔·帕特森《外出偷马》后最新力作,充满北欧的寂静与冷冽
◆独特的意识流写法,大量的内心独白勾勒出一个伤痕累累的灵魂,串联起过往和当下,文字透露出情景交融的诗意
◆讲述每个人生活中难以承受的钝痛:有关人的孤独、至亲的离去,我们如何与自己和解,与过去和解
◆几代人的丧失与寻获,抑郁和创伤如何在几代人之间延续,心灵的归宿与依靠又该去哪里找寻
◆小红书插画师王一冷×设计师朱镜霖,搭配出极具北欧风味的唯美双封。外封采用树纤纹纸,质感满满;内封烫透纸采用压凹工艺,纯白中洇出忧郁蓝色
那天是星期日,1992 年 9 月,时间差不多是早上七点。前一天晚上我出门了,最后一个小时是在托尔布大街上一家药房改建的酒吧里度过的。我没有跟任何人回家。那年,那样的时节,这几乎是不寻常的事,因为我总是会去奥斯陆市中心,违背我的本性去酒吧或者咖啡馆,找一个烟雾缭绕、人声鼎沸的场所,突然就有了归属感,于是我推门而入,仔细环顾四周,心想着今晚我要睡哪儿。几个小时后离开咖啡馆、夜店或酒吧的时候,我很少落单。过去的那几个月里,我去过的卧室、房子、城区,远比想象中我这样的男人可能做到的多得多。但那样的日子无疾而终,我曾想成为一团篝火,但现在我这团篝火中灰烬远多于火苗。
所以那天早晨电话铃响的时候,我正躺在自己的床上。我完全不想接电话,感觉自己精疲力竭。我的确喝了酒,但喝得不多,而且我确信自己在晚上十一点之后肯定没喝。我在市中心坐托森线公交车,在已经变成环岛的十字路口下车,冒着小雨经过萨格纳教堂继续朝比约尔森走。走进公寓的时候我还感
觉良好,并且确信酒已经醒了不少。
让我累成这样的,是我做的那些梦。已经到了第二页,但依旧很难解释它们怎么会让我如此疲惫,这我之后再说。
我本想再多睡至少一个小时,然后起床烧水泡咖啡,坐到写字桌前尽可能地写上几小时,尽管今天是星期日。但电话不肯罢休,于是我只好翻身下床冲进客厅去接,我这么做是因为感觉再让它响下去我就“违规”了。我总是有这样的幻觉——到现在都还有:我必须接电话,不然必遭惩罚。
是图丽的声音。一年前她带着姑娘们搬进了谢腾的一栋联排别墅。她在哭,据我判断她正用手掩着嘴压低声音,于是我说,图丽,出了什么事。但她不愿回答。你在家吗?我问。她不在。那么图丽,你在哪儿呢?我问。她不知道。你不知道你在哪儿?我问。她哭着说不知道。她不知道自己在哪儿。
该死,我心想。如果她哭成这样又不在家,那么姑娘们呢?那可是三个呀。她们反正不在我这儿,图丽的母亲在新加坡。我母亲去世了,我父亲也去世了,连我的兄弟们都差不多死绝了。你想让我过去接你吗?我问,因为我估计她的车不在她待的地方。她一边哭一边继续说,是的,所以我才打电话的,我没有其他人了。我心想,没有其他人的话你也就没什么人了。
但这话我没说出口,我说的是,但我也得知道你在哪儿呀,你在的地方看上去什么样子?这儿有个火车站,她哭着说,是黄色的,但没有火车。没有吗?我说,可能是时间有点早,怎么说今天也是星期日呀。她却说,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我的意思是没有可以跑火车的铁轨。
我想了想可能是什么地方,合情理的距离之内可供选择的地方并不多。肯定是别克朗根,我想不出其他可能性,天哪,离这儿五十公里,或许更远,六十公里也难说,她怎么会在那儿?没开车,没同伴,况且还在这个时间点。但这些我都不能问她,这都不关我的事,我还是管好我自己吧 —其实我管得还算不错。其余的不管怎么说都算是翻篇了。我甚至都不怀念,我心想,毕竟已过如此漫长的一年。但念起念落,我已经不那么确定了。
我知道你在哪儿,我说,我五分钟后出门。谢谢,她说。然后我说,到那儿得花点时间。这我心里有数,她说。我心想,她心里怎么会有数,她都不知道自己在哪儿。红色的电话亭,从那里她大概可以看到废弃的黄色火车站。如果我猜对了,找到她并不难。当然也可能是另一座废弃的火车站,在另一个方向的好几英里开外,但我想不出来。
第一卷
第二卷
第三卷
第四卷
第五卷
第六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