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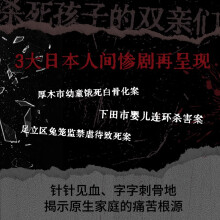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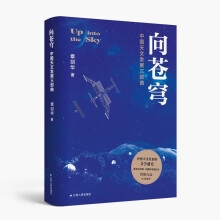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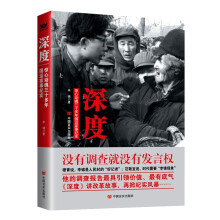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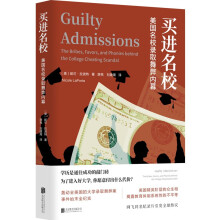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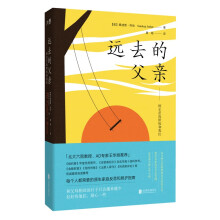
羞耻
这天晚上,我在网上申报所得税结算。点击“完成”按钮后,我立刻感到郁郁不安。我爬上床却睡不着。如果我操作有误, 税款没缴够,是会被起诉的。
恍惚睡去,我梦到我和父亲在同一个监狱的操场。我站在他旁边,但旋即走开,不想让看守看到我们在一起。梦里是一个冬日的下午,很冷。两个监狱看守大笑着,互相开着玩笑。我走上前,跟他们说我在这儿工作,下班了就会离开监狱。他们俩继续聊着天,仿佛听不到我讲话。我摸索着找钥匙,但钥匙包是空的。我问看守能否听见我说的话,但无人回应。
清晨五点,太阳刚升起时我就醒了。大雨斜着倾泻下来, 我出门往监狱走去,没有带伞。耳朵和脖子后面都湿了。到监狱安检门口,我脱掉泡湿的鞋、手表和腰带,穿过金属探测仪, 踩着湿透的袜子,感受着硬邦邦的地面。我有点眩晕,心跳也变快,像是背负了一桩疯狂而荒谬的罪。我的帆布背包正穿过X 光机。安检员严肃地看了我一眼,又盯着面前的机器判读我的罪行,我想象扫描器上的灯马上就要变红,发出哔哔的报警声,然后他们会在我的背包里发现一千克毒品。
没有刺耳的警报声。我有气无力地张开双臂让安检员检查, 套头衫的衣袖也是湿漉漉的。虽然通过了安检,我心里却仍然感到恐慌。我穿过监狱的空地,经过一堵开着一排排牢房窗户的墙, 一下子听到很多台电视机发出的声音。酸奶广告曲、紧急新闻报道、罐头笑声……
我曾偏执地认为,无论我自己做什么选择,父亲的罪过都会传给我,不过好几年没有出现过这种无端的恐惧了。这种认定自己会入狱的感觉在我十八岁时最强烈,那时我担心的不是被捕,而是如何被捕。我希望被捕的时候是白天而不是晚上,希望我是独自一人,不要有朋友在旁。我听到警笛声就心生恍惚,会停住脚步听声音是否越来越近。在监狱过道里,一名警员用绳子牵着一只德国牧羊犬迎面走来。我放慢了脚步,似乎想引诱它冲我吠叫,但它只用黑眼珠盯了我一会儿就走了。
我的学生戴维今天有人探视,不能来上课,所以我趁课前的午饭时间到他牢房送些阅读材料。他的狱友开了门,一股味道扑鼻而来。薰衣草香混杂着臭袜子味、煮泡面味和狭小空间里两个男人身上的味道。他们窗台上放了四盒紫色的空气清新剂,他跟我说戴维今天负责派午餐,还没回来。我到餐饮区一看, 那里大排长龙,不知道晚点儿来是否会好些。我问一位看起来约莫七十岁的老人午餐一般什么时候结束。他说:“我们半小时前就该吃上饭了。”他和我父亲操着同样的利物浦口音。“我问他们什么时候开饭,他们说等几分钟,他妈的已经等了二十分钟了。这种鬼地方就没有时间概念。”
于是我打算晚点儿再找戴维。回到教室,我发现一个女人正在往箱子里装玩具。泰迪熊、乐高积木、一架彩虹色木琴和一台费雪牌玩具电话,电话上装着轮子,前面还有张笑脸。她说她教会其他人玩玩具,这样探监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哄孩子了。
她走了。我把椅子摆成一圈,等待看守喊自由活动。
* * *
我出生的前几年,父亲曾蹲过十八个月的监狱。我童年时, 他又接二连三地触犯法律。我两岁时,有一次父母带我去泽西岛度假。我当时太小记不清,但母亲说假期的第二天晚上,父亲因为一名帅气的服务生对母亲彬彬有礼而吃醋。后来母亲和我返回旅馆,父亲自己则在外喝酒。凌晨一点钟,他摇摇晃晃地进了门,把一袋珠宝扔在她脚边。里面都是金戒指和钻石耳环。
“给你。”父亲说,浓重的酒气喷到母亲脸上。
“你干了什么?”母亲问。
他们听到警笛声越来越近。父亲站在那儿,手里还晃着一串珍珠项链。
他砸了一家珠宝店的橱窗,拿了陈列台上不少东西。几分钟后,警察赶到并逮捕了他。第二天,他出庭应诉。如果不是因为他拿的黄金、钻石和珍珠只是仿照正品做的塑料版,他就又回监狱了。法官判处了他财产破坏罪,责令他付了一笔罚金。母亲将留着度假用的钱交了上去。然后她改签了车票,我们当天就返程了。
父亲不想让邻居发现我们回来得这么早,因为他们就可能要问东问西了。于是,那周剩下的几天,我们都拉上窗帘在屋里待着。
我七岁的时候,父母离异,父亲搬去了距离我们三十分钟车程的地方。他做起了保险推销员。我每隔一周去他那里过周末,和同一条街上的孩子玩耍。十八个月后的一个周日,大约中午时分,电话响了。父亲还没起床。后来电话转到留言机,我听到一位老人指责父亲骗了他几千英镑。
两周后,父亲到学校接我,开车四小时去了他的新家。为了消磨时间,我看向窗外,数着高速上的交通灯,从一个数到一千个,然后再从头开始,又数了一千个。最后我们来到一个海滨小镇,他在那儿租了一个顶楼的单间公寓。
晚上,我们去了酒吧。他很快就喝醉了,还用假名跟酒吧的女侍和其他酒客搭讪。我们的桌子在角落。我啃着指甲,用手指绞着头发,坐立不安。
“老实坐好。”他说。
我把双手放在大腿上,紧张到想吐。
身份
自由
羞耻
欲望
运气
快乐
时间
疯狂
信任
救赎
遗忘
真实
凝视
欢笑
种族
内在
变化
故事
家庭
善良
教学资料及来源
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