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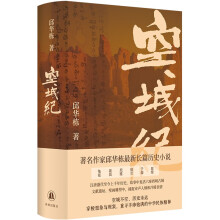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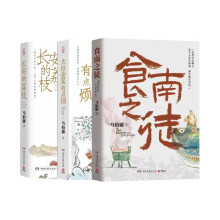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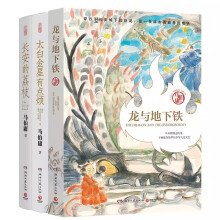
• 《西线无战事》作者雷马克创作巅峰期的泣血之作,照亮被残酷时代吞没的所有无名者。绝版40年后全新面市。
• 509,他用号码称呼自己,也让别人这样称呼他。在纳粹集中营里待了十余年,他早已不再是人,也不再想做一个人,那样只会压垮他的精神。这年春天,随着炮火声越来越近,离铁丝网颓然倒下的时刻似乎已经不远,也许就在明天,在竭尽全力躲避会传染的死亡才能抵达的明天。
•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君特·格拉斯、鲍勃·迪伦推崇的大师,茨威格、林语堂、木心盛赞的名家
这一小群犯人紧挨着营房蹲在一起。这是一个凉气袭人、迷雾朦胧的夜晚。他们却不觉得冷。刚才几个小时里,他们营房已经死了二十八个人。老兵油子们把死者身上尚有用处的衣服剥了下来,披在自己身上,抵御着寒气和疾病的侵袭。他们不想留在营房里,那里到处是喘息声、呻吟声和咂嘴声,死气沉沉。他们已经三天没得到面包了,今天甚至连汤都喝不上。每一张床上,都躺着受饥饿煎熬的生命,他们在挣扎,在苟延残喘,然后放弃,死亡。老兵油子们不愿意再进营房,不愿意挤在濒死者之间。死亡是会传染蔓延的,而且好像尤其容易出现在缺乏抵御力的睡眠中。因此,老兵油子们索性裹上死者的衣服,坐在外边,眺望远处的地平线,那里将是自由出现的地方。
“只有今天晚上了,”509说,“只有这一个晚上了!相信我好了!纽鲍尔会了解到这个情况,明天就会撤销这个命令。他们已经不能统一意见,这是他们末日的开始。咱们已经坚持这么久了,这个晚上也一定要坚持!”
大家都没出声。彼此偎依蜷缩在一起,就像冬日里的一群动物。他们得到的不仅是彼此的体温,更多的还是要活下去的勇气,这后者比体温更为重要。“咱们还是随便聊聊吧,”贝格说,“随便什么,只要同这儿没关系就行。”接着,他问身边的苏尔巴赫:“离开这儿以后,你打算干什么?”
“我吗?”苏尔巴赫迟疑了一下,“还是到时候再说吧,现在谈不吉利。”
“不会有什么不吉利了,”509激动地接过话来说,“这些年咱们一直没聊这个问题,因为只要一提起,它就会把我们吞掉。可是现在我们得聊聊了,尤其是今天晚上!不然还等到什么时候?让我们以希望为食吧!苏尔巴赫,你出去以后想做什么?”
“我不知道我妻子在哪儿。她以前在杜塞尔多夫,可杜塞尔多夫已经被炸毁了。”
“她要是在杜塞尔多夫,那她就没事了,杜塞尔多夫现在在英国人手里,广播里早就说了。”
“也许她已经死了。”苏尔巴赫说。
“当然这点也要考虑。外边的情况,我们毕竟知道得很少。”
“外边对我们知道得也很少。”布赫说。
509看着布赫。他还没有告诉布赫他父亲的死,更别提对他讲他父亲是怎么死的。现在离自由还有些时间,到那时,他会更容易承受的。布赫还年轻,将是唯一能带女友一起离开这儿的犯人。他会很快知道他父亲的事的。
“出去以后,会是什么样子呢?”迈尔霍夫说,“我在这集中营已经待了六年了。”
“我十二年了。”贝格说。
“这么久了,是不是因为政治原因?”
“不是。我有个病人,是纳粹分子,1928年到1932年间,我给他看过病。后来他成了冲锋队小头目。其实,他不算我的病人。他来我的诊所,我给他看了病,就推荐给诊所的一位朋友给他治疗。我的这位朋友是专科大夫。那个纳粹分子之所以到我诊所来,就因为我们住在同一栋楼里,他来治疗很方便。”
“就因为这个把你关起来了?”
“对,他得的是梅毒。”
“那个专科医生呢?”
“被枪毙了。我自己装作对他的病一无所知,假装以为他的病是‘一战’后留下的某种炎症。即便如此,为了小心起见,他还是把我关起来了。”
“你出去后他要是还活着,你打算怎么办呢?”
贝格想了想说:“我不知道。”
“要是我,我就把他宰了。”迈尔霍夫说。
“然后为这再进监狱?”雷本塔说,“因为杀人罪进监狱,还得关上十年或者二十年。”
“列奥,你出去后打算干什么?”509问道。
“我准备开一家服装店,销售上等的半成品大衣。”
“夏天卖大衣?列奥,马上就到夏天了!”
“也有夏天穿的大衣。我还可以经营西装,当然还有雨衣。”
“列奥,”509问,“你为什么不接着从事食品业?食品可比大衣需求量大,这事你在这儿可是一直干得挺棒!”
“真的?”雷本塔感到被认可的愉悦。
“千真万确!”
“也许你说得有道理,我会考虑的。比如说,可以经营美国食品,这生意肯定能做大。你们还记得上次大战后能买到的美国熏肉吗?厚实,肉又白嫩,就像蛋白杏仁膏,上面还有淡红色的——”
“别说了,列奥!你疯啦?”
“没疯。只是突然想起来罢了。不知道他们这次是否也会运些过来?至少应该运些给我们,对吗?”
“利奥,别说了!”
“贝格,那你打算干什么?”罗森问。
贝格擦了擦他发炎的眼睛,说:“我想找个药剂师当学徒,或者做类似这方面的工作。还做手术,用这双手?”他把手在披着的外衣下捏成了拳头,“停这么长时间了,肯定不可能了!我就去学着当个药剂师吧。你呢?”
“我妻子同我离婚了,因为我是犹太人,她现在的情况我一点也不知道。”
“你不想找她?”迈尔霍夫问。
罗森犹疑着说:“她当时这样做也许是因为压力,她又能怎样办呢?是我自己劝她离婚的。”
“也许她现在体型早已走了样,已经不好看了,”雷本塔说,“那对你就不成问题了。也许你还挺乐意摆脱她呢。”
“咱们也不年轻了啊。”
“是呀,九年了!”苏尔巴赫咳嗽起来,“这么长时间了,该会有怎样的久别重逢啊?”
“真要能有重逢,就是幸运了。”
“这么长时间了,”苏尔巴赫重复说道,“相互还能认出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