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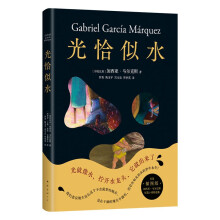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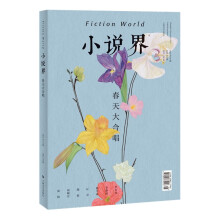

1.昆德拉的“遗忘三部曲”之一、“法国周期”开官之作
发出终极追问——“我是谁”
尚塔尔在儿子去世的时候感到一种解脱,因为这样就不必爱这个世界了。
她还希望从她的过去、她的身体、她的年龄和她的职业中解脱出来。
更甚,她已经离开了身份的领地,也就是说每个人都必须展示一张面孔并为之捍卫到死的世界。
让-马克感到痛苦,他在人群中甚至偶尔会认不出她来,当她和上下级在一起,当她在工作中,当她在梦中的时候:尚塔尔有好几张面孔,她不能也不愿在其中做出选择。
在《身份》的结尾,尚塔尔进入了一个神秘的大宅,她陷入混乱,有人对她大喊:安娜!她惊恐万分,只知道自己不是安娜,但想不起来自己原本的名字,忘了自己是谁。
我们怎么证明自己是个自由独立的个体,是自己灵魂的唯一主宰?
2.永远令人魂牵梦萦的可能性之树
那些尚未走的路,像树枝一样分岔,想象一下生活在我们面前就像一棵树——“可能性之树”,这样去看生活只持续了一小段时光。随后生活就显得是一条一次性强加下来的路,就像是一条隧道,无从出去。但原来的树的意象成为一种抹不掉洗不去的怀旧之情,我们仍然能听到它迷人的絮语。
令尚塔尔忧伤的是,男人不再回头看她了。即使让-马克仍然迷恋她,深深爱着她,但是他那情人的目光无法安慰她。
因为爱情的目光是一种使她的身体成为唯一的目光。
她需要的不是爱情的目光,而是陌生人的、粗鲁的、淫荡的目光的淹没,这些眼光毫无善意、毫无选择、毫无温柔也毫无礼貌,不可逃脱、不可回避地投注到她身上。正是这种目光将她保持在人的社会群体中,而爱情的目光则将她从中拉出来。
3.梦与真实的界限
我们正在经历的人生是真实的,还是一个梦?从哪里开始是一个梦?
在《身份》里,梦与真不再是两个对立的世界,而是一个世界渐渐变成了另一个世界,一种“真实”在人们当时还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开始变化,移向梦的领地(更确切地说,是走向噩梦)。
假如说这种从现实向梦境的过渡只不过是一种技巧上的成功,那么它的意义还是有局限性的,它运用在《身份》中,突出了“脆弱性”这个意象——不仅是身份的“脆弱性”,也有爱情的让人难以忍受的脆弱性,这种脆弱性也是爱情的无穷的力量。
一家诺曼底海滨小城中的旅馆,是他们在一册旅游指南上偶然找到的。尚塔尔星期五晚上到,先独自过一夜,让—马克会在第二天中午与她会合。她将一个小行李箱放到房间里,出门在一些陌生的街巷转了一小圈之后,回到旅馆的餐厅。七点三十分,餐厅还空着。她在一张桌旁坐下,等人来招呼她。在餐厅的另一头,靠近厨房门的地方,两个女招待谈得正欢。尚塔尔讨厌提高嗓门说话,就起身穿过餐厅,在她们旁边停下来;但她们两人完全投入到话题中去了:“要知道,十年了。我认识这一家子。真可怕。一点儿线索也没有。一点儿也没有。电视里都讲了。”另一个接着说:“他到底发生什么事了?”“简直没法想象,这才叫可怕呀。”“是谋杀?”“四处全搜索遍了。”“给绑架了?”“谁会绑他?既没钱,又无权势。他的那些孩子和他老婆都上电视了。他们可绝望了。你想啊?”
这时候,她注意到了尚塔尔:“您知道电视上有个节目专门讲失踪的人,叫《杳无踪迹》?”
“知道。”尚塔尔说。
“您可能看到布尔迪厄一家发生的事了吧?他们是这儿的人。”
“看到了,真可怕。”尚塔尔回答说,因为她实在不知道该怎样把一件悲惨事情的话题转到平庸的吃饭话题上。
另一位女招待终于问道:“您是来吃晚饭的吧?”
“对。”
“我去叫餐厅主管,您去坐吧。”
她的同事又接着说:“您想一想,您一直爱着的一个人消失了,而您又永远无法知道他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可不是要发疯!”
尚塔尔回到桌边坐下。餐厅主管五分钟后过来了。她点了一盘冷食,十分简单;她可不喜欢一个人吃饭。唉,她真是不喜欢一个人吃饭!
她一边在盘中切着火腿,一边脑子里继续着被女招待引起的思路:在今天这个世界里,我们每个人的一举一动都被控制,都被记录下来,那些大商场到处有摄像机监视我们,人们摩肩接踵,接连不断,甚至连做爱都会在第二天被搞调查或做研究的人盘问(“你们在哪里做爱?”“你们一星期做几次爱?”“用不用避孕套?”),一个人怎么可能避开监视完全消失,连一点痕迹也不留下?她当然知道这个电视节目,那名字让她害怕:《杳无踪迹》。这是电视上惟一能让她心动的节目,内容真实而悽惨,仿佛一种来自这个世界之外东西的介入,迫使电视节目放弃了它的平庸性。一位主持人用沉重的语气,要求观众提供一些证词,可以帮助找到那些失踪者。节目快结束时,电视上打出一张张前几集《杳无踪迹》节目中提到过的人的照片;其中有的人已经失踪十一年之久了。
她想象有一天就这样失去让—马克。对他一无所知,只能凭空去想象一切。她甚至都不能自杀,因为自杀就意味着背叛,意味着不愿意再等待下去,完全失去耐心。她将会一辈子都生活在一种无尽头的可怕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