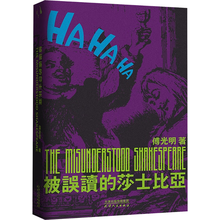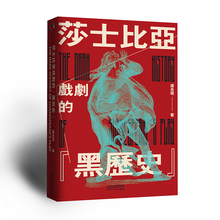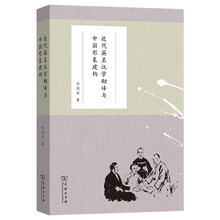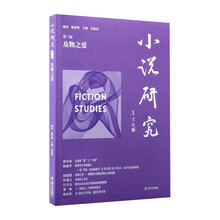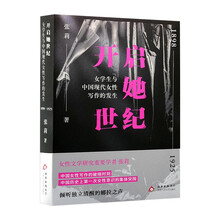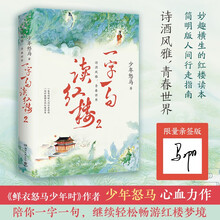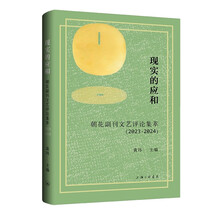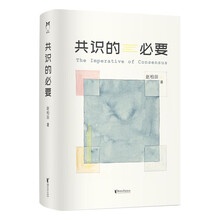绪论
鲍里斯 托马舍夫斯基在《诗学的定义》中指出,“诗学的任务(换言之即语文学或文学理论的任务)是研究文学作品的结构方式。有艺术价值的文学是诗学的研究对象。研究的方法就是对现象进行描述、分类和解释”。作为一个文学理论概念,小说诗学是对小说创作风格和叙事结构进行研究的一项审美策略。虽然,当前的小说诗学已超越了研究小说文体、结构、创作技巧等形式的传统研究领域,进入了通过对文学文本和文学现象的文化解析来提倡人文关怀和诗意追求的“文化诗学”领域,但对审美形式的探索仍然是小说诗学研究的基本内容。
大江健三郎是一位对小说形式极为关注的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歇尔 耶思普玛基在1994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中切中肯綮地指出了大江文学的显著特征。“大江说他的眼睛并不盯着世界的听众,只对日本的读者说话。但是,其中存在着超越语言与文化的契机、崭新的见解、充满凝练形象的诗这种‘变异的现实主义’。让他回归自我主题的强烈迷恋消除了(语言等)障碍。”
的确,大江文学具有浓厚的社会文化意蕴和强烈的现实关怀,这一点与日本当代社会文化语境息息相关。“变异现实主义”这一大江文学特征,如果脱离了其小说形式就成为空洞的评价。大江小说的文学诉求与作家的形式创新紧密结合,使形式本身具有了主题建构的重要意义。在这个意义上,大江的小说诗学无疑会为中国作家的小说创作提供重要的借鉴。在大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中国和日本的研究者重新开始审视大江的小说诗学,出现了一些颇有分量的研究成果(详见附录一),但从整体来看,这一领域的研究尚需进一步拓展和深入。之所以如此,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大江小说创作数量庞大且风格多样,而且不断在对旧作题材、主题的重新书写中推陈出新,这就要求研究者要持续关注大江的小说创作,同时,对大江的文学理论著作、文艺随笔、演讲、访谈等与大江文艺思想密切相关的内容也需要深入研读,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把握大江小说诗学的发展脉络和思想精髓。
大江既是作家,又是文学理论家,其小说诗学毫无疑问包含了“理论”和“实践”两个向度,二者互相阐释,共同构成了大江小说诗学不可分割的部分。由于大江的小说创作在文学界影响深远,在某种程度上遮蔽了其文学理论家的光芒,造成许多研究忽略了其文学理论在其小说诗学中的重要作用,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因此,学界需要一种将二者结合起来的整体性思路来拓展大江小说诗学研究领域。本书尝试将小说理论和小说个案考察紧密结合起来,探究文本所反映的大江的思想文化来源,真正分析并归纳出大江小说诗学的主要内涵及其总体特征。大江对世界文学、现代思想发展状况极其关注,同时在电影、音乐、绘画等艺术领域造诣颇深,这使其小说诗学具有了广阔的世界文学、文化背景和明显的跨媒介特征。因此,比较文学的跨界视野为将大江小说诗学置于世界文学、文化背景及当代日本社会文化语境中给予重新观照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可以说,只有将宏观理论研究和微观文本分析结合起来,将比较文学、文化视野导入大江小说诗学研究,才能真正理清大江在小说结构、技法和思想表达方面对西方文艺理论、现代思想的吸收、借鉴,以及对日本传统叙事文学批判继承的创作脉络,真正把大江小说诗学研究推向深入。
大江健三郎小说诗学研究一直是笔者研究的对象。为了更为全面地考察大江小说诗学的整体特征,本书选取大江早期、中期和晚期的长篇小说作为研究对象。其中,《感化院少年》为大江第一部长篇小说,在其早期创作中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个人的体验》为第11届“新潮文学奖”获奖作品,是大江“与残疾儿共生”主题系列的扛鼎之作;《万延元年的足球队》为第3届“谷崎润一郎奖”获奖作品,是一部将历史、现实共时再现,蕴含着之后大江小说诸多创作主题萌芽的巅峰之作;《亲自为我拭去泪水之日》在小说叙事上极具实验性,为大江反天皇制主题小说的代表作;《别了,我的书!》是晚期三部曲“奇怪的二人组合”*后一部,集中体现了大江的“晚期风格”;《优美的安娜贝尔 李寒彻颤栗早逝去》是中国“21世纪年度*佳外国小说(2008)微山湖奖”获奖作品,充分体现了大江小说创作的跨界思维;《水死》为2016年度国际布克奖长名单入围作品,是一部采用戏剧表现手法,对《亲自为我拭去泪水之日》《优美的安娜贝尔 李寒彻颤栗早逝去》等旧作进行改写,明确体现大江“重写”这一晚期创作风格的恢宏之作。以上小说无论是发表后的社会反响,还是在大江创作中的地位,都可以说代表了大江某一时期小说诗学的集大成之作,很好地体现了大江小说诗学的发展脉络和总体特征。本书试图从小说叙事入手,考察大江小说形式实验的先锋色彩,探讨小说形式实验与小说主题表达、伦理诉求的关联,深入挖掘大江小说诗学所体现的对日本和世界文学、文化思潮的认识和接受,以期对中国读者深入理解日本当代文学,对中国的当代文学创作提供有益的借鉴。
第一章 《感化院少年》的创伤叙事与主体建构
《感化院少年》的创伤叙事与主体建构
《感化院少年》(『芽むしり仔撃ち』1958)是大江健三郎第一部长篇小说。该小说讲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为躲避敌军轰炸,一群感化院少年被疏散至一个位于山谷中的小村庄后发生的故事。由于村里发生瘟疫,他们被村民抛弃,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建立了自己的共同体。但是,这一共同体*终在村民归来后被迫解体,成员屈从村民的淫威而集体沉默,而坚贞不屈的“我”不得不在村民的驱逐下朝村外逃亡。小说以悲剧告终,但大江却认为,通过创作这部小说,自己能够以直率的形式将少年时期无论是甜美还是心酸的记忆在小说的意象中释放出来,直言“对我来说是*令我感到幸福的作品”。也就是说,《感化院少年》直面惨淡的人生,生动地呈现了战时日本人的精神生态,是一部源于大江战时生活体验的激情之作。在叙事上,别具一格的边缘人物视角、意味深长的空间设置、哀婉凄楚的叙事格调,使这部小说所体现的战争反思和主体性叩问主题绽放出了璀璨夺目的人性之光。
第一节自我与他者:凝视与反凝视
刘小枫指出,现代的叙事伦理包含着人民伦理的大叙事和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人民伦理的大叙事的教化是动员、是规范个人的生命感觉,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的教化是抱慰、是伸展个人的生命感觉”。《感化院少年》就是一部讲述曾为不良少年的“我”在战后这一时代语境中讲述的自己的生命故事。
感化院是对失足少年进行改造的地方,对“我”来说,这一空间本身就意味着对人身自由的禁锢。感化院的高墙构成了文本中具体有形的“墙”,意指被囚禁之人与外部自由世界的隔离。疏散地“山谷村庄”虽然不同于感化院的高墙,但取而代之的却是一种更深的禁锢。村民和感化院少年之间的隔阂使山谷村庄无论是在地理上还是在精神上都成为一个封闭的空间。在这一空间中,“我们”成了被凝视的他者。
我们这一群像被猎获的怪兽一样的异国人在众人盯视的眼皮下,*安全的办法就是变得像花草木石一样,没有眼睛、没有感情,成为只供人观赏的一件物品。正因为弟弟执拗地反盯着村里人,他的面颊有时就要遭受村妇卷着黄褐色的大舌尖啐出来的唾液,有时还要挨小孩子的石头。
在此,“我”的弟弟在小说第一章暂时成为第一人称回顾性叙述的视点人物,因为“我们”被物化,只能通过弟弟的眼光来呈现“我们”所处的境况。因为弟弟与“我们”不同,他并非因为犯罪,而是为了躲避美军对城市的轰炸被父亲送至感化院的,所以并没有受到过感化院的规训和惩罚,尚未习惯他人的凝视。“它(凝视—笔者注)通常是视觉中心主义的产物,观者被权力赋予‘看’的特权,通过‘看’确立自己的主体位置,被观者在沦为‘看’的对象的同时,体会到观者眼光带来的权力压力,通过内化观者的价值判断进行自我物化。”在村民压迫性的凝视下,“我们”这些感化院少年被剥夺了主体性,将自我物化为“只供人观赏的一件物品”。天真无邪的弟弟“执拗地反盯着村里人”,显然被村民视为挑战他们的权威,势必会遭受来自村妇和村里孩子的暴力。通过被凝视者被塑造为他者这一权力运作结果,大江揭示了凝视背后的权力规训和压迫。“我们”都无法摆脱代表国家权力的村民带有歧视色彩的凝视对自我的控制,但对自由的向往又促使“我们”反凝视,这充分体现在南这一人物对南方的向往和多次逃跑这一行为上。小说第一至第三章全面采用了“我们”这一非自然叙事形式,与村民(“他们”)泾渭分明地区分开来,本身就具有与山谷村庄村民共同体对抗的性质。“在绝大多数现代叙事作品中,正是叙事视点创造了兴趣、冲突、悬念、乃至情节本身。”“我们”这一第一人称复数叙事,由于其所指人数模糊不定,从而具有较大的灵活性。“我们”一开始仅指感化院少年,之后,弟弟、朝鲜少年李、逃兵、少女等分属不同群体的人陆续加入了进来,*后形成了与村民对立的少年共同体。石原千秋指出,小说叙事在“我们”与“我”之间自由穿行,“这使《感化院少年》的视点结构不稳定,‘我’的实质几乎没有涉及,这一点象征着只要‘我们’包含‘我’就行了”。的确,从表层看来,第一人称复数叙述属于一种想象的集体身份,是讲述少年共同体集体记忆的叙事装置。或许可以说,使用第一人称复数叙事就是为了强化感化院少年这一群体与村民这一群体的对立,是一种反凝视的表现形式。“就意识再现(即对人类意识的映射—笔者注)而言,第一人称复数叙述显然把作为个体的‘我’的意识与作为集体的‘我们’的意识推到了关注的*前沿。鉴于第一人称复数叙述者指称范畴的模糊性,由此导致了其‘意识’再现的潜在冲突性。”从逻辑上看,在第一章“抵达”和第二章“第一次劳动”中,由于“我们”这一复数叙事形式的大量使用,“我们”的声音与意识压制了第一人称单数叙述者“我”的声音和意识。但从第三章“传染病流行和村民逃难”开始,随着村民躲避瘟疫从村庄撤出,“我”开始从权力的规训眼光中解脱出来,主体意识开始觉醒,获得了观察和讲述的个人主体性,逐渐从“我们”这一群体叙事视点中解放出来,“我们”这一群体视点叙事也开始转为第一人称单数“我”的个体叙事。
在村民撤离后,摆脱了村民凝视的个人主体性开始萌芽,与外界隔绝的山谷村庄这一封闭空间为文本中人物肉体和精神的历练提供了广阔的舞台,成为少年们获得个体成长的自由天地。第七章“捕鸟和雪节”描写了相当于少年们成人仪式的狩猎活动。弟弟因捉到一只漂亮的野鸡而获得了同伴的赞叹,“一边大笑一边不厌其烦地讲述他的历险记”。在朝鲜少年李的提议下,“我们”举行了村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