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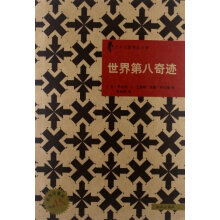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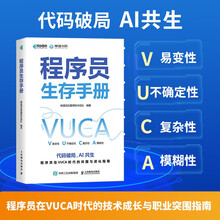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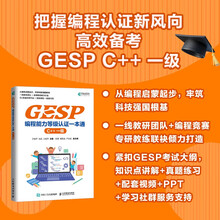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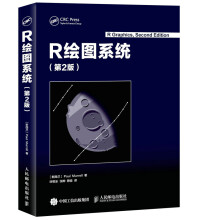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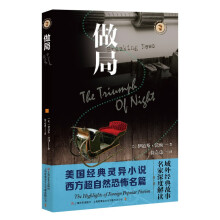

◎刀尔登的文章素来清峻精炼,幽默与警世混为一体,精辟透彻,值得反复品味。
◎刀尔登的文章像一面镜子,可以照出人们的愚蠢匮乏,及其所处时代的病症。
◎《背面》的主题,爱好,是个有趣而普遍的话题,看似个人化,刀尔登却将爱好与个体的精神世界、人类社会的希望关联起来,角度独特,启示颇多。
爱好与信心
在以前的文字中,我数次表达了一种悲观和一种乐观:那悲观是,人类在未来,或全域或局部,总要一次次退回到黑暗中去;那乐观是,人的某些能力,又总能冲破最荒陋的蒙昧、最深崄的堕落、最坚固的牢笼,一点一点地创造,一点一点地积累,终如草之破土,光之穿云,瓦解那该瓦解的,建立那该建立的。对这类能力,我的认知是浅薄的,无得具体而名之,但顽固地相信它有最纷繁的呈现方式,以至于那纷繁本身,都可以作为我们的希望所在。而人的爱好之五花八门,虽不过其小者,恰也是一种呈现。
然而这些话,一直没有说清楚。时在秋冬之交,按《月令》,该是大史“衅龟策,占兆,审验吉凶”的时候了,我连小史也不是,却也想谈谈过去和未来,顺便将忧心和信心整理一下。
我们对未来的一切推断,有两种认识上的来源,限于篇幅,本文只涉及第一种,即历史的,或经验的。读读政治幻想或科学幻想的作品,便知人类最狂野的想象,也不过是将已经发生的事予以最狂野的重组;历史同时又是解释,我们从历史中看到趋势,这趋势的延长,便是我们心中的未来了。
问题是,我们的历史太短了。相对未来而言,历史永远是短的,我们只能将自己对未来的推断,限制在我们已经拥有的理解力之内。早期的幻想小说家,只预写未来几十年的事,一个原因是他们都是乐观的进步主义者,相信几十年的时候,已足够天翻地覆。另一个原因便是他们的谨慎,——是的,你可以在作品的第一行写下长长的年份数字,但既然你的材料仍然不外乎我们已知已闻的那点事,你创造的遥远也难免是空洞的,没有说服力的。
然而人类似乎需要更遥远的信心。那怎么办?遗憾的是,历史不提供这方面的出路。想象一个拥有海拔计的尺蠖群体,不知为什么离开了枝叶,在山脉里爬行(这在生物学上是不合理的,姑且这么说),它们对“地势”会怎么看?如果它们自有历史以来一直沿着山坡上行,中间虽经过无数的坑坎,它们中间的历史学家也一定会得出结论:尺蠖拥有远大前程,进步是历史的必然。如果它们自有历史以来一直在下行,又难免流行黑暗的哲学,将自己的时代形容为黑铁时代,将先前的赞为黄金。又假如这个群体的历史足够久,已经翻起了几座山,自然也穿行了几处峡谷,它们对未来会如何看呢?
至于群体中的单只尺蠖,一生处于更小的尺度中,似逃不脱庄子的嘲笑,不过与朝菌和蟪蛄不同,它知道些历史,知道自己的生命虽然短暂,却处于一个更大的进程中。然而,这种知识果真能使它在得意时谨慎,在失意时达观吗,果真能使它知道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吗?它接受了历史学家和长老的说教,相信自己身处一出伟大的戏剧,然而它又如何得知自己是在第二幕,还是第四幕,如何对这出戏剧的性质,是悲剧还是喜剧,拥有不败的信心呢?
我们人类的现有历史是进步的,无论我们是依据什么来定义进步,是依据理性或教义,依据情感,依据对生活的实际考察,还是依据历史的唯一性。但即便用着这样的定义,如果单从历史或经验出发,谁也没办法合理地推论,这种进步是一种长期的趋势,且不要说什么永恒。谁也不能保证,人类只是短暂地爬一座山坡,山坡的那面不是低谷甚至深渊,谁也不能合理地将已有的趋势视为超越性的。如果将人类的进程比作直线,我们已经经过的短短的线段,确乎可用一个进步的数学公式来描述,但谁知道这个公式会在哪一点上开始失效呢?
我们所需要的对未来的信心有两种,一种是短暂的,一种是长远的。如果我们只谈短暂的,似可忽略历史在预示未来方面的局促,然而即使如此,我们也无法达到我们需要的乐观。人类社会在以前曾经倒退,曾经停滞,也许那倒退是局部的,停滞是暂时的,但一个人若认真地考察使人类堕落的因素,就会发现这些因素至今一样也没有消除,那么,他将无法保证这些因素会在适当的时机发生更大的作用,而不得不推论说,如果进步是必然的,那么,堕落也将是必然的。
我们习惯地忽视隐藏在日常生活背后的危机,特别是在繁荣时代,在进步时代,在所有问题或者已有解决之道、或者似将要有解决之道的时代,在对日常福祉的关心压过对更广大的事务的关心、而对更广大事务的关心又往往忽略对日常福祉的关心的时代,我们歌舞升平,踌躇满志,一边嘲笑前人,一边为后人指引方向,在技术的时代,我们注意不到技术主义正侵蚀已有的驯化权力的手段,我们自认为是在、也确实是在充满机会的时代,而注意不到那同时也是充满机会主义者和充满成为机会主义者的机会的时代,所以当变化发生时,我们瞠目结舌,好像那是突然的事。
曾经发生过、也必将在未来发生的,是权力一次又一次改变世界的面貌。人们总是忽视征兆,当美好的、先进的观念将权力视为手段时,人们只顾着赞美那观念的美好,而不去阻止它们的结合;当权力机构将远大的社会目标当作美酒递到面前时,尽管历史一次次地告诫我们那是可警惕的,人们不曾警惕,反而开怀畅饮;当群体被赞美,个人被压制时,尽管这是最紧迫的信号,人们仍无动于衷,反而忙不迭地通过附入群体的方式而在实际上瓦解为权力所需要的碎片;这时只有日常生活中的不便才会让人们烦恼,然而人们将幸存作为生存,将生存作为生活或者将希望纳入幻想,毫无道理地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本雅明曾经说,相信进步是必然的,会必然地导致无所作为,导致实际行动的无限延迟。然而有人会说,这样责备人们有什么用呢,得靠制度啊。是的,我们只好靠制度,但也不很靠得住,从第一天开始制度就是陈旧的、拖沓的、千疮百孔的,疲于奔命地应付着四面八方的侵蚀,它当初的宗旨或者退化成空洞的教义,或者被抽象为可以容入新的、危险的社会动员,它本身就是权力结构,无可避免地或者从自身产生出怪兽,或者腐朽,成为新的权力逐鹿的目标。
无论如何,曾经发生过、也必将在未来发生的,是人类被自己的创造腐蚀,而放任巨变在眼前发生。这种过程如果是突然的,大概还有些人抱有遗民心态,苦苦地守着点什么,“穷经待后王”,时间一久,终归于混同,大家渐渐地以为世界就是这样的,生活就是这样的,匍匐是天赋的姿态,困苦是应有之义,时间再久些,则连困苦也感觉不到,不知道自己的实际状态,不记得人类曾经达到的状态,也不去想象人类可能达到的状态。毕加索曾说自己蹒跚于白色画布的黑暗中,在真正的黑暗时代,人类被权力的光芒照射着,便自以为一片光明,在空洞的光明中茫然游荡;在真正的黑暗时代,黑暗是人们所同意的,这种同意,并不如某个心理学家说的“人们非理性反应的总和”,而是颇有理智,在相当程度上是斤斤计较的成果。
这些和爱好有什么关系吗?当工作被统辖,变得整齐划一之后,人类品性的丰富,如果说还有什么机会呈现的话,爱好至少是其中的一种形式,它本身完成不了什么,却通知我们,人类的一些能力还没有消亡,也不会消亡,不管需要多久,不管要“经过多少炼狱和地狱”(茨威格语),总有出头之日。我们可以想象一个村庄,也许在喀尔巴阡山中,也许在艾伯丁,那产咖啡的地方,反正是在遥远的地方,在过去或在未来,反正是在遥远的时代,想象全能的眼在夜间透视一个山村,看到戢羽的鸡,眯缝眼睛的猫头鹰,酣睡的孩子,还有成年人。在没有入睡的人当中,我们看到三个人。第一个是少年,在白天他是模范学生,服装整齐,步履中式,擅长高声朗诵课本和咒骂一切需要咒骂的东西,在这个晚上,他逃过疲倦的父母的监视,在暗淡的光线下组装一只用线轴当轮子的小车。在隐秘的私藏中,他已经有了十几辆这种手掌大的小车,仍然乐此不疲,醉心于装配和衔接,苦恼于轮子的润滑和方向的校正,最后让小车在他自制的滑道上滑行,便感觉难以解释的快乐。
我们在想象中看到的第二个人是一个年轻的母亲,白日里她与许多人在一起劳作,听大家聊天,听到定时发布的鼓舞人心的消息,也学会了如何偷懒,给自己省些力气。这样到了晚上,她偶尔,且恰好在今天,能够盗用一点时间,画树。她画过许多棵树,有的有鸟巢,有的没有,但没有一棵完完全全地合她的意,她用着最初的手法,在技巧上几无进步,也并不多想什么,只是重复地画。画完后看一看,就有些高兴,当然还要叹口气。
第三个是村里的有德之人。在今天的我们看来,他的品德并非无懈可击,主要是因为在我们眼中,这个村庄的道德规范有些缺陷,那一半是传统的,一半是新近规定的。前者只能处理小范围的关系,所以在它的约束下,一个人意识不到行为的广泛影响(同时也意识不到自己身受的影响来自何处),所以完全可能一边做着好人,一边做着恶,后者则来解释行为的全局性意义,使一切行为都可能是正当的,只要符合一种虚无缥缈的目的。不管怎么说,这第三个人在白天做了几件心满意足的事,调解了两起纠纷,赞同惩罚几个怀疑者,发表演讲来支持那些需要他支持的。到了晚上,我们看到他打开一个小箱子,取出玩偶、针线和布片,还有别的工具,戴上眼镜,耐心地给玩偶编制衣服。这不是每天都能看到的事,他今天做这个,也许是因为到了换季的时候吧,反正他做得很沉迷,就连僵死的内心也跳了几跳,让我们看到后疑心他是一个活人。
第一辑 私人花园
有用的诗,无用的人
人籁是已
象棋与围棋
矿石与锈铁
马尾与牛皮
火与石
经济人的雅好
咖啡与茶
恶习,爱好,难民
第二辑 离场备份
小心驶得自家船
和彼特拉克一起爬山
不爱越野
钓鱼与打猎
广场晨昏
班里的魔术师
看 人
第三辑 夜间游戏
爱好是软弱的
夜间的游戏和爱好
好而不乐
坏的爱好
苏格拉底的疏忽
同好,同志,及其他
爱好与信心
愿欲与察断
善 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