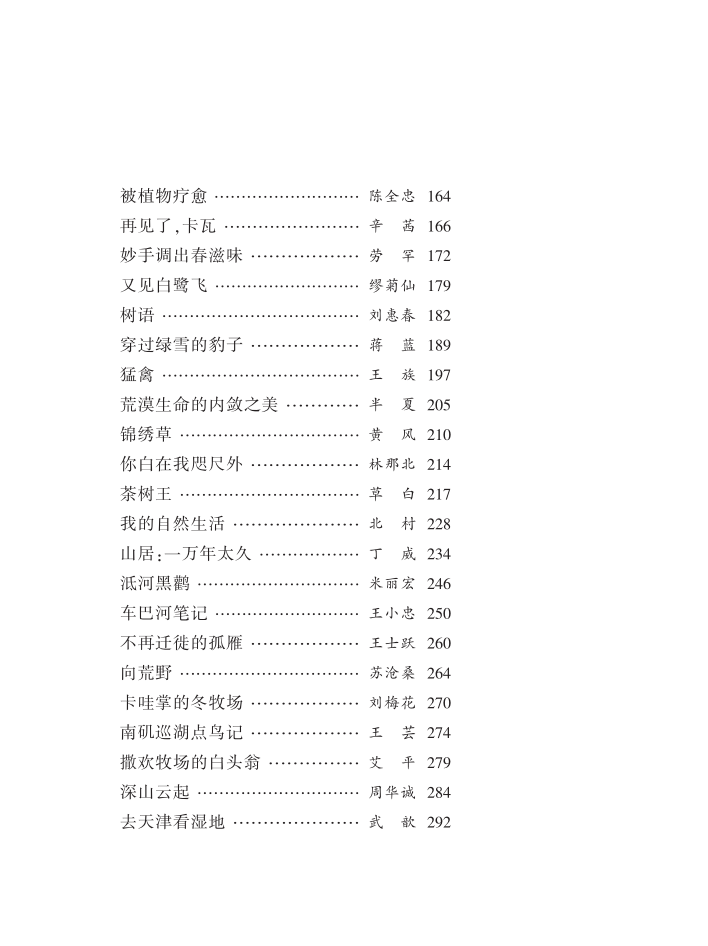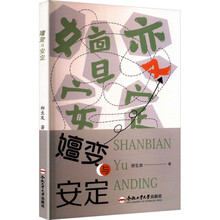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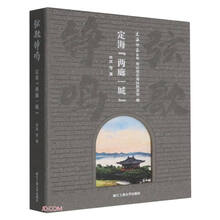
在生态文明建设不断推进的新时代,生态文学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生态文学在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学思想的交汇作用下,越来越受到人们重视,成为中国文学的重要生长点。《中国2022生态文学年选》所选文章集中体现了编者与作者对生态文学的独特感悟,是对生态文学的中国表达。这些文章充满美的特质,语言通透,立意深刻追寻生态自然的关爱。文章既具文学性,且体量适中,可读性强,能使读者在欣赏文字的同时,体味生态文明的意义与自然的魅力。
人与自然 人民与生态
李敬泽
这两年来,自然和生态书写蔚为潮流,《十月》《诗刊》《人民文学》《草原》各立名号,大力倡导。有的叫自然诗歌,有的叫自然写作,也有像《十月》这样,叫生态文学。如果我们大家投个票,选一个名号,我比较倾向于“生态文学”。
这件事要从“自然”说起。“自然”是个老词,老到老子那里,老子“道法自然”,这是中国精神的根基。“圣人任名教,老庄明自然”,晋人论孔孟老庄之异同,结论是模棱两可的“将无同”,名教和自然一体两面。“自然”派生出的文学和美学传统根深蒂固、至大至远。
但也正因为这个传统之深远,它对我们来说已经是自然而然,身在此山中,我们容易忽略这个传统本身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最近在学术界,谈山论水成了显学,巫鸿从图像史、美术史的角度去讲,哲学家们以山水为中心,梳理远古自然崇拜以降的观念演进。我对此没什么研究,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远远地看去,感觉他们都不大谈图像和观念据以展开的社会历史条件。比如东晋之后,山水诗大兴,对后世影响甚巨, “石横水分流,林密蹊绝踪”,“鸟鸣识夜栖,木落知风发”,诗很美,但是,大家别忘了,写诗的是谢灵运,那是王谢世家啊,王谢堂前的燕子都知道这世上有阶级,谢灵运的诗怎么可能是人与自然浑然为一。表面上是人和自然的问题,稍微推敲一下,这里边还有人和人的关系问题。当年衣冠南渡、门阀政治,世家大族一路跑到江南,一边掠夺一边改造,建立起一套压迫性的生产方式和等级森严的社会结构,一小撮人鄙视欺负绝大多数人,然后谢灵运他老人家站在社会顶端,穿着木屐倘佯山水、澄怀味象。历史的镜头也是势利眼,只追着他,他后面跟着一大群人伺候着,在史书中都自动屏蔽。物我两忘,物我之间那一大群人也忘得干干净净。《宋书》本传里说,谢灵运“尝自始宁南山伐木开径,直至临海。”从原始森林里开一条观景小道,把“林密蹊绝踪”的问题解决掉,这活儿肯定不是他拎一把大斧自己干,谁干的?还不是一群农奴。所以他后边有一大套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支持,他的审美精神是具体的社会结构的分泌物。这种情况在古代大致如此,王维写那么多山水诗,很美,很静,但他是有辋川别业的,他是一个贵族抒情者,所以“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陶渊明的情况有所不同,但陶渊明在他的时代本来就是特例,直到宋代经过苏轼等人的阐发,他才获得经典地位。
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审美意义上、抒情意义上,一定是复杂的社会系统、经济系统、政治系统、文化系统运作出来的结果,这个关系我们看在眼里的是“人闲”“夜静”,后边一定有广大的不闲不静。
当然,时移世易,这些诗已经脱离了它所产生的社会历史土壤,它不再是长在地上的花,它成了天上的星星,成为飘浮的能指。现在读它的时候,除了我这般杀风景的粗人,都不会看它背后的东西。谢灵运、王维是伟大的,一千多年后他们的诗依然运行在我们的心里、我们的口头,支配着我们的感受和表达。对于一般读者,这就足够了。但作为写作者、研究者,我们恐怕还是应该想得更多一些。处理人与自然这个主题的时候,我们背负着强大的传统,这个传统,它的观念、情感、修辞,都已经脱离了本来的语境,已经成为自动的抒情装置,预装在我们脑子里,它的功能就是让我们写不出所见,甚至根本无所见,眼前有景道不得,一大堆古人的话在我们心里等着。
我当编辑的时候,很怕诗人或散文家写自然、写山水、写乡土。有些人一提起笔来就“乡绅”附体,看山看水、看土地看村庄,都像个古人,而且是有闲的、其实也是有钱有势的古人。他要是穿越到东晋,肯定一头扎到谢灵运身上,到唐代,就是王维,扎到陶渊明身上也是个小乡绅啊,要不然他就拐个弯,飞过太平洋,扑到梭罗身上去了,反正他不会扑到千年前一个普通农夫身上。乡绅气是我们文学里一个老病根,时不时发作,也不限于和自然、乡土的关系。
日本的柄谷行人早就提醒我们,自然风景并非纯然客观之物,是通过主体的认知装置生产出来的。说白了大概就是,存在决定意识,你在什么社会位置上是什么人,决定了你看见什么景,风景是你的镜子。古人讲“景语”即“情语”,放大一些看,也是这个意思。 “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辛弃疾揽镜自照,英雄妩媚,跌宕自喜,但写这词时,他毕竟也是一方豪强。
中国现代以来,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一个是周作人等人花鸟虫鱼的路径,上接古人特别是晚明,终不免像周作人那样,“绅士鬼”附体。还有一个是从西方浪漫主义、梭罗等等接过来的路径。这两个路径有冲突,互相还瞧不起,但其实,作为现代主体,他们至少也是表兄弟或堂兄弟。我们文学中讲人与自然,其实主要讲的是“我”与自然,吾与天地独往来,做排除法,把中间一大摊事全删掉。在这一点上,现代传统和古典传统接得特别顺畅,周作人他们接晚明、接谢灵运王维,梭罗一脉是洋皮土骨,其实是接陶渊明。但接得这么顺畅也有问题,这可能说明那个面对自然的现代主体还没有充分发育起来,更没有为自己发明一套新的认知装置。或者说,在我们的现代文学中,人与自然、“我”与自然的书写还没有经过现代语境的充分考验,不是从现代以来的社会历史条件中分泌出来的,基本上是从古代穿越过来,从西方空降过来。在人与自然之间,还有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种种中介,还有一个广大的生活世界,我们对此并没有充分地领会,这一切都没有收入主体之中。休看他在大地上、村子里转来转去,俯仰感叹,实际上,大地上的事不在他心里,他的心里是一大堆文本,他的写作是案头写作。“我”不在捕鲸船上,当然就不会遇见“白鲸”。这个问题一直悬置在那里,直到八十年代,特别是九十年代起,猝然面对超大规模的工业化、城镇化,人和自然的关系一下子高度紧张,而我们毫无准备,没有一套有效的认知装置。
——但是这话也不准确,我们其实曾经发明了一套非常独特的认知装置,不是从古典中来,也不是从西方浪漫主义那里来的,主要来自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主要体现在十七年的文学艺术里面。一些年轻的学者对此做过研究,比如上海的朱羽,他写了一本《社会主义与“自然”——1950-1960年代中国美学论争与文艺实践研究》,就是讲新中国成立后的工业建设、农业集体化对自然观念的重塑,所谓“改天换地”,与此相应的是文学艺术中新的认知和表现模式。确实是这样,我们看长安画派的画,刘文西、石鲁等人,极具革命性,从古典绘画看下来,到这里忽然别开天地,有了全新的气象和语法,山水和自然不再是被静观玩味,它被置入一个庞大的行动和实践的视野里,由此带来了艺术上一系列革命性变化。这就是新的认知装置,后面是一个新的现代主体的生成,这是属于“我们”的“我”,是现代人民国家的主体性的确立。在文学中,你读周立波的《山乡巨变》,也有很多山水乡土的描写,但是完全没有乡绅气、士大夫气,生产方式的巨变、社会政治实践与自然景物深刻地相互映照,在这里,人和自然是另一种相亲,不是静观的,在心与物之间有了政治和劳动。
——这是革命性的,是非常超前的现代。与古典传统不同,也与西方传统不同,这是中国独特现代性的产物,出自人民主体,构成了我们自己的一个新传统。非常可惜的是,这个传统后来被悬置起来,很长的时间里被遗忘了。很多画家八九十年代又退回去了,还是笔墨意趣那一套,加了一些装神弄鬼的现代技法。在文学中也一样。
这个新中国新传统的革命性意义应该重新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不能等同于“我”与自然的关系,从“我”出发回到“我”,不管在古典视野里,还是在西方个人主义视野里,自然都被收进了自我的“内面”,自然作为“大他者”、作为人类生活的条件、作为人类实践的对象的浩瀚意义由此就被屏蔽、就失落掉了。西方面对自然时那个“我”与殖民经验、与资本主义侵犯“荒野”的经验密切相关,这个我们是没有的,然后我们又把自己五六十年代的那个革命性传统悬置起来,剩下什么呢?恐怕就只剩下单薄的趣味与心情,现成的抒情装置空转起来,复制和输出成熟的、没有难度的修辞。
所以,我赞成“生态”。 “生态”是个新词、新概念,当然不是说概念越新越好,重要的是这个新概念带着新的问题意识,打开了新的的认知空间。“生态”包含着总体性,是人与世界关系的总和,你可以说“我与自然”,你说“我与生态”就很怪,生态所对应的一定是广大的人群乃至人类。这个关系不仅是审美的、哲思的,更是实践的和社会性的。英文的生态这个词是“ecology”,Eco据说源自希腊文,是“家”的意思,这个家是人的家,人既为自己建设一个家,又被这个家所限定和塑造,而且,我再推论一下,既然是个家,它就不仅仅是一个场所、一个海德格尔式的栖居的地方,它还包括着生活世界,包括着切实的生产生计。在古典视野中,人和自然关系的关系是不怎么讲生计的,能想到这儿的人都没什么生计问题,它被很自然地屏蔽掉了,只剩下哲思和审美。但在生态视野中,你绕不开具体的人的生活,它把社会政治经济结构收了进来。这也是“生态”这个概念的力量所在,它表征着某种总体性“危机”,自然不再仅仅是抽象、绝对之物,它作为现代性的后果、巨大的人类活动的对象和后果显现出来,现在的问题是,这个“家”陷入了危机,气候变暖、生物多样性等等,而且这种危机必须通过全球规模的人类行动、通过对现代性的反思、通过社会和生活的革命性变革来解决。所以“生态”既是批判性的,又是建构性的,它认识和想象一种总体性危机,然后把“我”“我们”和全人类都放到这个危机中,去展开总体性的行动。它当然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但这个人不仅是审美的、内面的“我”,它同时必须是“大我”,必须建构起更为自觉、更为主动的社会主体。
英国首相约翰逊在今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有一个讲演,呼吁停止砍伐森林。森林当然很重要,但这位首相忽然要表现一下他的诗人气质,他说,那些自然界的“大教堂”是我们星球的肺。我想,我们的很多诗人也会这么表述,森林是人类的圣殿等等。这很有修辞效果很抒情,据说源于十九世纪浪漫主义,夏多布里昂说,“森林是奉纳神性的原初神殿”。但是,我在《法国理论》的公号上看到,法国人把首相大人狠狠挖苦了一通,大概是说,生活在森林里的亚马逊人可没想到那是教堂或神殿,砍伐森林关系到他们的生计,而他们的生计又深刻地被嵌入全球生产流通体系里。也就是说,你不能置身亚马逊木材做成的家具之中,然后吟唱圣殿,按那个法国人的说法,这就是一种美学诈骗。在生态视野里,最应该警惕的,恰恰是绕过人类生活的根基飘在天上抒情的“我”,首相大人忽然飞起来扮演诗人,那是揣着明白装糊涂,而在我们的作家或诗人那里,可能是真糊涂,或者是懒惰和迟钝。抒情是重要的,但问题是这个情从哪儿来,我们需要一个新的更大的认知装置,或者说,我们要建构起更为广大的、很可能充满矛盾的主体,把自然和人,把人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感受方式都放进去,把人的世界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放进去,以强健、复杂乃至庞杂的主体去观看、想象和书写。我的总的感觉是,在这里,纯文学的小说家们最为迟钝,这也难怪,他们已经被训练出了某种洁癖,不愿让梢大一点的、不那么“文学”的事物打扰自己,无法把“我”与绝对、抽象的自然之间横亘着的巨大世界收纳进来,所以一点也不奇怪,这几年能够有效、有力地处理这个主题的是比较边缘的科幻小说。在诗歌中,我看得少,不敢乱说,但欧阳江河的《凤凰》有这个气象。
话说到这儿,必须重提刚才谈到的新中国的传统。我们要在一个更广阔的视野里看待我们的历史和现实、经验和创造。中国走出了现代化新道路、开辟了现代文明新形态,其中很重要的一个维度,就在于人和自然的关系,在这个关系中确立了人民主体。党的十八大以来提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其中包括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是一体的,是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生态文明建设是关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决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必须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更加自觉地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之所以要完整地引述这一段,因为它集中体现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生态被放在五位一体的总体性里,放在文明发展道路的总体性里,在这里,贯穿着一个巨大的、又是落实到每一个人身上的主体,就是人民。
这就是我赞成“生态文学”的原因。因为由这个“生态”可以通向新中国的经验、新时代的创造。这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总体性的生态,在“人民”的主体性中,新的视野在我们眼前打开,新的认知装置必定会被发明出来。我们看电视剧《山海情》,你也可以说它是生态文学——这个时代的电视剧差不多就等于十九世纪的长篇小说——它就是在中国人民的生产生计中,在中国人民的生活、发展和创造中去重新认识和观看自然,重新界定人和自然的关系。
所以,选择“生态”不是词的问题,不是概念问题,是世界观和方法论问题,是主体的位置和构成问题。生态文学当然包括自然书写、博物学书写等等,但就文学整体来说,一种人民主体乃至人类主体的生态视野可以脱去乡绅气、士大夫气,在人和自然之间把广大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收纳进来,在这样一个总体性上去重新想象,人是不是一定要这样,人的新的可能性在哪里,“我们”是不是一定要这样,我们中国人如何为人类创造和展开新的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生态文学面对着新的广大空间,它不仅仅是想象和决断人如何与自然相处,它也在想象人如何与自己相处、人和人如何相处,甚至想象如何成为一种新的人。这种新人不是回到千万年前,不是回到小农经济,而是说我们就在二十一世纪,我们面向未来,我们回不了头,继续向前走,但我们要重新设定人的条件。在这个意义上,“生态”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核心命题,如何回应这个命题,一定程度上关系到文学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