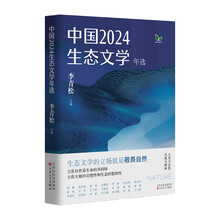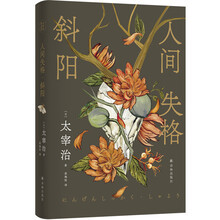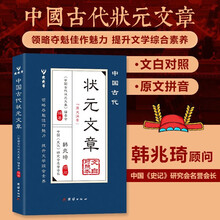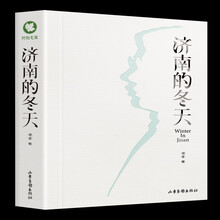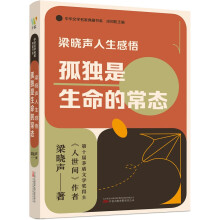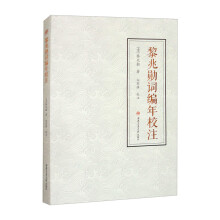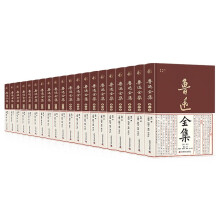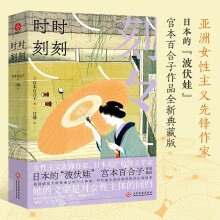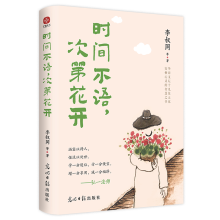1.作家刘亮程三十年来首部和迄今wei一谈话集,精选历年演讲和对话结集
2.讲述《一个人的村庄》《寒风吹彻》《捎话》等创作经历;喧至荒处,聊到天上,心中有天和荒,才能写出地老天荒的文章
3.“万事天做主,什么事都先跟天说,人顺便听到就行了,这就是聊天”,从过去聊到现在,从村庄聊到世界,从人类聊到万物
4.散文就是聊天艺术。把地上的事往天上聊,这不仅仅是散文,也是所有文学艺术所追求的蕞高表达。“我喜欢像聊天一样飞起来的语言,从琐碎平常的生活中入笔,三言两语,语言便抬起头来。那是把地上的事往天上说的架势,也是仪式。”
5.译林版du家版权,全新力作+系列quan面更新,“世界蕞美的书”得主、易烊千玺推荐的设计师朱赢椿整体设计。“刘亮程作品”(du家典藏版)包括小说《本巴》《虚土》《凿空》《捎话》,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在新疆》,访谈随笔集《把地上的事往天上聊》,均为译林社du家版权,囊括刘亮程全部重要作品,完整呈现刘亮程创作全貌与精神世界。刘亮程是21世纪真正的田园作家,物欲喧嚣下的精神守护者,具有陶渊明的悠然与宫崎骏的时空。在将“刘亮程作品”整体交予译林社时,刘亮程系统梳理作品集思路,亲自修订,校正老版本中320余处问题,撰写全新后记,完整阐释各本修订方向与内容。知名设计师朱赢椿整体装帧,灵性设计,wan美呈现刘亮程笔下宇宙混沌、自在自足的文学世界。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