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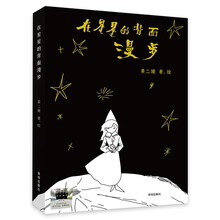







我的赣江
1
生在江边,水是我一生的景。水中嬉水,塘中摸鱼,做凼抓鱼,这些技能我在很小的时候就会了。
一条鱼像是被炸蒙了,头探出水来,挣扎着想沉下去。江岸一群人看着,多是老人和少年。冬天,江风吹在脸上刺痛。我敌不住鱼的诱惑,脱去衣服下江。我触碰到鱼时候,感觉鱼很大,我试图两手去捧它,慢慢地将它引导到岸边,可它虽被炸晕,但还是本能地挣扎开。如此反复好多次,我的手僵硬了,感觉身下皮肤紧绷,嘴唇开始颤抖。岸上的人不断唤我上岸。我知道这是生的呼唤,冥冥中我决定放弃之前的努力,吃力地游上岸。
这一年我十二岁。赣江边的孩子诸如这样的经历不会少。我在八岁的时候被人救过一次,当然我也救过别人。
春天雨水多,赣江慢慢丰满,正是放排的时候,上游不断有排放下来,风浪大来不及靠岸,木排迅即被冲散。下游的人站在江堤上,看着满江的木头,一窝蜂奔下江去,收获自然不少。那时放的排都是公家的木材,风平浪静之后,公社派人来了,说是坦白从宽,如数上交。我记得当时木头或是藏楼上,用柴草遮盖,或是埋在菜园地里,公社干部搜得仔细,偶有幸存,对于平原上的人家也是了不得的收获。这似乎就是一个游戏,年年都会做下去。
在明朝,我们那一带有一个樟树排帮,专门为放排的东家服务。为首的是新干人肖伯轩,他不仅本领强,而且心肠好,在赣江上的名声很大。他百年之后,人们尊崇他为肖公,赣江上不少地方建了肖公庙祭祀他。后来由于政治需要,永乐皇帝朱棣将肖伯轩之孙肖天任御赐为水神,从此肖公庙的香火愈加旺盛。
在中国好人就是神,人们不必担心做了好事没人记住。有的时候,大好人甚至进入国家意识形态的层面,让人们顶礼膜拜。
赣中小平原一望无际。河东种稻,河西栽果,是一种被乾隆皇帝赐名“大红袍”的三湖红橘。我们常常望见河对岸那平畴万顷的橘园。“花吐园林别有香,维橙维橘蔼春芳。”“春来到处发奇花,橙橘逢时吐翠华。”隔河千里,我们闻不到香,却看得见花,更知道其果珍贵。“直待秋来成果实,厥包赐贡献皇王。”“记取合欢香有果,分甘共羡帝王家。”后来我知道那是张恨水谈情说爱的地方,那个世界的芳名就是北雁南归。橘红时候,是一条很长的红艳艳的江岸,似乎赣江也被冬红感染,潋滟的水波上跳跃着冬红的兴奋。
我们等待着冬红下树。这个时候一艘艘满载冬红的船向我们靠岸。秋天的等待终于变成了现实。一筐筐的橘码在岸上,等待105国道上的汽车装运。夜色清冷,我们从篾筐中掏出冬红塞进衣兜,腆着大肚皮逃窜。在物资极匮乏的公社时代,这样的收获已是奢侈的享受。
我常常在堤上与江上的机帆船赛跑,我赢了,收获汗水和经验。我知道溯江而上的船,速度几乎等同于我的小慢跑。这似乎还是一个游戏,我没有任何目的。只是如此。旧时光留给我的不多,却永远都是我的,我没有办法失去这些。我骑在牛背上看河下桅杆和江风吹胀的风帆,我知道这个季节风是干的,晨露在阳光下一会儿消散,正如我望着水流怀想的远方。
2
大洋洲中学所在地是三千多年前一个王国都城,三千多年后我在这块土地上感受不到一丁点儿王气,王国都城的影子都不见了。
1980年我进入大洋洲中学读高中,正是梦想放飞的年龄,可我没有梦想,睁开眼睛想的就是跳出大洋洲。
那时候,王国都城的秘密还在地下。在我的记忆里,没有人谈起大洋洲的历史,好像大洋洲根本没有历史。千百年来,人们在这里休养生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从来没有享受过厚重历史的地域自豪。
大洋洲是一个很粗糙的地方。粗糙与粗犷不同,粗糙是一种习惯,而粗犷则是一种性情。大洋洲像是没完没了地劳作还换不来温饱,所以这地方没有情调,生长在这个地方几近悲哀。
我后来才意识到,我带出来的母语有多糙:说话带“操”,似乎不“操”则不可交流。大洋洲的起名哲学,不在乎好听,也无须寄托什么,一律的根、如、芽、欠、苟、平,信奉的是名贱好养。所以欠儿、欠苟、正如、二根、发芽、细平之类的名在我的同学中比比皆是,到高考的时候,同学们都为改名的事费尽心思,结果改名的占了六成,我的同学李欠儿改名李洪瑞,刘正如改名刘捷,张二根改名张林泰,如是云云不胜枚举,这一奇特现象让人匪夷所思。大洋洲这一地域在起名的问题上,“60后”与他们的先辈在审美标准和价值取向上发生了强烈冲突,冲突的结果似乎并未昭示这一地域新的文化气象。
大洋洲中学旁边有个村子叫牛头城,处在一块黄土坡上,名字来源于村旁巨石像牛头。村子房屋老旧,我记得好几栋是有天井的老房子,因为村子不大,人口不多,村庄外象并不动人。村子周围许多夯土堆被村民种上了庄稼,在这块土地上劳作似乎总有拾不完的瓦砾,人们能够感到此地异样,却总也说不上来,历史教科书也没有把我们这些孩子的想象打开。
也许历史过于久远和虚无,从来就没有人把中华煌煌历史与大洋洲这个小地方联系在一起。
实际上大洋洲的诡异早已露出端倪。1970年代,大洋洲公社组织社员在牛头城的东边修建中堎水库,一个社员挖出一堆“烂铁”,足有十多公斤重,社员把“烂铁”拿到永泰公社供销社卖了。不知经过怎样的环节,“烂铁”居然到了省博物馆考古队专家手上,这些人左拼右凑,“烂铁”神奇变身青铜器。经过鉴定,这批青铜器竟是商代物件。
一件平常的事,演变成了发掘牛头城遗址的理由和线索。不过,这一切进行得静悄悄,好像没有人在意,大洋洲似乎并不期待。谁知道呢,大洋洲的神经竟会如此疲惫。大洋洲泥一样的朴实和牛一样的勤劳,对无数次擦肩而过的历史机缘浑然不知,当青铜大墓惊现于世的时候,大洋洲看到了地方性格中的弱点,开始懂得好奇和探索的可贵。
对于未知的历史,坟墓里的东西最有说服力。寻找古墓与成就学者成正比,这是考古界生生不息的动力。寻找大洋洲商墓没有停止,但寻找古墓真的需要机缘巧合。1989年新干大洋洲青铜大墓发掘的时候,我已经离开大洋洲到了万安工作。得知青铜大墓发掘过程,我惊叹曾经与青铜王国擦肩而过。大洋洲是我的故乡,族谱记载我的先辈在大洋洲已经繁衍了九百年。在大洋洲中学读书时,几度寒假我都参加了加固赣江大堤的劳动,在发现青铜大墓的遗址附近取过土。
大洋洲青铜大墓位于牛头城西北,距离牛头城大约四五公里,这里是濒临赣江的平原,有遭遇洪水的危险,而牛头城东北则是延绵起伏的丘陵。人们推测,中堎水库发掘的商代文物正是出自牛头城贵族墓葬,那么牛头城西北的程家沙地是牛头城王陵?如果真是牛头城王陵,为什么仅此一处?难道还有没有发掘的王陵,或者经过几千年这座王陵被侥幸留下?
一开始,我倾向考古学界的质疑,地处赣中腹地的大洋洲怎么可能发现商代青铜大墓?是不是因为载有殷商青铜器的船只在此沉没?几千年前程家沙地未必不是赣江故道,如果这个推断可靠,学者的质疑就有了合理性。
然而,现场的考古专家们面对着发掘出来的1368件各种质地的遗物不禁深深为之震撼,礼器、乐器、陶瓷器、玉器、兵器、农具琳琅满目,简直就是一个微缩版的王国。
当人类懂得用铜和锡的合金铸造青铜器的时候,双手已经充满力量,有了让日子过得好起来的心智,从石器时代跨入青铜器时代,人类迈出的这一步很猛。
诡秘而灵动的大洋洲让人们听到来自远古的天籁,这声音刺破苍穹。
乳钉纹虎耳方鼎,形体硕大,造型雄伟,装饰华丽,四角饰羊角兽面纹,耳上铸虎形样饰,耳外侧作空槽形,深腹平底,下承四足,鼎身四壁饰以乳钉纹,极尽王权风范。
伏鸟双尾虎,体貌憨态可掬,却不失威武勇猛之风,体态蓄势待发,尽显王霸气象。虎后长着两只尾巴,违背自然常理。不知大洋洲先民为何有此新奇想法,是单纯为了设计美观还是另有神秘意图?虎背静卧一只小鸟,扬起脖颈悠然自得,与身下那只凶猛大虫形成动与静、强与弱、大与小的鲜明对比,鸟儿虽然渺小,却全然不惧猛虎之威严,宛若猛虎的驾驭者,颇有以柔克刚的哲学意味。
虎带着大洋洲的气质走进专家的视野,如果这一地域真是商代的方国,那么这个方国的名字叫什么?专家在浩瀚的史籍中寻找,却没有结果。接下来的问题自然是王国都城,通过对牛头城遗址的发掘,考古学界得出的结论是方国的都城就在牛头城。
一座大墓书写了大洋洲的历史,也改写了中华民族的文明史。
然而,这只是大概,大洋洲是一个永远的谜。人们想知道远古的方国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国?它的国王是谁?它在大洋洲存在了多少年?它管辖着多大的版图?
让人诧异的是,南方方国出土的青铜文明与同时代北方殷商青铜文明可以比肩,可创造殷商青铜文明的人们被历史记录得栩栩如生,而创造南方青铜文明的所谓何人,这些人从哪里来,最后又到哪里去了,恐怕永远也不会有人知道。
方国文明没有留下今人能够破译的文字,出土的器物中青铜铭文很少,仅有一件铜手斧形器双面有刻画符号,陶瓷器上发现的刻画文字符号最多,占总字符一半以上,可惜这些字符目前无人能解。考古是从实物中寻找历史演进的证据,当实物上找不到文字的时候,考古只能依据推断,通俗一点说就是猜。
大洋洲是一个历史符号,这个符号颠覆了江南文明的进化史,昭示中国版图文明从一开始并非倾斜,只是北方作为中国政治中心,具备了文化核心地位。生活在南北版图上的人们具有同样强大的创造力,然而,创造的意义却因为人性的贪婪黯然失色。在物资出现剩余的时候,分配又出现了难题,而远古的人们缺乏调和社会矛盾的智慧,因此,暴力和战争这种简单而极端的方式便在历史的舞台上频繁上演。
大洋洲青铜大墓出土的兵器品种繁多,器类齐全,总量为232件,考古学界把这些兵器分成8类26种39式,既有长杆格斗兵器戈、矛、长条带穿刀、钺以及把手,又有短柄卫体兵器刀、剑,还有射远兵器镞以及防护装备胄,几乎包括了中国早期冷兵器的全部类型,说明三千多年前大洋洲有着强大的军备。可是,强大的方国跟谁打,打的结果如何,所有这一切都淹没在了历史的深处。
掠夺与反掠夺、暴力与反暴力、战争与反战争,世界充满血腥的屠杀,一些人死亡,一些人逃避,在没有人烟的地方重新繁衍。迁徙伴随着人们从远古走来,文化也在人们迁徙的步履中被重建和遗忘,从此地到彼地,化有形于无形,化无形于梦魇。文化的多样性存在于先秦之前,秦统一中国之后又拿起了对文化扼杀的另一把利剑。当一种文化记忆在时空中完全丧失之后,新来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已经不可能享有文化的尊贵,没有人可以体会文化被连根拔起的疼痛。
大洋洲原本就是个非常美的地方,在赣江没有修筑堤坝以前,站在丘陵上的方国都城可以看到赣江如玉带,赣中最大的平原上水草肥美,良田万顷。利于耕种的地方无疑是繁衍的好地方。
大洋洲青铜大墓出土的143件青铜农具和手工生产工具,似乎告诉了人们隐藏在历史深处的秘密。考古界有过这样的结论:大洋洲青铜大墓出土的51件农具是考古学上罕见的现象。这些农具包括耒、耜、铲、䦆、锛、锤、镰、铚、犁铧等。在所有农具中,我最感兴趣的是耒和耜,因为这两样刻录了中国农耕文明最早的印记,有了这两样东西,农业才可能结束象耕鸟耘的时代。其实,耒和耜是很简单的农具,作用都是起土,但它们到底是什么样的玩意儿,过去我一直没搞清楚。在大洋洲青铜博物馆,我看到了这两样东西,尽管是复制的物件,但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这里展出的物件都是照原样做出来的。有了先进农具,商代大洋洲农业就十分发达,这也让大洋洲先民站在了世界的制高点。
大洋洲青铜博物馆静静地立在程家沙地,偌大的广场散布着青草的气息,仿佛不忍惊扰三千年前的亡灵。抚摸冰冷的青铜,我的内心一直热乎。
平原上的记忆艰辛而苦涩,一江春水或许就会湮灭大洋洲半年的辛苦。这样的记忆充斥在我青少年时期。端午时节,禾苗灌浆打包,洪水来了,半年的辛苦就没了,生计变得艰难。因为赣江,我的村庄两次搬迁,但都是近一百年的事情。宋代开基时,祖宗的房屋建在江岸,后来人口多了,村庄铺陈江岸。春夏秋冬,年复一年,洪水去了又来,但村庄形态千年不变。七十年前,江堤将村庄斩断,毁了大半个村庄,最古老的房屋陈设以及记忆消弭。二十多年前江堤加宽加高,大半个村庄毁去,新的村庄整整齐齐坐落在105国道旁。一千年的村庄形态彻底改变,人们的生活水平和形态也都在改变,而精神世界里的价值形态发生了多少变化却很少被关注。洪水肆虐的千百年,村庄的人口发生过重大改变,明朝的迁徙中,一房人口悉数迁往四川,而另一房只留下少数,其余迁往云南。如果要说保留,村庄的精神大概都随他们去了。也许就是这样,天天伴人的物件并不珍惜,离开了才会是念物。
赣江给予我的苦难和磨难已经淡了。我记住的那些童趣和快乐全留在我三十多年前的一篇习作里。在这篇《故乡的河在我梦中萦绕》的命题作文中,我有板有眼记叙我少年时的过往,我的老师陈延吼极为重视,居然推荐到杂志把它发表了。就是这篇作为我处女作的小文引领我走上文学创作之路。我感谢陈老师。他吃了太多苦,作为“右派”被打倒下放农村,平反后重返讲坛,而此时他已年过六十,如今他已作古。年轻时的过往,我只能写意般像流水经过,我只需记住奋斗和不屈的精神。
目录
001 赣江源记
044 赣石记
069 遂川江记
090 蜀水记
114 禾水记
139 富水记
154 泷江记
171 乌江记
190 袁江记
214 锦江记
240 赣江入湖记
256 后记:行走江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