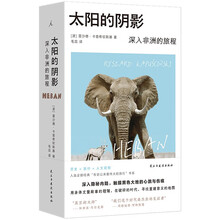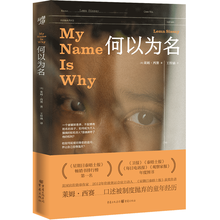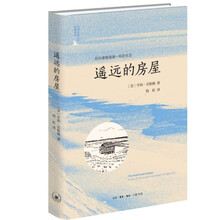耳子
山里的雨脾气烈。
金米村白天还艳阳高照,像是要晒化人,麻影子时才聚了一点儿黑云,一擦黑说发作就发作,闪电像要把天撕裂,雷炸得地都能抖起来。避在大棚里的吊袋木耳还好,就是不知大田里的地栽木耳受不受得住。
我初来乍到,遇上的村支书李正森是个热心肠。
小伙儿30出头,身高一米八,体重超200斤,皮肤黝黑,盯着人说话的时候黑眼仁几乎全露出来,眼皮一个单、一个双。他看起来五大三粗,嗓音却极柔和,喊来两个女村干部帮忙,把我安顿在村委会二楼靠西的一间房。
雨夜闲来无事,便捧起一本《柞水县志》读,想搜寻点与金米有关的文字,不觉越读越入迷。
县志里讲,柞水地貌大势犹如手掌,山脉呈手指状依次向南、东南延伸,流经金米全村的社川河则如指缝由北向南蜿蜒。受东西向和西北一东南向的构造断裂所控制,同时遭受长期风化剥蚀,由此形成山岭纵横、千沟万壑的掌状岭谷地貌。
这种山大沟深、土薄石多的特殊地貌,导致境内耕地面积仅占到总面积的百分之三,且分布流散,形状不整。但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其地处秦岭南麓,林木与中草药资源丰富,又因地质史上的燕山运动时期褶皱和断裂伴随着岩浆活动,带来丰富的矿液,生成多种多样的矿床,自唐中期便有人来此淘金…… 及至夜半,窗外雨声渐小,河水声不绝。迷迷糊糊入睡,直到隔壁院子里两只公鸡争相打鸣方被闹醒。
早起与正森相约,直奔一组财富湾的地栽木耳基地。已经有不少耳农拎着铁桶下到田里。上年纪的坐着小板凳,把木耳菌棒横在腿上,左手转动棒子,右手来来回回地挑大拣小、挑肥拣瘦。
柞水当地老百姓管木耳亲切地称为“耳子”,摘完一茬又有新的生发出来,因此摘木耳又叫“拣耳子”。细看整个劳动场面,不觉令人啧啧称奇,再没有比“拣”字更传神、更贴切的了。
我就近掬起一个菌棒,嗬,分量可不轻。接地气的那一面,木耳朵儿明显更大更稠密。正森眉飞色舞,跟耳农们聊得热络:“耳子这东西喜欢雨水,只要不下雹子,越是电闪雷鸣越能激发出它的灵性,长得越好。”
放眼望去,只见两山对开,一层又一层的山头叠着,山问升腾起雾霭,笼着这条上望不到边、下看不见头的川道。
照正森的说法,柞水的山大多以山形命名。
比方说钟鼓山,山似洪钟矗立,却又有平地一片;再说狮头山,山中间鼓起一个包包,身下好似有两只前爪伸将出来,像极了毛乎乎的狮子头。金米村沟口叫“金龙嘴”,也是这个缘故。
山都是被树盖着的,当中最显眼的自然要数杨树,但村里老一辈的人却最中意耳树。耳树又叫柞树,正森领我上坡看:这种阔叶树树皮糙厚,小时候呈棕色,长大了逐渐变成黑色,连树上的裂纹也跟着狰狞起来。
这树用处却大。在物资匮乏的年代,耳树被山民锯成长短一般齐的木桩,桩身打出一排排小洞,塞入菌种,盖上盖儿捂住,不久就能长出耳子来。当地有文人墨客为木耳写赋,称赞其为树上精灵,“一包贮天浆”。
前些年封山育林,对这种老式的“段木点耳”生产方式有影响。不过山封了,种木耳的营生却没封,而是通过别的山路迂回了——金米村现在搞的是木耳代料栽培,而且不是一家一户在弄,有基地。代料的好处是护了树林而且高产,基地则带来集约与高效。
只是作为大山的馈赠,每年仍有少量耳树通过疏林计划,变身木耳代料中的木屑,“零落成泥碾作尘”,为这川道里蓬勃而出的“大地耳朵”源源不断地供给营养。
P3-6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