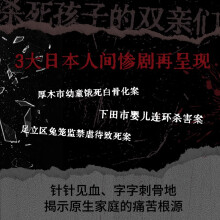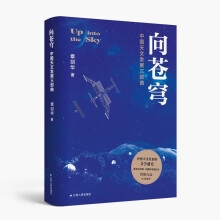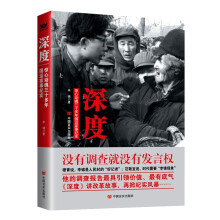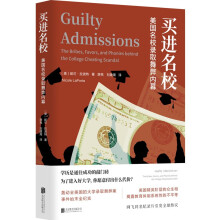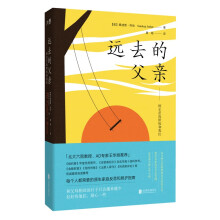父亲
一
清明、中元和冬至,我都要到山上去看我的父亲。
在父亲坟前,我点燃三炷清香,思绪随三缕青烟袅袅升起。此刻,对父亲的思念如潮水般涌上我的心头。
父亲坟前供着一捆捆折叠整齐的纸钱。我点燃了这些纸钱,“呲”的一声,一蓬红色的火焰开始跳跃,那些黑色、灰色、白色的烟灰,像一只只蝴蝶在坟前盘旋,一会儿就消失在天空中。而后,我面朝大山虔诚地拜了三拜,又烧了些“元宝”给山公山婆。
我跪在父亲的坟墓前,嘴里喃喃地祷告着……
此前,父亲曾托梦给我,要我多烧点纸钱给他。他说,他想在天堂租个鱼塘养殖珍珠。
二
早在1972年,那时我还没有出生,父亲就开始养珍珠。但在当时那个年代,养珍珠只能偷偷摸摸。父亲第一次是在自家屋后水沟小塘里养,后来发展到在村里的马塘湖、垛子头、蝴蝶角等水域养,又去邻村广山村和何家山头村养,远的地方甚至到过宁波和江西鹰潭。
在养珍珠的那些年,每到冬天,我家就像鲁四老爷家祭祖那样忙碌。外公做饭,父亲起蚌,母亲种蚌,而穿线打结、刻字做记号则是我们三兄弟的活。
到了夏天,父亲就带我们三兄弟去蚌塘。碧波荡漾的水面上,挂着一个个浮球,下面吊着珍珠蚌,全都鼓着肚子,像待产的孕妇,孕育着我们家的希望。
老房子墙上挂着父亲的三张奖状:“养蚌育珠专业(重点)户”“劳动致富光荣”“发展生产,勤劳致富,成绩显著”。金黄色的面,黑色的楷体字,鲜艳的大红花,最醒目的是第三张上盖的诸暨县委县政府的两个红章。从1982年11月一直挂到现在。岁月如梭,它们跟我一样,也进入了中年。黄色的木质镜框像是得了骨质疏松症,斑驳裂纹;金黄色的面淡化成米黄色;那朵一直盛开着的大红花,也已黯然褪色。
现在,我把这些奖状修缮一新。在我心里,这是父亲留给我的一笔丰厚遗产。它们跟父亲的墓、父亲的遗像一样重要。
我出生于1975年1月15日,农历腊月初四。那天,白塔湖畔的藕山脚下,三间平房里传出一阵婴儿的啼哭声。接生婆告诉父亲,是个男孩。父亲的心愿落空了,脸上的那份喜悦荡然无存,便顾自走出了家门。木根外婆见我父亲走来,关心着问道:“柏荣,月娜生了吗?”父亲皱着眉头回话:“生了,又生了一个儿子。”
家中已有两个男孩,父母亲一心想要个女儿。倘若有个女儿,她会像母亲那样有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和如珍珠般白皙闪亮的肌肤,父母亲会把她当成家中的“小九妹”。她会包揽家务,端茶做饭,洗衣拖地……她会时刻关心着父母亲的身体,嘘寒问暖。
父亲发病前,总是说腰不好,我们三兄弟没当一回事。倘若有个女儿,她一定会拉着父亲去看病,那样的话,父亲的病可以早些得到治疗,也不至于病入膏盲而无药可救。
父母亲生育了三个男孩,在他们身上父亲的基因凸显。在我身上,父亲的基因更明显些。他们都说,我长得最像父亲,简直与父亲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瘦瘦的体型,高高的鼻梁,走起路来,两只手像荡秋千那样前后摆动。记得有一年暑假,我跟着灿生娘舅去广州竹园旅店。正当我弯腰洗漱时,铁元走进房间,朝我喊了一声“柏荣”。我回转身,铁元一看竟是柏荣的小儿子,笑了笑,就走开了。
正是得益于父亲的遗传,我的身子,我的思想,我的行动,让我坚持去完成一道题。我常常扪心自问:这道题,我完成了吗?
父亲发病时间是1994年10月,其实应该更早,确切的时间是从他接到母亲的电话开始。母亲哭哭啼啼说着,欠我们家珍珠款的黄老板跑路了。这个电话如刺骨寒风,从遥远的西伯利亚呼啸而来,一夜之间大地变成白茫茫的一片。从那一刻开始,原本寡言少语的父亲变得更加沉闷。他担心母亲的安危,担心拿不到六十五万元珠款,担心珠农们来家里闹事……而此时的母亲第二次滞留在广东。
稻穗开花,父亲最后一次给自家的六亩八分口粮田上了水。口粮田在大塘头,划船过去十多分钟。父亲弓着身子,桨成了他的拄拐,蹒跚着上了船。父亲跟我们说不碍事,只是闪了腰,休息几天就会好。
在农村,农民从事体力活,担水,挑箩筐,背袋头,腰酸背痛比较常见。轻点,躺几天硬板床就能恢复。严重点,就去同昌叔公那里拉腰。同昌叔公是位杀猪师傅,手劲大,拉腰是他的拿手活。闪腰者平躺在地上。“躺好,躺好。”同昌叔公话音一落,就开始拉腰。滴答一秒钟,“可以站起来了”,同昌叔公拉开大嗓门喊道。闪腰者犹豫着站了起来,走两步,再走两步,腰就恢复如初。
我想父亲跟他们一样,躺几天就会恢复。实在不行,就去找拉腰师傅整一整。
然而,六十五万元珠款打水漂,这压力比1987年发生的那次辛酸的珍珠贩销损失大好几倍。父亲如坐针毡,他完全没有了病痛的知觉。
那天晚饭后,父亲把我叫住。父亲的眼里充满了痛苦,他沉着脸对我说:“今晚,你留下来,睡这边。”
这太出乎我意料了,我从断奶后就一直跟外公睡,如今,我已是一个成年人了,还要父子睡一起?突然,我心里一个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