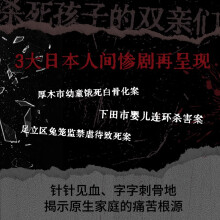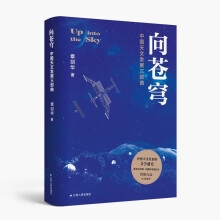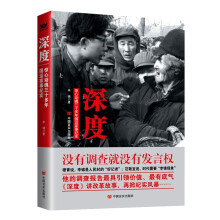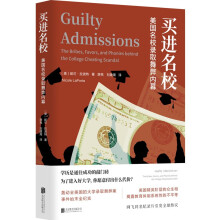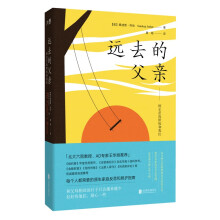挖了九天塘子
开了九天大沟
大汗流满了塘子
大汗流满了大沟
大汗滋润着种子
大汗孕育出芽儿
——拉祜族创世史诗《牡帕密帕》
看见那只鹰隼的时候,我把车停在了江桥边。
鹰隼正凭借着气流,以不动的姿势停留在澜沧江上空。白云从头顶飘过,江风穿越指尖,站在江边与鹰隼对视、与江水对视,那种感觉是奇妙的。光影、云朵、石头、树林,苍茫的大地、寂静的山寨、山峦的粗粝、作物的色块、斑斓的大美使我想到了“魔法”这个词,想到了与生活生存息息相关的种种气息和秘密,不由得心生温暖与安稳。
我一直偏执地把澜沧当作自己行走的固定目标,可以从任何季节开始,也可以从毫无由来中开始。十多年了,像赶赴千年又千年的约会,我一遍又一遍辗转于那些属于拉祜族人的山岗,真是一件说不清的事情,也许,那种古老而沉默的气息,暗合了我身上的某种特质,而心总是会在某一刻被唤醒、被灼痛、被慰藉。
2020年6月18日,我再次来到澜沧,来到拉祜族人的山寨。虽然澜沧机场早已于三年前通了航线,从昆明到澜沧700多公里的路程,一个小时就可以抵达,就可以与蛮荒、遥远之类的词语彻底绝缘。然而,快捷之余不免怅然,有时候,一条公路一根电线就结束了一段历史,更何况机场呢。所以,我一如既往地选择了车行,沿着水泥路或柏油路,沿着似曾相识的城镇、村庄,一路前行。我愿意带着体温,听从自己内心的召唤,以慢一些,再慢一些的速度,甚至是以行走的方式,以咀嚼的方式,透过瓦蓝的天空,透过荡漾的云海,透过高山大水,走进澜沧,走近拉祜族人,走向拉祜族地理人文的纵深之处,去邂逅那些深深浅浅的有关拉祜族人的故事,去打捞
那些散落在山谷里的古老的符码。与五朵相遇,与灵息相遇,与澜沧江边最深的蹄印相遇,与拉祜族山上最美好和最残酷的现实相遇,与快乐和忧伤相遇。犹如江里那些逆向源头的鱼,犹如翱翔在山谷里的鹰,我愿意以鱼的方式,在水波里与拉祜族人相见,以鹰的方式,在山岗上与拉祜族人相见,敞开自己的心扉,彼此拥抱、彼此温暖,彼此感知生命的悸动与宁静。
从昆明出发,沿着昆洛公路往西南走,到了普洱再转而沿澜沧江前行。过了那澜镇,就可以看到澜沧江。江的对岸就是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因澜沧江而得名。旱季的澜沧江,江水细小而散漫,白晃晃的阳光在它身上浮游,莹白细碎。我在意每一次对澜沧大地的触摸、学习、对话,对于我而言,所有的出发都是一次次全新的开始,都会让我惊讶,让我感到兴奋和满足。
在澜沧山脉纵横、河流交错的大地上,沿着山转,绕着水走。繁衍生息着拉祜族、佤族、哈尼族、彝族、傣族等民族,其中拉祜族最多,人口约22万人,占全县总人口43.5%。这里是拉祜族人口最为集中的地区,聚集了全世界1/3、全中国l/2的拉祜族人口。在这样的地方,不得不叹服自然的伟大,成千上万年的历史,不动声色间便豁然呈现在人的眼前。
关于澜沧,关于拉祜族,也许汉语的记忆并没有遗弃,但实际上知道的人并不多。在拉祜语里,“拉’’为虎,“祜”为将肉烤香的意思。拉祜族自称“拉祜”,分为拉祜纳(黑拉祜)、拉祜西(黄拉祜)、拉祜普(白拉祜)三个支系。拉祜纳和拉祜西两支以澜沧江为界,拉祜纳主要居住在澜沧江以西,拉祜西居住在澜沧江以东。三个支系中,拉祜纳人数最多,另外两个支系人数较少。当然,“拉祜”一词还有另外一种解释,在1953年4月澜沧拉祜族自治区(辖今澜沧、孟连、西盟三县)各族各界代表会议做出的《关于拉祜族自治区若千问题的报告》明文指出:“‘拉’即大家拉起手来,代表团结,‘祜’即代表幸福的意思。作为一个古老的民族……主要分布在澜沧江西岸,北起临沧、耿马,南至澜沧、孟连等县,国外拉祜族主要分布在与中国接壤的缅甸、泰国、越南、老挝等国家。”
说到拉祜族,就不能不说到拉祜族大家庭中的苦聪人,目前苦聪人口约4万人。苦聪人自称“锅搓”,清代前后,又称为“古宗”,主要居住在云南省哀牢山、无量山一带海拔1800~2100米的山区,分布于镇沅、金平、绿春、新平和墨江等县境内。
《新唐书》记载的“锅挫蛮”,指的就是源自古代氐羌部落的苦聪人。清代前后,又称苦聪人为“郭搓”“古宗”等。苦聪人世世代代生活在高山峻岭中,刀耕火种,漂泊不定,“种一山坡,收一箩箩”是他们的真实写照。历经千年的遁迹山林,让苦聪人害怕与山外接触,成了神秘的“野人”。P2-6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