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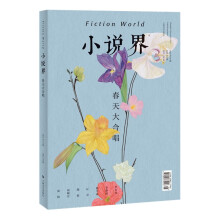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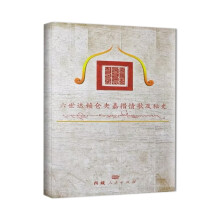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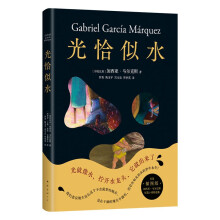
▲ 茅盾文学新人奖、汪曾祺文学奖得主、《王小波传》作者房伟全新小说集
▲充满王小波式的戏谑、夸张与幽默,背后隐藏的是对时代以及时代中人类处境的反思
作为《王小波传》作者,房伟对王小波的整体创作和个体性格均极为熟稔,其作品中亦充满王小波式的戏谑与夸张,背后则是作者对时代和时代中人处境的理解、同情和反思。比如假扮的杭州鲁迅先生的真实心境如何,“历史的残酷在于,它只能将一个小人物以丑陋的方式钉在《鲁迅全集》之中,而我想打捞他,让假鲁迅和真鲁迅同处于一个历史关注时空。”
▲ 鲁迅、张爱玲、郁达夫、王小波……关注“作家人生终点”,以及文学大师的樶后时刻
本书中大部分作品聚焦关注文学大师或文学写作者的樶后时刻,鲁迅、张爱玲、郁达夫、张资平、王小波、女频写手……他们的死亡事件中,深刻打上了时代精神的烙印,更表现出独特的中国文学风景与中国现代性经验。关注文学大师的樶后时刻,从中照见文学、历史、政治、巧合乃至身体疾病、精神疾病等对文学个体的影响。“当故事逼近死亡,天堂与地狱的对话,仿佛就变成了人类精神至暗时刻的喃喃低语。”
▲ 以真实历史事件为底,在虚构与非虚构之间,间杂推理与幻想,拼贴历史与未来
作为学者、苏州大学教授,房伟对现当代文学史料信手拈来;作为作家,他又对文学史中的诸多人事命运的多重可能性充满好奇。本书便是其充分衔接作家和学者二者身份后的产物。有的作品介于虚构与非虚构之间,以真实历史事件为底,在房伟看来,历史事件中的间隙谜点丛丛却暗藏玄机,借助文学家基于历史事实的合理想象,在小径分叉的路口,历史有了一个更为合理妥帖的结论;有的篇目则充满隐喻的未来狂想,科技发展与道德人伦之间的摩擦和悖论在作品中也展露无遗。
▲ 范小青×孙郁×程永新×王尧×邱华栋等名家诚挚推荐
学者孙郁称:《杭州鲁迅先生》中,鲁迅、郁达夫、张爱玲、王小波等人的影子以另一种方式走进小说。在作家邱华栋看来,房伟是一个天生具有复活历史现场和想象未来能力的学者小说家。他生动描绘了鲁迅、郁达夫生死故事的“本事”,还把真实与幻象潜藏在大洪水漶漫后的人工智能地下城、寒武纪生命大爆发后的文明层垒的夹缝中。因此,房伟作为一个奇特的时空穿梭者,有着超越前辈作家的伟大抱负和卓越表现,这本小说集就是明证。
▲ 内含著名人物画家周矩敏先生倾情绘制的鲁迅、张爱玲等多张人物彩色插图,与作品中相关人物图文呼应,形象传神,庄谐相济,妙趣横生。
“杭州鲁迅”先生二三事
春天来了,上海的风还透着湿冷。某日下午,章谦来和我讨论鲁迅的话题。他四十出头,师从著名的鲁迅研究专家金教授,近些年致力于鲁迅交往史。我们都是大学教师。在上海这座热闹的现代化都市,他独自蛰居在我楼上,像安静的蜗牛,不问世事,整天研究学问。
章谦坐在我那张发霉的床垫上,摆弄着床边凌乱的书籍。他瘦高,忧郁,头发有些花白。言辞木讷,却有双细长灵动的手。那个下午,章谦的手神经质地抖动着,翻翻书,又插回口袋,好像兜里藏着什么东西。看他兴奋的样子,应该是有好事。
老章,有什么好玩的?我问。
杭州鲁迅事件,知道吗?章谦说。
我晓得,没啥大惊小怪。
我用这个素材写了一篇小说。章谦又说。
想混点润笔?我笑着说,还是骗骗女学生?
就是好玩。章谦涨红了脸。
我劝他不要不务正业,评上副教授才好过活。他没房,没车,没女人,连朋友也没几个,虽然勤奋钻研学问,但文章发表得少,人到中年,职称还无法解决。
这样的男人不会有了,这个世界上。章谦喃喃自语。
简直穷酸让人倒牙。有这工夫,不如帮出版社编资料,或者上几节函授课,都能搞些快钱。这么多年,我还真没看出章谦有啥“创作才能”,这纯属瞎耽误时间。
室内陡然黯淡,我寒碜的教师宿舍仿佛深穴幽墓。我揉揉酸涩的眼,仰起头。一束莫名的光从铁锈斑斑的窗棂猛地射进,落在章谦纤长灵活的手上。那双手抖动着,掏出一叠写好的稿纸。
匆忙间,我只看到“鲁迅”两个字。
章谦的手按在稿纸上,继续抖动,好似跳到烈日滩头的鲑鱼……
一
我姓周,绍兴人。我写作。民国十六年冬,我就在杭州孤山,家里人都称呼我大先生,但这里,没人认识我。
初级师范毕业,我在绍兴本地教书,勉强度日。绍兴的学校解散,我又冒着初春潮冷,来孤山附近的小学谋食。我时常倦怠,懒得上课,懒得吃饭,也懒得说话。不知何时,我开始咯血。我自小瘦弱,家贫无力调养。父亲病逝后,母亲艰难养大我们兄妹,后来妹妹远嫁苏北。我把血咳在手绢里,不敢让别人看到。手绢沾染暗红的血,被我攥在手心,好像破碎的心脏。
学校有一百多个孩子,十名教师。校长总忘记我的名字,叮嘱我干杂活,才挠着头,含糊地说,那个周什么先生,辛苦跑一趟。我应着,下次他找我,还是记不住我的名字。
校长不爱读书。他原本是洋布贩子,趁着国家动荡,赚了几个钱,又要附庸风雅,这才活动当了校长。他还在上海小纱厂投了点股份,格外关注时局,什么上海工人罢工失利,红党被清除后在南昌暴动,蒋司令大婚,都是他在校务会上讲的。只是学校太小,没什么左倾分子,让他拿来做进身阶梯。我和同事也少有言语,只和梅先生谈几句。梅先生很年轻,和我一样穷。他只读过中学,黑矮,肥胖,是个大大咧咧的山东男子,似乎有点义气。他总拍着胸脯说要帮我。我曾听他在校长那里告我的小状,说我上课经常走神。当然,那也许的确是事实。
女同事中只有一个未婚的姜小姐,和我一样教国文。她也是初级师范毕业,自小发蒙上过“女学”,不欣赏白话文,喜欢班马史笔,韩柳古文。我和她说不到一起。她圆胖的脸上落满雀斑。我不喜欢她,她也没正眼看过我。学生也愚笨怯懦。他们大多出身小市民家庭,有的来自附近乡下,对大多数人来说,读到小学就可以了。即便如我这般,多读了点书,出路也有限。
我悄悄读鲁迅的作品,对这个有名的同乡非常羡慕。有消息说,鲁迅离开厦门,又出走广州,将来杭州隐居。我期待着,如有可能,要当面向他请教困惑。我已不是青年,不过比他小几岁,但也急盼他指点一二。像我这样,既无财产,也无能力的小知识者,如何才能找到活路?想要从文,写的东西浅陋,投稿石沉大海;即便闹革命,像我这般衰老,革命党也不愿顾看我。年轻时我便无胆气。有当革命党的同学,也曾劝我入伙,我不敢应承。还有同学跟着秋瑾起事,被贵福知府砍了头,我当时还庆幸命大。死的革命党同学成了烈士,受香火供奉;活着的大都当了官,飞黄腾达。我是活着,但卑贱谨慎,默默无闻。如今共党又闹工农起事,我衰弱老病,连“壮烈”的机会也没有了,不过挣扎着“不死”罢了。
我秘密地热爱文艺。冬天黄昏,最后一节课,我给高年级学生讲解嵇康的诗,不知为何,就扯到白话文,不知不觉讲起了鲁迅。学生们当然是不通,懵懵懂懂地被我严肃悲哀的样子骇得不敢说话。我低声朗诵《呐喊》自序:“我在年青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后来大半忘却了,但自己也并不以为可惜。所谓回忆者,虽说可以使人欢欣,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丝缕还牵着已逝的寂寞的时光,又有什么意味呢。”
我的童年比鲁迅先生更不堪吧。先生出入当铺,好歹是大户人家,我的父母不过是开小商铺的普通人。这生意不好的小铺,也因洋货冲击倒了灶。父亲欠下高利贷,吐血而死,只剩下母亲带着我和妹妹。可怜母亲凭着几分姿色,周旋于本家几位富有叔伯,才给我争来学习机会。我年幼就知道,觉得丢人,只想早些挣钱,不让她太辛苦。革命的事我断不敢参与。我年轻时候的梦,是做文学家,写出让人赞叹欢喜的小说。这个可怜的梦,我现在也大半忘却。
我又向孩子们讲起小说《在酒楼上》。破落的小教师吕纬甫,简直是在说我!我甚至怀疑鲁迅先生早知道我。我是山阴县人,离会稽不远,先生祖父介孚公是翰林,大家都晓得。
我的同学也有和先生相识的,只不过我们不认识。鲁迅怎知道我说过类似的话呢?“我在少年时,看见蜂子或蝇子停在一个地方,给什么来一吓,即刻飞去了,但是飞了一个小圈子,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便以为这实在很可笑,也可怜。可不料现在我自己也飞回来了,不过绕了一点小圈子。”
天色愈发昏暗。我背对黑板,黄昏的光流过,仿佛在我身上涂上一层暗金。那行白粉笔痕迹也模糊了。我剧烈地咳嗽,嘴角有点腥甜的东西钻出。我使劲抑制住胸口剧痛,抿着嘴,许久才平抑住了。我缓缓转过身,教室很静。学生仰着小脸,呆呆地看着我,鼻子和眼睛慢慢融化了。他们的表情也在我眼中渐渐模糊了,飞散了,好似荒野漂流的白蒲公英。
先生!一个瘦高个子男学生站起,兀自喊道。
我被唬了一跳,难道校长来了?我慌乱地看向四周,没有校长的身影。也许这正是我想要的。我厌倦了这里的一切,学校的薪水不固定,时断时续,我早想离开这里,去别处谋生,不过没有一刀两断的勇气罢了。
您是周先生,男生的脸上迸发出极大光彩,嘴角抽搐着说,您一定是周先生……
我是周先生呀。我不解。
不!男生摇头,营养不良的脸竟充血到了红润,您是鲁迅先生,我在报上看过您的照片。
我哑然失笑。这个男生是班里天分最高的学生,喜欢阅读思考,家境贫寒,经常饿肚子我有时接济他,也借给他书看。
您是鲁迅先生,男生激动地跑上讲台,揪着我的衣衫,我看过您用毛笔写的小说草稿。您和照片上的鲁迅就是一个人!
我明白他的意思。因为都是绍兴人,我也个子不高,清瘦,蓄须,浓眉。如果穿上鲁迅先生的大褂,留起先生式的短硬直发,还真有八分相似。从前也有同乡开过这方面的玩笑。我的那个同学,和鲁迅兄弟都认识,就惊讶地说,预才,你长得真像鲁迅,如果刻意模仿一番,能乱真了。
我没想冒充鲁迅。我将男学生劝回座位,宣布下课,自顾自地踱回宿舍。不知怎的,我的步履分外轻盈,连咳嗽也几乎忘记了。回到房间,我平复了心情,拿出《狂人日记》想抄写一遍,再去吃饭。小学有包饭。我们几个单身教师都在门房凑合,每月交伙食费。正在这时,梅先生冲进来,看到我,一下子停顿住,有些拘谨紧迫。我问他什么事。
梅先生悄声说,大先生不赌钱,也不叫局,安安静静地写东西,您是有大志之人。
我怀疑地看了他一眼。我写东西的事比较隐秘,还有我的私人称呼,他如何得知?因为我在家中是老大,家人朋友通信,都称我为周家大先生。我给母亲写信,也是这样题头:“母亲大人膝下敬禀者”,落款是“大男 预才 恭请 金安”。
梅先生黑黝黝的脸泛起酱红色。他讷讷地说,我,我偶然发现先生抽屉没上锁,就学习了大作,都是顶好的文章。看来先生准备在这里蛰伏休养,再拿出去发表吧。
您是不是……梅先生激动地结巴了,他指着我,好半天才说,是鲁迅先生?
“杭州鲁迅”先生二三事
苏门答腊的夏天
一九九七年“海妖”事件
寒武纪来信
谋杀女作家
外卖员与小说家
侧写师遗情录
惜琉璃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