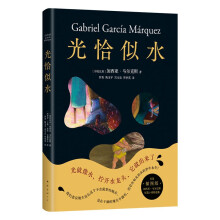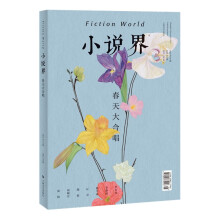常青池畔
第一章 她是什么人?
1964年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在农学院遗传教研组给李月波教授当助教。我生性沉静,不爱交际,在大学里同学们就常笑我有女孩子气。当时只有二十二岁的我,很少参加各种娱乐活动。业余时间最喜欢做的事,就是钻进图书馆的书库里,在那些散发着轻微的书香味和灰尘味的书架间流连,在人类千百年积累下来的智慧宝库中漫游。
李月波教授是一位好老师。他学识渊博,待人恳切,毫无保留地把他的知识财富传授给年青一代。他对我们这些年青的助教们常常喜欢重复下面几句话:“人类在科学的道路上,正在进行着一场永不休止的接力赛。这场接力赛是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和前进的动力之一。”接着摘下老花镜,一面慢慢地擦着镜片,一面朝我们点着头,“年轻人,你们要积聚充分的力量,接过接力棒,跑出好成绩来啊!”
作为一名年青的助手,印发讲义等具体工作当然是我的份内职责。我首先要把李教授那些字迹潦草的讲稿誊写清楚,然后送到教务处去安排刻写;刻好的蜡纸由我校对,然后付印;印好了的,拿到各个班级去分发。这样,我每个月都要往教材科跑好几次。
教材科刻讲义的人,大多数是临时工,而且年纪都很大了。但是,给我们刻遗传学讲义的,却是个年纪很轻的姑娘。除了那苗条的身材和一种独特的、训练有素的风度以外,她丝毫也不引人注目。外貌平淡的脸上,只有一双异常聪慧的眼睛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她的沉默寡言,已经到了不正常的程度。我和她打交道时,她向来是连眼皮也不抬一抬的。她总是默默地听取你对这几章讲义的刻写要求,或是一言不发地为你改正几个刻错了的字,如此而已。我心里不由得嘀咕:真倒霉!碰上了这么个从修道院里出来的姑娘。但不管怎么说,遗传学讲义既然分工给她了,我们之间至少要打上一年的交道,还是应该“搞好关系”。所以,我对她总是又客气,又尊重。可是客气也罢,尊重也罢,她一概毫无反应。那张瘦瘦的脸上的表情,总是莫测高深:既无快乐,也无悲伤;既不像高傲,又不像自卑。
两个月过去了。一天午饭时,我跟她在食堂门口面对面地碰上了。为了表示礼貌,我赶快对她笑了笑,点了个头。她笔直地朝我脸上看着,毫无反应地走了过去。那目光好像穿过了我的脸,在看什么很远很远的东西。我不由得也回过头去。看看我背后有什么值得注意的东西,没有。这种视而不见的“穿透性目光”实在有点吓人,从此以后我尽量避免和她狭路相逢。
终于有一天,当我去校对蜡纸时,她忽然主动地跟我说话了:
“史老师,请你看看这一段:‘四线期的交换和染色体的分离,在减数分裂过程中也会遇到。可是,在减数分裂时是独立的两个过程,而在有丝分裂中这两个步骤是合在一起进行的。这两个过程总称为体细胞重组。’但是,事实上应该是:在有丝分裂中,这两个步骤是独立进行的,在减数分裂时才是合并的——这是不是你的笔误?”
我仔细看了一遍,果然不错,是我在抄稿时,把两个概念抄错了。我连连点头说:“是的,是的,你改得对!”
取了蜡纸回来,好奇心使我重新回忆她的一言一行。我是个不爱管闲事的人,几个月下来,连她的名字也不知道。只听见别的教师叫她小樊,我也跟着叫她小樊。她是个什么人?没有学过遗传学的人,不,甚至一般学过的人,也不大容易发现这个不显眼的、纯理论性的错误。我还注意到她搞生物制图的技术水平极高。她通过显微镜观察切片标本后,就能够直接绘制出十分精致准确的植物病理解剖图来。这些专业性极强的插图,绝非一个美术学院的毕业生能够办到的。
她的年纪不过二十三四岁,但是我却从来没见过她的笑容,也从来没有(至少我)看见过她有什么悲哀。
P1-3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