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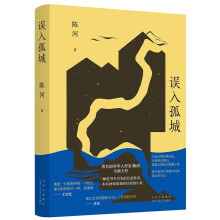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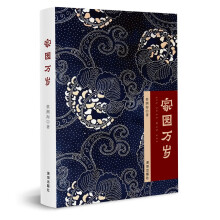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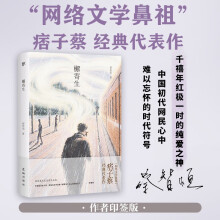



一心想要转正的编外人员、从乡村走出的大学生、被怀疑出轨的女性、保健品推销员……记忆中的牙印儿,是一道道隐形的伤口,来源不明,却无法消除。
一些随时可能脱离生活轨道的瞬间,或撕裂,或温暖。
被生活咬过的疼,在心里,在爱里。
茅盾新人奖·提名奖、滕王阁文学奖得主 宋小词 最新短篇小说集
武汉故事的新写法 湖北作家的新代表
在烟火中纯粹 在日子里爽辣
一些随时可能脱离生活轨道的瞬间,或撕裂,或温暖
被生活咬过的疼,在心里,在爱里
舅舅的光辉
五一期间我回了趟老家,落屋没多久,我妈便嘱我去看望外婆。我妈多年风湿病,脚步干难,自从我爸去世后,近几年不常回娘家,总觉得她自己孝行有亏。替母尽孝也是应该,再说九十岁的外婆,看一次就少一次了。
外婆住在白家岗村,离我们家十多里地,小时候腿短,觉得路长,如今他们村一位大款出资把路修好了,走,也就半个小时。外婆一直跟着大舅生活,这两年大舅他们在县城带二胎孙,她便一个人过,身体倒硬朗,去年我还见过她担水浇园。
远远地看见她在稻场上剥豆子,我喊她,她张望了半天,认出我后,欢喜地把我迎进屋。我们东扯葫芦西扯叶地拉些家常。我问大舅多久回来一次。她说,每月回来三四回。说大舅跟邻居都打了招呼,叫每天都来看她一下,死了好及时递信。我笑了笑。坐了片刻,我掏出孝敬钱给她后便起身告辞,免得她留我吃饭要花费一番心思。我们这里礼行规矩大,留客招待,即便是常来常往的亲人,若席面置得不丰盛,也会有怠慢之嫌。外婆自然苦留,但我执意要走,她也只好随我。送我到六棵槐那儿,她说,你今年回来过年吧,你小舅说今年回来呢。
哦。我木木呆呆的,对这个小舅没有多大感觉,从小到大,拢共也就只见过三次面。外婆说起他来,于我就像在说别人的舅舅。
回来吧,跟婆家打个商量,今年回来过年。外婆强烈要求,我不忍拂了老人家的心意,便说,好。
从来团圆都缺只角,今年不缺了。
她这样说时,我看见她浑浊的眼里放出了亮光,离过年还有大半年呢,她已经开始憧憬了。
我说,外婆你回吧,别送了。
好哦,好哦。外婆嘴里应着,停止了脚步,却没有进屋,站在稻场旁的六棵槐那里看着我。我走了好远,回头看,她还在槐树下望。我的眼前是大量抛荒的田野,杂草疯长,地里偶有老农挥锄整平,越发地令人觉得村子快要与世隔绝了。站立在天阴雨色中的外婆,让我想起风烛残年这个词。这个词语连同孤零零的外婆和凋敝的乡野一起让我的内心充满伤感。
外婆两儿四女,六个子女中,小舅读书最多,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代大学生。外婆总说她这串葫芦里,只锯出了小舅一把好瓢。这话我不大认同,那是他们舍不得锯,若舍得,不定出多少把好瓢呢,至少我妈就是一把。我妈跟着民办老师的我爸,认识了不少字,都能读下全本的《水浒传》和《红楼梦》,我爸都很为她可惜呢。不过我妈心态很平和,既不埋怨爹妈,也不眼红小弟,相反,她和大舅姨妈们都一样以这个小弟为骄傲。这“一把好瓢”成了他们共同的荣耀。
回到家我把小舅要回来过年的消息说与妈听,她说,回不回又值得了多大的事。我妈的反应倒出乎我的意料。好像是前年还是大前年,说起小舅她都是一脸神气,说小舅给我们这些外甥和侄子都做了安排。
我呵呵笑,说,妈,你洗了睡吧。
妈说,哼,你不要不信,你还不知道你小舅的实力,到时他拔一根毫毛,也够你吃一辈子的。
呵,够我吃一辈子,那得是多少?个十百千万十万
百万千万?就算是,也拔不到我们外甥的头上。要拔早拔了。
我妈显然是深信不疑,说,你呀,你别到时吃相难看。
呵呵。我对小舅早已没有任何期待了。
我第一次见小舅是六岁,记事如刀刻的年纪。春节里,小舅带着他的妻女回来过年。我们正月初二去给外婆拜年,一路上我那小脑瓜都在想省城的舅舅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礼物。我们这里有这样的礼行,出远门的人一般都会给亲友带礼物,叫带折食。像我那银行工作的表姑,我爸每次去县城开会,她都会托他给我捎一袋鲜果冻或是一袋饼干或是一袋鸡汁快餐面。折食不一定要多贵,就是一个心意,但我喜欢这种被人惦记在心里的感觉。
还只走到六棵槐这里,我就瞧见外婆家里有个生客,个不高,穿着带毛领的黑色皮夹克,脸很白,似从没见过太阳,鼻梁上一副大眼镜,眉眼像我妈。
叫小舅。我妈在旁边指导我。
小舅!我响亮地叫了一声,叫声里充满了期待。
哎。这是春来吧,都这么大了。小舅摸了摸我的头。我以为他摸完我的头就会去摸他的荷包,但没有,他直接跟我爸握手去了。
折食是不能讨要的,那时虽然年纪小,但也知道了丑,只得没劲地走了。在火塘屋里看见一个长卷发涂着口红、怀里抱着一个胖女娃的女人。大舅说,这是小舅妈。我喊了小舅妈,她也是答应了一声,然后就纹丝不动了。反倒是后面来的姨妈们给我们几个小孩子带来了新年礼物,大姨妈是红毛线围巾,大表姐织的,二姨妈是卜卜星,小姨妈是砸炮。我们围着崭新的围巾,吃着卜卜星,时不时从兜里抠出个炮往地上一砸,砰一声响。这才是过年走亲戚的味儿,不然大老远的,走得腿酸,图啥呢!
其实小舅也不是啥都没带,吃过饭,小妹妹说要玩炮炮,她当真是大城市里来的,瞧不上我们土鳖的砸炮。小舅从门后拖出一只皮箱,我们几个毛头孩子全都围了过来。他从里面拿出一个塑料袋,从袋里拿出一个花花绿绿像秤砣似的东西给小妹妹,在小舅的帮助下,她拉了吊在下面的一根绳子,突然“吱吱吱”几声响,射出一大堆彩纸,这些细碎的彩纸从半空中落下,犹如一场童话梦,引得我们在彩纸雨下转圈圈。这也罢了,更奇的是,这里面居然还射出一只小小的降落伞,粉红色的,就挂在稻场旁的榔树上,我跑去踮起脚摘了下来。这只降落伞太漂亮了,我如捡到孙悟空的三根毫毛,喜得哦哦叫。可小妹妹也要降落伞。我当然不给,这是我捡的,捡的当买的。
小舅说,还有,还有。接着又放了一个,可这个降落伞却落在了高树上,搭了梯子也够不着。又放一个,是烂的。眼看着袋子里没几个炮了,我赶紧上前跟小舅打商量,说,小舅,我把降落伞给小妹,你给我个炮吧。
小舅说给。我刚好接时,小妹嚎啕大哭,她不让,小舅就转而拉了引线,这一个却落到了水塘里。我好泄气,盼望下一个能顺顺当当。不如此,我感觉我手里这个就保不住了。最后一个总算如愿所偿,落在草垛上。我像狗一样跑过去捡给她,她总算破涕为笑,可还没高兴三分钟,她去火塘找她妈,不小心把降落伞给烧了。她又哭了起来。我赶紧提着降落伞撒腿往家跑。
春来!
我妈赶了出来,身后跟着小舅和哇哇大哭的小妹。我想,若是迫我,我就一把撕了。我玩不成,大家都玩不成。
我妈说,春来,你听我的,把这个降落伞先给小妹妹,小妹妹大老远来,是客。
我也是客。
我妈又说,你把这个给小妹妹,等会儿小舅再给你一个新的。
我不信。
我妈说,小舅箱子里还多的是。
我有些将信将疑。
小舅也附和说,是的是的,还有还有,还有更大的呢。
我总算信了,将那个降落伞给了她。然后我心里就开始惦记那个“更大的”,问他什么时候放“更大的”,他说,等吃了晚饭。我如得了令一般,跑到厨房跟外婆催饭。外婆说,乖乖,中午的饭才丢碗,哪有那么快的晚饭。外婆说的是实情,可我心里就是不爽,便跑到猪圈去找猪撒气,用棒头捶猪,猪没捶着,失手把猪食缸给打破了,潲水拌糠流了一地。这下连猪都知道我闯了大祸,拿俩眼看我,不敢哼哼。外婆和大姨妈听见动静往猪圈一瞧,就全明白了,她们没有声张,但随后而来的我妈看见了,她顺手拿起门边一根吹火棍。我赶紧撞了“天网”往外跑。我妈说,我今天不把你的手铲肿,我白字倒过来写。
屋里女人们都在弄猪食,男人们打牌,没人给我解围。还是大舅耳朵尖,他从屋里出来,冲到稻场一把拉住我妈,说,你真是,碎碎平安,打发打发呢,大正月里,外甥给我这么好的一个彩头,你还打她?我妈也就借坡下驴,将棍放了下来。为着这场恩情,我一直都坚守着正月不理发的传统。
好不容易等到吃晚饭了,我瞅着小舅的饭一吃完,就一步一摇地摇到小舅跟前。小舅看见我如看到活怪,放碗筷的手都哆嗦了一下。小舅说,你再等等,我去上个厕所。这一等就等到天麻眼,我担心小舅是不是掉进了茅坑。外婆家的厕所是埋的缸,上面搭两块木板,没处下钉,木板是活动的,踩不稳真会掉进去。我想去厕所看看,可厕所在屋后面,屋后是竹园,黑漆漆的,我害怕。我对我妈说,我要去厕所。
怕厕所里面有人,我妈在外面咳嗽了一声,可里面没回应,我心里顿时咯噔一下。
我被骗了,先前我妈要拿棍子打我我都没哭,可这会儿,我实在憋不住了,一下哭起来。我妈说,好端端的,哭什么?你上不上厕所?我不说话,只哭。我妈慌了,赶紧用手把我的额头往上抹了三下。然后抱着我边走边朝竹园里破口大骂,骂那些没长眼的孤魂野鬼,大过年的享了那么多的祭,还出来害人
回到堂屋,所有人都问我哪里不舒服,我不做声,我不能让他们知道我那点小心思,那样会让他们觉得我没出息。我只哭不说话。大舅便拿着一刀黄裱纸到竹园那里烧去了。就让他们误会我是见了鬼吧。
这一次因大姨的儿子肖立秋来武汉办事,我们几个在汉的表亲在楚河汉街的小龙坎设宴款待。我们表亲相聚聊天,一般都会聊到小舅,我们最感兴趣也最疑惑的就是小舅到底有没有钱,有多少钱。白家岗的人都认为小舅是岗上走出去的第一代大学生,国家选拔的栋梁之才,到如今只怕在朝中都能呼风唤雨了。他们这样猜测时,大舅和我妈他们也不作解释,小舅便在这种静默中演绎成了一个人物。
小舅很早就去了深圳,在一个大型国企集团当财务经理,还给我们亲戚都寄了一张名片,烫金的,上面还印了相片,白玉寿、五八集团财务经理,然后是两个电话号码,一个是座机号码,一个是大哥大号码。
那时候看港片,大佬们出场都是手里握大哥大,后面一群马仔,大哥大一按,江湖上立刻就会掀起一阵腥风血雨。村里有见识的年轻人说那东西可贵了,要好几万块。当我们为节省一毛钱两毛钱在菜摊子上挑挑拣拣讨价还价时,我们的亲舅舅手里却握着几万块的大哥大。小舅矮小的身躯在我心里一下子高大起来。
妈跟小舅感情很好,那是她脚下的弟弟,小舅差不多是我妈带大的。看到我为小舅高兴,她也跟着眉开眼笑,说,你小舅从小就是个聪明人,读书识字过目不忘,白家岗的神童。要不岗上几个参加高考的,就独你小舅一个人考取了?照古理讲,你小舅那是天上文曲星下凡。
咿呀咿呀,还文曲星下凡,这话也说太大了。我很烦我妈那套下凡论,我曾问我妈我是什么星,我妈说我是一颗吵星。从此我便对我妈这套歪理邪说没有了好感。
不管怎么说,生命里有了个发财的舅舅,成了我小小的骄傲。上小学和中学,学校经常让我们填一些表,逢到填写姑舅姨亲属那一栏,我第一个会写上小舅,单位:深圳五八集团公司,职务:总经理。我从不写大舅,也不写亲姑亲姨,他们都是农民,我妈已经是农民了,再多一个我觉得蚀人。然后我会写表姑,单位:县人民银行,职务:副行长。这便好了,虽然我的字歪七竖八,成绩一塌糊涂,但我家世显赫,出身富贵啊。
我把这些记忆中的小事说给我的表哥表姐们听,他们一个个笑得差点把食物喷在火锅里。
我说,我也不知道那时候怎么就有了这样的思想,就觉得穷是一件羞耻的事。
表哥表姐们终于不笑了。我们都是一根藤上结出的瓜,除了小舅跳出了农门,披挂了一身城市衣,我们的童年都是跟着爹娘在泥田里打滚。
添了汤,火锅暂时停止了沸腾,我们也安静了一会儿。秋表哥说,你小时候国家已经改革开放,农村分田到户,虽然穷是普遍的,但贫富有了差距,一旦有了穷与富的差别,嫌贫爱富就是很自然的事,也就是说你的势利是时代之故。
海表哥说,其实我们小时候对小舅生出过一些幻想,幻想走出去的小舅能伸出一只大手拉我们一把。
年表姐也说,我们那个时候能靠什么改变命运呢?一靠读书,可农村孩子靠读书,家里劳力不宽展,钱也不宽展,读书读得战战兢兢,指不定哪天家长就来学校搬桌子。像我家供了我哥就供不了我,能让我读到中学毕业,已经是父母莫大的恩情了。二靠什么呢?靠亲戚。像我们村有个人当兵出去提了干,然后就把他家里的侄儿侄女外甥拔萝卜似的,一个一个全拔到了城里。看着别人的叔叔姑姑姨妈和舅舅都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我们那个时候也真的指望着小舅能像菩萨一样,显一显圣,让我们有个奔头。
年表姐的话让我们想笑,却又笑不起来。记得那年我们家盖房子,我爸动过找小舅借钱的心思,但我妈没有接话,我妈的意思是,不到节骨眼上,不要去找他。什么是节骨眼呢,她觉得在家人的重大疾病上,在我读书毕业找工作时,人生至关重要的节点,小舅一伸手就能扭转乾坤满血复活的那种。我妈是把小舅当成了王牌,不到见底是不能出炸的。
小舅到底有没有钱?酒过三巡,我们差不多异口同声地问秋表哥。
在我们这些表亲中,秋表哥与小舅是接触最多的,他一年中上海待一半深圳待一半,再一个他是我们当中的首富,弄不好也有可能是整个白氏亲族的首富,毕竟小舅的底我们一直没摸清。
我们掐指算过,秋表哥的资产大约上亿了。他在深圳和上海都有房有厂有仓库,一个公司养着几百号人。虽然他总是自谦说是过过小日子,可他的小日子跟我们的小日子那是两个概念。他的大中华一摆上桌,海表哥的黄鹤楼蓝腰带就吓得藏进裤兜里;他身上的乔丹威风凛凛劈着一字马,而我身上的乔丹畏畏缩缩蜷着一支腿;同样都是大众,但秋表哥的大众多出一排字母,他的车一上路,许多车都躲得远远的,给他让一道。海表哥说,不怕奔驰和路虎,就怕大众带字母。还有我们的车需要我们亲自开,但秋表哥的车有司机开。我们在座的,试问谁家逢年过节没喝过秋表哥顺丰快递过来的茅台酒、蒙顶茶?资本为大,一般秋表哥说话,哪怕就是放个屁,我们都觉得香。
秋表哥说,我也不知道小舅有没有钱,我只能说几个事,你们自己判。小舅这几年经常要去北京,他说他在北京国贸大酒店有个长期包房,我打听了一下行情,这没个百把万下不来,这是有钱人的做派吧。还有九妹和小舅妈她们在美国过的可不是普通人的生活,她们的房子买在富人区,前后都有大草坪,九妹开的是兰博基尼。这些都是小舅给她们创造的,有钱吧?可我前一阵子公司资金周转不灵,缺笔钱过渡,找小舅开口借六十万,我想六十万对他来说是小意思吧,但他说没有。前年,白家岗修路,他不是抬起众人摔了一跤?所以有钱没钱,真不好说。
秋表哥一番言语令小舅的身家越发像太虚幻境,这么多年都弄不明白,令我们有些垂头丧气,但也勾起新一轮的好奇。
与小舅第二次见面是在我十二岁。那年家里建房,工程几度因缺钱而停止,直到秋后姑舅姨们卖了粮,借了钱给我们,房子才上梁。我们一家人在稻场旁的窝棚里从惊蛰住到小雪才搬进新房。腊月初八办贺房酒。农村里盖新房算是一件大事,我们提前十多天就给小舅写了信。
记得大舅和姨妈们合伙给我们制了一块大匾,红丝绒的底面,正中四个烫金大字,华屋春晖。大匾披红挂彩,三个姨爹和大舅抬着,还雇了乐队。外婆走前头领着穿得色色新的姨妈表哥表姐们浩浩荡荡的,将这块大匾从白家岗一路吹吹打打抬到我们家。为了迎这块匾,我爸在稻场上放了三挂万字鞭。
把这块匾送得这么声势浩大是大舅的谋划。在农村推倒旧房盖新房,一般都算作是女主人的志气,是女人在夫家的业绩。大舅这是在给他的妹子扬名立万。大匾用两架梯子一步一步升上去的,每踏一脚,喊彩师就要喊一句彩,什么步步高升、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养子成龙、养女成凤之类的,母亲好激动,不停地用手抹眼泪。热火朝天之际,门口的咨客先生高喊一句,贵戚到。我们一齐往外面看,屋檐下站着一个穿毛料西装、戴眼镜提公文包的男子,样款像极了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里的领导干部。
这贵戚是小舅,他的从天而降令白氏亲族像是活捉了一只凤凰。
虽然稻场上一桌茶席才布上不久,只动过几块麦芽糖和黄豆酥,但为了凸显小舅尊贵的地位,我妈将其撤掉重新布了一席。白家人坐在一起热热闹闹吃茶,时不时从讲话声中爆出一串洪亮的“哈哈”声。小舅出类拔萃的仪表吸引了满稻场的目光,连筛茶装烟的往这一桌跑得都勤便些。
那时秋表哥已经是第三个高三了,小舅自然问起他的状况,他鼓励秋表哥,说,秋儿一定要扳下脑袋好好读,考个好大学,你一生的道路就平坦了,你是老大,有楷模和标杆的作用,你读出来了,底下的弟弟妹妹就会跟样学样,这样一个一个就都出来了。
大姨爹吸了一口烟,弹了一下烟灰,说,秋儿这书读得我骑虎难下,劳力劳财读了这么多年,考不取不甘心,考取了我为难,没钱呢,他小舅舅。大姨爹说着低下了头。
一桌子的欢喜劲儿出现了片刻的低沉。每个人都望着小舅,仿佛他就是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小舅略沉吟了一下,说,先一门心思赴考,有我在,有白家这么多亲人在,不会让他考取了还读不成。
小舅舅说话向来轻言细语,连下诺也不像村里人恨不得把自己胸脯拍烂。我妈教育我时就喜欢拿小舅做比子,说有志不在年高,有理不在声高,像小舅舅,小声音也说得起大话。小舅的一番话把我的舅姨和我妈听得笑嘻嘻的,一个个都对秋表哥说,这颗定心丸子吃得好,明年秋儿高考顶状元。把秋表哥说得满脸通红。
我似乎也得到了某种鼓舞,在一旁洋洋得意。逢到有客人来打问这个“贵戚”时,我就会骄傲地告诉他,这是我的小舅舅,亲亲的小舅舅。
连我那县里做人民银行副行长的表姑都托我爸引见,跟我小舅握了手,交换了名片。表姑在我们当地那也是大筛子面上的人,饱受尊敬的,但小舅对她不过就是很平常的客气,表姑几次敬烟,小舅都给推了。虽然他个子矮小,但坐在人群熙闹的稻场上,表现出的那股有知识有文化有本事又有钱的气势,让我觉得小舅真的像庙堂里塑了金的菩萨,宝相庄严。
晚上最后一场宴席完毕,写账先生将人情簿交给我爸。爸妈连夜在灯下对账。我爸看完账本像是怕漏了什么,又从头翻了一遍。我妈问,你还查什么?这礼金跟账目是对的。
我爸疑惑地说,我在找玉寿。你弟弟莫非没上情?
我妈“嗯”了一下,似也觉得奇怪,但转而说,没上就没上,他大老远地为你这场事赶回来,就已经是很大的人情了。
我爸说,这个我知道,我不是争他的人情,只是奇怪,你说他千里迢迢的人都赶回来了,上个人情那不就是挖苕扯蔓子顺带的事吗。
我妈顿了顿,似怕我爸在此问题上过多纠缠,说,哎,人情再多总是要还的,他今天往我这屋里大匾下一坐,我觉得我这新屋都不一样了,蓬荜生辉。我爸嘿嘿一笑,夸赞我妈蓬荜生辉这个成语用得好。
我妈之前就教给我一句话,说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小舅从深圳坐火车转汽车,那时荆州与松滋还没有架桥,隔着一条长江,得转一次轮渡,然后又是汽车转麻木,路不平,那坐麻木的滋味可不好受,浑身骨头恨不得要颠散架,然后还有三四里小路得靠双脚亲自走,这么一段隔山隔水又隔岩的远路,小舅能回来一趟确实不容易。而且今天贺房子,我们家的亲戚六眷都来齐了,他们看到了我们家的大匾,看到了我们家的“贵戚”,还看到了我们家因这位“贵戚”有可能出现的光明未来。
我躺在床上跷着腿说,爸,其实小舅也送了礼,如果说大舅和姨妈们送的是物质意义上的大匾,那么小舅送的就是精神意义上的大匾。
我把话一说完,我爸妈都齐声喊“呀”!然后我妈忽然捧着我的脸左右狠狠亲了一下,说,这才是我们家今天最值得庆贺的事,我们家的小春来长大了。
目录
001固若金汤
087舅舅的光辉
167牙印儿
225祝你好运
305丰收之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