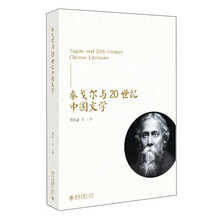《汉魏六朝书信研究》:
3.礼仪性
作为应用文的一种,书信必然要讲求格式。书信作为私人交往中运用最为频繁和广泛的载体,古人对其礼仪要求实际上是烦琐而细致人微的。
书信在一开始就不是一种随意的交往方式。书信的用语、用字,实际上都是书信礼仪性要求的一种体现,早期书信将日常的交往礼仪变化融入书信的用语中,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秦汉立仪”之后,书信的基本形制得到了确立,这一过程实际上也是书信礼仪逐渐形成的过程。
当然,书信礼仪的要求开始并不是特别严格,或者可以说并非一种硬性的规定,只是出于日常交往中的习俗,尤其是朋友间的交往。然而书信并非完全是身份平等的人的交往,“秦汉立仪”时不仅将奏章议表与书信进行了分割,也对书信中奏记和书笺做出了不同的要求,这一点刘勰《文心雕龙·书记》篇总结得最为清楚:“原笺记之为式,既上窥乎表,亦下睨乎书,使敬而不慑,简而无傲,清美以惠其才,彪蔚以文其响,盖笺记之分也。”西晋时留存下来的《月仪帖》表明,朋友之间的交往也有着固定的礼仪规定,且在彰显才情的作用下,书信的礼仪性也愈加雅致。南朝时,琅琊王氏的书仪成为大家写信时必须遵守的礼仪,礼制的要求成为书信的硬性要求,并且在上层社会普遍流传开来。无论是婚丧嫁娶,书信中的礼仪都成为关注的焦点,也是家族地位和身份的一种象征。书信中的礼仪被极度强化,有时甚至高过书信本身的内容,复书中上纸所写的内容虽是冠冕堂皇的客套话,却能从侧面反映出书信礼仪的被重视程度。唐宋时期,魏晋南朝的书信礼仪被继承,并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变革。敦煌书仪中的对于不同状况下书信格式、用语、用典等的详细分类和记录,充分说明书信交往过程中礼仪是被高度重视的,书仪也成为写信不可或缺的工具。书信的礼仪要求,在历史的发展中,不断地下移至民间,成为普遍采用的一种形式,很多书信用语一直延续至今天。
在书信礼仪的规定下,无论是用语、用字还是用纸、封缄,都有着严格的规定,可谓影响深远。与书对象的不同会带来礼仪上的差异,如家书往往是家庭成员间的书信,一般较为随意,而与他人通信时,往往要特别重视措辞,同样是陆云的书信,他的《与戴季甫书》《与杨彦明书》同《与平原兄书》相比,风格迥然不同。与书对象不同所带来的礼仪上的差异,这是很好理解的。需要注意的是,因为礼仪性的需要,与书中如果特别讲究措辞,复信者在复信用语上也同样会斟酌,这应当是书信礼仪作用下的一种交互现象。交互现象的出现,实际上加强了书信的文学性。如果与书的文学性很强、用语典雅、文辞优美,那么,复信时的写作往往也有文学性逐渐加强的趋势,这种交互性也引导书信在文学性不断加强的过程中,出现“滚雪球”效应,曹魏、齐梁时期文学水平颇高的书信集中出现,与此不无关系。
4.审美性
较之于实用性、私密性与礼仪性,书信的审美性是其能立足于散文之林的最主要因素。审美性,历来是文学理论研究中的难点,何为“美”也早成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争论性话题,然而这不是本书所要讨论的问题,笔者只从真、自由和书法艺术之美三个维度来探讨书信的审美性。
以实用为目的的书信,实用性如何演变出审美性,集实用与审美为一体?赵树功在《中国尺牍文学史》中谈到尺牍由实用性转化为审美性时,认为情感的郁结、历史的距离感和淡然之趣等因素造成了实用与审美的转化。赵先生的观点,与笔者的观点基本相同。本书伊始,笔者在探讨书信何以能作为文学作品出现时,从情感和距离(包括空间距离和时间距离)两方面进行过论述,这自然是书信从实用到审美不可或缺的因素。
情感之于书信,实有灵魂主宰作用,其首要的要求是“真”。《庄子·渔父》说:“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故强哭者虽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强亲者虽笑不和。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