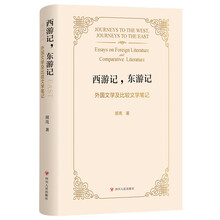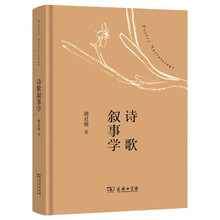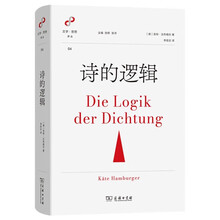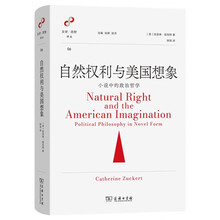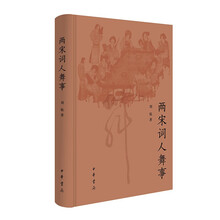王维将这个景点取名“漆园”,本来就很有意味。庄子曾为漆园小吏,主督漆事。或曰“漆园”乃古地名,庄子曾在此做官。不管怎么说,庄子与漆园密不可分,提到漆园就会想到庄子,“漆园吏”也成为庄子的别称。《史记》卷六十三《老子列传》附《庄周传》中说: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庄周笑谓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独不见郊祭之牺牛乎?养食之数岁,衣以文绣,以入大庙。当是之时,虽欲为孤豚,岂可得乎?子亟去,无污我。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你庄子不千也就算了,干嘛要嘲讽来使,羞辱命官?这不是狂傲又是什么呢?因此,庄子也给世人留下了一个“傲”的印象,而多称庄子为“傲吏”。郭璞《游仙诗七首》(其一)曰:“漆园有傲吏,莱氏有逸妻。”郭璞《客傲》又曰:“庄周偃蹇于漆园,老莱婆娑于林窟。”郭璞每每将庄子与老菜子并举,意思是,庄子漆园为吏是一种狂傲不逊,老莱子隐居林窟是一种潇洒自适。而庄子之漆园,则成为庄子之后的失意文人所特别看好的失意去处与生活方式。
《漆园》这首诗的写法,也非常有意味。《辋川集》二十首诗,一首诗写一个景点。在写法上,前十九首诗皆写景,这最后一首叫《漆园》的诗却侧重于议论。这似有“卒章显其志”的意味,似乎是在解答:我为什么乐山水而不疲,我为什么要以漆园命名一个景点。《漆园》诗通篇议论,准确地说是“辩”,为庄子辩。庄子明明是个“傲吏”,旷世“傲吏”,在某种意义上,古来也真没人比他更“傲”的了,简直是不可理喻的“傲”。然而,王维则说他不傲,说他不是傲吏,这自然就让人看不懂了。“古人非傲吏,自阙经世务”二句意谓:庄子不是傲吏,他是自知无经世之才具,而不想去揽相国这活儿。这是庄子对自身角色的清醒认识,也是对其当下站位的正确选择,而没有认知迷失和角色错位。或者说这叫做“错位发展”,就是行为主体根据自身条件,选择了一种与众不同而适合自身发展的方式和路径来谋求发展。这是一种摆脱困境或培育优势的求异思维和生存智慧。怎么能够说是傲呢?
“偶寄一微官,婆娑数株树”二句,似为举证性质的自圆,解释“非傲吏”的观点。两句意谓,做一微官,而兼得“婆娑”生意。前句是说只需要简单的物质条件,后句则是说却获得了富足的精神享受。原来庄子是追求自由啊,自由大于一切,惬意就是所有,洵为人生之大智慧也。庾信《枯树赋》中有“此树婆娑,生意尽矣”的说法。王维以婆娑喻树,取枝叶纷披而生机勃勃之意,喻指山林之隐居,是他效法庄子所谓“傲世”的人生理想。于王维看来,这怎么能说是“傲”呢?怎么能说庄子是“傲吏”呢?他连漆园吏这样的微官都乐意去做,难道能够说他“傲”吗?其实,这是王维在借题发挥呀!王维为什么会有此创作感发呢?一定是他王维亦官亦隐的行举也遭人诟病,被说成是“傲”了,当成“傲吏”了,于是便借庄子以自写自喻,表白自己的隐居,决无傲世之意,也非满足现状而不思进取,而是一种自甘淡泊的人生态度,这种摆脱物累心役的精神超越,则是一种鱼与熊掌两者兼得的生存智慧。
原来王维是在为庄子辩,准确地说是他借为庄子辩之名而行为自己辩之实,也主要是在为自己“辩”。他非常心仪庄子,而以庄子自视,一介微官,几树婆娑,仕隐通兼,两全其美。王维巧于用典,根据自身的特点,放大了庄子“行隐两适”而恬淡自足的人生态度与生存智慧。关于这一点,朱熹能解,也非常欣赏,成为王维的精神知己,而有“余平生爱”“余深爱之”之说。然而,要真正做到一介微官、几树婆娑谈何容易,故而,朱熹也便有了高“不可及”的愧叹。
这为什么让大多数人不能读懂呢?之所以“领解者少”,是因为非黑即白的思维两极,是因为非仕即隐的评判极端,不能理解这种“亦官亦隐”的人生态度与生存智慧。同样是追随漆园高风,王维就不是魏晋风流的那一种。著名历史学家柳诒徵一针见血地指出:魏晋“旷达之士,目击衰乱,不甘隐避,则托为放逸”,其实乃“故作旷达,以免诛戮,不守礼法,近乎佯狂”。①柳先生认为,魏晋人放浪山水不是一种真正的闲适,而是狂狷,是一种以破坏礼法为手段的怪诞佯狂。这种放达形式,根本谈不上适意会心,而是一种非“正常”性的内心蹂躏,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自戕性对抗,是非到万不得已而不如此的人性人格扭曲。当今著名禅学大师铃木大拙说:“禅要一个人的心自在无碍,不能戕害精神本来的自由。”比较起魏晋人,王维才是真正读懂了庄子的人,体悟到庄子的精髓,“偶寄”而已,“婆娑”适意,物质与精神两可,悠哉乐哉。他顺应天命而安于自然之分,从闲逸和虚静中找到了安顿生命的方式和人生原则,而生成高蹈超逸的主体精神,表现出以安命养性为宗旨的“漆园”境界和生命自觉。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