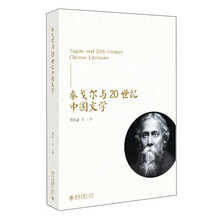再考察1949年以后、特别是“十七年”时期的红色经典,我们会发现,民族革命战争背景下的女性又成了另一种模式——“女战士”模式,即将女性彻底男性化,成为革命/战争中的枪杆,比如《野火春风斗古城》里的金环、银环,《铁道游击队》里的芳林嫂,《新儿女英雄传》里的杨小梅,等等。这些作品与人物都较为简单,对女性做“减法”,将女性人物简化到最低限度,与男性战士/革命者差堪比拟。
在这些作品中,战士/革命者的身份是具有优位性、排他性的,其他身份相较之下必然是微不足道。这不仅表现在它比其他身份更重要,更表现在对其他身份的彻底摒弃。于是,牺牲一己私利乃至自己、爱人或亲人的性命以维护革命利益也就势所必然。这些作品一定不遗余力地将选择时的诱惑、痛苦、短暂的犹疑以及最终忍痛后的斩截无限放大,不吝以最动人的笔触渲染其间的张力。也正因此,这些小说基本看到开头便能猜到结尾,呈现出模式化的面貌。这样的模式化,也正是意识形态宣传所需要的。
不过,女性本应有着多重身份,比如母亲、妻子、朋友、情人、国民、革命者等,也因此注定会有多种情感和人性的向度,她会爱孩子、爱丈夫或者情人,也会爱国、献身于革命。但为了意识形态宣传的需要,文本难容多重话语的共存,私人话语因为宏观话语的鼓荡而被芟减净尽。在1949年以后,民族主义话语的正当性当然不容置疑,作品也只需突出表现女战士,表现其爱国热情与能征善战,其他的人性向度早就可有可无,遑论女性独有的向度。战争中的女性形象也便单一化、模式化。如此想象战争中的女性、如此呈现人性向度显然太过简单。
但是,在《秘密的故事》中,小说至少为我们展示了民族革命背景下女性的四个维度:情人性、妻性、母性、暴力。借用路德维希“克娄巴特拉传”的标题,可以概括为:情人、母亲、战士、妻子①:
一、情人。袁倪对青子的眷恋无时或已,一俟重逢,更显炽烈。与此同时,青子却对袁倪早已失去兴趣,只是心系抗日大业,因利用袁倪对抗日仍有所帮助,才与之虚与委蛇。袁倪对此并无感知,沉溺其中不能自拔。袁倪的一厢情愿和青子的周旋不已形成张力,成为小说主要的推动力。行礼如仪的夫妻之情当然不能有此伟力,唯有逾越伦常的虐恋情深才能成为摧枯拉朽的洪流,席卷着袁倪抛妻弃母,一路忘我狂奔。这虐恋正如青子给他的一吻:“然后她吻住了我一面的脸颊,许久,不肯放开我,好像要从我脸上吻下一块肉,才是终了。”夹杂着快意和痛苦的诡异感觉,使袁倪既害怕又沉迷不已。
二、妻子。青子在小说中扮演着妻子的角色。小说对青子和她丈夫之间的情况交代很少,我们却可从不多的文字中略窥一二。青子当年嫁给丈夫后,便随他一起投身民族革命。两人同为义勇军战士,不得不服从大局,因而聚少离多,根本难以顾及家庭的经营,青子因此对于自身妻子的角色和身份投入甚少。两人之间虽然感情平淡,但也有夫妻之情,这从送别时的细节不难看出,只不过,两人其实更近于并肩作战的同志关系,夫妻之情被民族主义伦理整合进了自身的逻辑,实际上已被湮没、销蚀。
另一方面,小说对叙事人袁倪的妻子苓子着墨甚多,并将她的贤惠写到极致。与青子不同的是,苓子扮演了典型的“妻子”角色,这一身份几乎占据了她的整个生命。诡异的是,越是铺陈她的贤惠,越是反衬出她作为妻子的无力。苓子日复一日、无怨无悔的付出,抵不上青子的一个小动作、一句软语温言,数年来日积月累的夫妻之情,也抵不上年湮代远的旧爱。或许,我们从中并不能读出袁倪对青子有多深的情意,反倒看出“妻性”在“情人性”面前的全面溃败。试想,若是当年青子与袁倪成婚,她的一言一行还能如此魅惑?
三、母亲。相对于“五四”小说对母爱的极力歌颂,这一小说则要复杂、暧昧许多。小说中,青子和丈夫育有一女一子。起初,作为母亲的青子对孩子的情感是毋庸置疑的,只是因为难以从民族革命中抽身:并未尽到母亲的责任,两个孩子长期无人看顾,她为此饱受煎熬。丈夫死后,随着她对革命的越发狂热,革命已然成为绝对律令,病子又成了拖累,她必须结束这一两难的局面,而杀子后的狂笑正印证了她内心的痛苦——她对孩子有着太多不舍,只不过,对民族主义伦理的偏执已使她丧失理性,逼得她亲手绞杀了亲情伦理。
袁倪与其母亲的关系也耐人寻味。母亲爱袁倪,但这其中有无私,也有自私,她也伤害了袁倪,有主观导致的,也有无意为之的,因而,袁倪对母亲也是爱憎交加。小说一开始,“我”便交代,自己爱着母亲。可是,当母亲为了让“我”断绝旧爱,藏起了仅存的青子旧照,苦寻无果后,“我”竟这样描述母亲:“‘你找什么?’母亲问我,她的声调,很不自然,仿佛有些惭愧,有些虚伪,有些愤恨。”“我”向苓子提出离婚,母亲不允,并说除非在她死后。于是,当深夜街上乞讨者的手风琴声声入窗,“我”竟起了诡异的念头:“‘要在我死后!’这句话引起了我一种幻想——想象那琴声是母亲的葬曲了。”对情感的各个隐秘面、阴暗面的钩沉,造就了这一小说的暧昧与深度。
四、战士。有革命伦理打底,暴力的使用也便获致了正当性,“暴力革命”本是偏正词组,却几乎成了人们习以为常的同义反复。不暴力,怎么能荡涤旧迹,通向未来?人们不会有阿伦特的洞见:“革命”一词虽由来已久,本指英国式的“光荣革命”,直至法国大革命以后才染上了血与火的雄浑色彩。这一偏至背后,可能是目的和手段的倒错。①当女性成了女战士,怎能不暴力甚至嗜血。舒群不动声色、详细入微地描述了青子杀子的暴力场景,看似冷静客观,不加评论,立场却隐然由叙事人之口托出。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