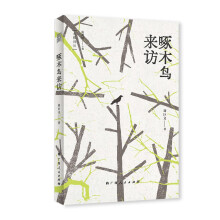《“他者”幻象与身份建构:异域题材作品研究》:
异域题材作品的跨文化写作首先与形象学有关。比较文学意义上的形象学研究与一般的形象学研究不同,它研究的是异域形象,即异国异族形象,而不是一国之内的形象。因而比较文学的形象学本身适合用来分析异域题材作品。晚清域外游记是国人第一次有规模地走出国门,睁眼看世界的行旅记录,郭嵩焘、王韬、薛福成等使官的域外游记建构了国人对西方社会的集体想象,重塑了中国自身形象。“这种文化想象不是简单的先验于文本或视像的现实复制物,而是以直接体验的方式,以注视者自身的文化模式为基础,通过注视者和与读者的集体行为建立起来的复合想象,是中国文化共同体的经验投射。”①他们以晚清知识分子的立场,认同和维护中华文化共同体,但在异域场景的凝视下,晚清帝国的衰败显露无遗,西方社会的现代化信息注入中国传统的社会集体想象,原有的根深蒂固的华夏中心主义话语开始动摇。域外文化成为社会变革和文化转型的契机,他们是睁眼看世界的先行者,在重构晚清对于西方的集体想象中担任重要角色,他们很大程度上是清代乃至后代中国人对西方社会集体想象物的建构者。但华夏一夷狄的思维模式真正转型是在甲午中日战争之后,“西化”后的日本打败了晚清帝国,这彻底击碎了中国的文化自信,千年的中日关系彻底颠倒,中国开始向日本派遣留学生,通过日本学习西方文化。由近代留日热潮催生出来的留日作家群体,以郭沫若和郁达夫为代表,他们的域外题材作品代表了近代中国人看世界的眼光。中国留日学生再无晚清使官的文化自信,他们的留日体验充满了屈辱与痛苦。明治维新后的日本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综合国力显著提高,留日学生对日本的感情除了仰慕之外更多的是痛苦,日本国内弥漫着歧视中国人的氛围,在日本人眼中,中国是一个停滞萎缩的封建帝国。外来的身份使留日生在爱情、学业、生活等各方面处处受挫,弱国子民的自我形象设定取代了天朝上国的文化自信。而南洋开发时间较晚,中国近现代作家笔下的南洋形象带有异国情调,是大中华文化优势心理运作的结果,但中国与南洋的关系不同于东方与西方的关系,两者之间不是对立的,而是保持温和的距离,中国作家描述南洋不是俯视的姿态,更多的是借南洋回望中国,寻找中国文化之根。许地山讲述南洋背景的婚恋故事,目的是探讨普世的终极价值,他言说的是融合佛教、基督教、道教、儒家等各种思想的人生价值观,他是站在中国的角度看南洋的。林语堂的南洋题材小说《赖柏英》反映的是他晚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回归态度。林语堂对初恋情人赖柏英精神的依恋充分体现了他的“山地人生观”。
西方人眼中的东方形象表现为两极,要么是被理想化的乌托邦世界,要么是被妖魔化的人间地狱,前者是为了超越社会想象,后者是为了巩固社会想象,反映的都是形塑者的文化欲望和文化利用。海涅笔下丑陋的、被妖魔化的中国形象并非真实的中国,而是作家附和西方社会集体想象物的结果,他加入了同时代的负面中国形象的大合唱。詹姆斯·希尔顿笔下的香格里拉世界在中国的西藏,是被理想化的人间天堂。但香格里拉并不是一个真实的地点,而是作家想象出来的,它是经历过“一战”和1929年经济危机之后的西方人想摆脱精神危机的诺亚方舟。美国电影动画片《功夫熊猫》反映了进入二十一世纪新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的特点,“功夫熊猫”是用文化同化的形式表现当代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其反映的中国形象较为客观,需要注意的是,它虽然运用了大量的中国元素,但深层传递的却是美国的文化精神,熊猫阿波的成功模式是美国西部牛仔式的而不是中国式的。芥川龙之介的《中国游记》反映的是近代日本人的中国观,他们通过想象古典美的中国来保持对脱亚人欧后的日本现实批判的文化欲望,同时在日本的“东方主义”影响下,对现实中国极端蔑视和憎恨。格雷厄姆·格林笔下的东方是落后的、失语的,但又是神秘的,需要被了解的。
异域题材作品的跨文化写作与离散关系密切。全球化带来的大规模的“越界”群体给跨文化写作带来契机。跨文化成为许多离散作家的生存方式和精神体验方式。二十世纪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特别是九十年代后半叶,其中大部分都是离散作家,作家们以跨文化经历为资源的创作成为世界文学的重要支流;本书所论及的海外华人作家大多是海外移民,他们长期居住国外,异域的政治、经济、文化对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文化观、家国意识等产生巨大影响,他们处于中外文化交汇点上,有明显的文化对比意识。母国文化积淀与居住国新的生存体验合成的离散经验成为他们创作的资源,这使得他们的写作明显有别于单一文化背景下的作家创作,他们不局限于一时一地的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