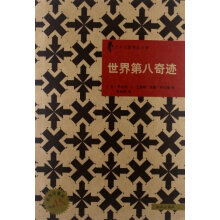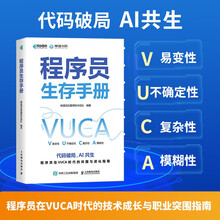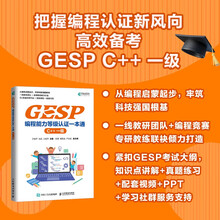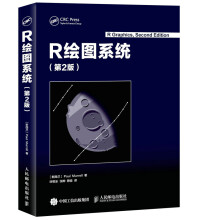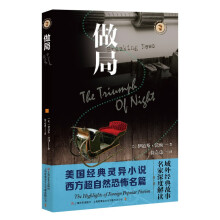《断裂与延续——傈僳族文化变迁研究》:
2.宗教组织
傈僳族信仰万物有灵的原生宗教时,并没有独立的宗教体系,通灵人虽然有影响力,但他的影响范围是神圣领域而不是世俗领域,又因为傈僳族宗教是非理性的松散的自然宗教,且有巫术性质,所以也没有独立的教会组织。
自从傈僳族信仰基督教后,传教士下了很大的功夫使傈僳族基督教理性化,成为有经典、有仪式、有教会组织的体系化宗教。宗教组织一跃成为傈僳族文化体系内的重要组织,教会领袖也成为重要的权威人物。在传统社会傈僳族村落中谁是最有影响力的人物?那无疑是教会领袖。教会领袖成为村庄秩序的维护者,公共事务的组织者。他的影响力不仅仅存在于精神领域,也存在于世俗领域。村中孤寡的照顾、贫弱的扶持、家庭纠纷的解决、人生礼仪的完成都由这些教会领袖来负责。
教会领袖们还是婚姻的撮合者,一方面是他们经常有机会参加宗教培训,有机会与跨村落的宗教领袖们结识,因而掌握更多的信息,包括双方家人的生活状况、当婚者的品性等;另一方面也因为这些教会领袖的威望也是一种担保,将来婚姻中万一产生矛盾,这些教会领袖有义务来处理。所以,家长们总是托教会领袖带着当婚男青年去本村或他村找对象,本地人叫作“问姑娘”。所以,婚姻圈与教会领袖的交往圈几乎是重合的。随着交通通信的发展,这一圈子近些年来逐渐扩大,甚至扩大到缅甸,我所住的房东的三儿子的妻子就是缅甸人,通过傈僳族教会领袖结识,在教堂中举行婚礼。2019年,四儿子也通过教会在缅甸一带物色到合适的结婚对象。
所以,傈僳族的教会组织在文化网络中占着极重要的位置,而文化网络的权力结点也在教会领袖那里,虽然这结点并不固定在某个人身上(像当年的约秀那样),而是在教会选举时在各亲族激烈的竞争中不断地更替。
3.政治组织
如同宗教组织一样,传统社会傈僳族也没有专门的政治组织,亲属结构承担着此种组织功能。自从殖边队直接管理边疆地区后,才产生专门的政治性组织的萌芽,最初是伙头、保长、甲长之类的职务的设立,但是这些人仅仅是国家与地方之间信息传递的联络人,而不是国家代理人。到上帕一带成立设治局后,头人迫于政治上的压力,出于自保的目的,与政府逐渐联系多了起来。在这种交往中,头人也的确能获得一些益处,他们逐渐成为代理人。但是,这些代理人远远没有宗教组织领导人的影响力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可以说他们远不是文化网络中的中心结点,而是在较边缘处。此时,他们在乡村中几乎不能借助政府之名实施横暴权力。文化网络中以传教士为核心的同意性权力、教化性权力占据中心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传教士被从傈僳族文化网络中清理出去。政府对地方文化网络实施很有限的横暴权力,更多是使用以威望服人的时势性权力。政府与地方文化网络之间展开良好的互动。到了“大跃进”与“文化大革命”时期,受错误思想的影响,地方社会权力的文化网络被忽视,村落中国家代理人使用横暴权力过多,造成很多负面影响。到了改革开放后,地方社会权力的文化网络再度受到重视。随着国家的日渐强大,在地方社会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国家代理人在权力的文化网络中与教会领袖一起占据着中心结点的位置。
4.文化网络与集市
集市是一个连接文化网络内外各种组织的重要因素。傈僳族的集市是以星期为周期的,比如某些地方定为星期二、某些地方定为星期五,总之是星期天之外的某一天。星期天是安息日,除了去教堂聚会,一般不做农事,当然也不会去赶街天。
傈僳族集市是殖边队进入后才逐渐出现的。之前,因为交通的阻隔,峡谷内外没有互通有无的商贩。有了国家力量在治安方面的保障后,外地商贩才逐渐进入峡谷内。不过,那时交易非常少,峡谷内的人基本上过着自给自足的日子。随着峡谷内外交通的改善,傈僳族与外界在经济上的交流增多。怒江峡谷内盛产优质黄连以及麝香、熊胆、动物皮毛等山货,交易多是以物易物的形式。“查上帕地面,银币尚未通行,即生银、铜、铁亦不使用。汉商与怒族、傈僳族等交易,向系以其所有,易其所无。现在逐渐进化,银币虽已通行,而零星菜蔬等物,仍以盐布互相更换,以物易物之俗尚不能免。”①这是边疆开拓之初的情况,后来,随着交易越来越频繁,货币使用逐渐普遍。
怒江一带街天的周期以星期来计算,所以集市应该是在基督教传人后才设立的。但赶街天真正成为村民们不可或缺的日常活动应该是从改革开放后才形成的,一是因为有购买力的人口迅速增加;二是因为人们的货币拥有量迅速增加,购买欲也相应地越来越旺盛。
施坚雅从市场体系的角度研究中国社会,因而声称市场体系理论可以解释中国乡村社会,市场体系把一个个乡村联结起来,呈六边形。而在山地受制于交通则是珠串形状②。杜赞奇认为,市场体系与其他组织一同联结为文化网络。因为集市中村民纽带在提供多种服务、促成交易,市场体系及村民纽带联合决定了乡村经济交往③。对于傈僳族来说,市场体系的确成为文化体系的一部分,因为村民赶街时与沿途居住的其他人的交往使同一村落的文化网络周期性地产生互动,也与周围村庄的熟人之间产生连接。平时,人们各自参加生产活动。参与宗教活动时,也以各自的聚居点的教会为活动范围。除了重大宗教节日外,一般不举行全村参加的宗教活动。街天就成为交通不便的山民们的重要社交活动日。人们三五成群地去买东西,边走边聊,还会在沿途去看望自己的亲戚朋友,在那里歇歇脚、喝喝茶。所以,街天成了各个聚居点交换信息的时刻,形成村庄舆论的时刻。购买物品时的交往仅限于表层信息交换,沿途的闲谈反而是交流对公共事件的态度与感受的重要时刻,也是对村落中权威人物评头论足的时刻。至于村民纽带是否能在经济活动中提供服务、促成交易,其作用力倒不怎么明显。
(二)国家权威在傈僳族乡村权力的文化网络中的在场
国家是抽象的、不可见的,但国家以某种形式表达出在地方权力文化网络中的在场,这样才能使国家的管理有实实在在落实的场域。所以国家或以符号形式在场,或让某些人物代表国家在场,或以国家的直接行政干预在场。
1.以符号形式表达国家的在场
国家在里吾底村最明显的符号是飘扬在村委会院落上空鲜艳的五星红旗及那整洁而坚固的村委会办公室。2007年时,村委会的房子是国家拨款修建的,与周围用竹子和木板搭成的千脚落地房相比,要豪华许多倍,门前有一大块用水泥铺成的开阔地带,建有供村民娱乐的篮球场。在到处是陡坡的山石地面上造出这样一块约500多平方米的空地,其成本是相当高的。没有国家力量的参与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就是在2018年时,虽然周围盖起了漂亮的楼房,村委会依然是较宽敞气派的建筑物。
在里吾底村每个寨子都可以看到直径5厘米的铁制自来水管道,这些管道把山上的泉水直接引到村民家门口,并修了蓄水池,世世代代背水吃的傈僳族现在一伸手拧开水龙头就可以接到水了。这些自来水管道由国家投资修建,也是国家在场的有形表达。除此之外,里吾底村还有一种国家在场的符号表达,就是山坡上覆盖在全村五个寨子上空的两个网。一个是电网,一个是信号网(固定电话线路和移动通信的信号塔),这两个网源源不断地把国家的各种信息输入进去,也随时能把村中的信息反馈到国家各有关部门。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