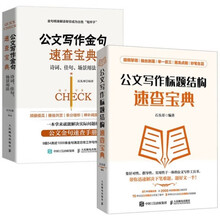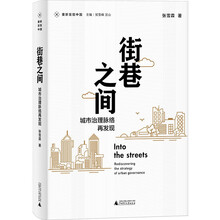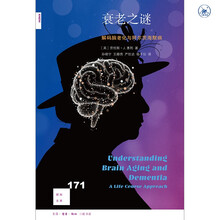《落脚县城:县域城镇化的农民参与机制研究》:
传统中国农民是生活在“乡土社会”中的,其生产生活的场所和组织形式离不开农村和土地。家庭是农民生产、生活、公共服务、社会交往的组织单元,大部分功能在乡村社会中完成。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流动社会形成,越来越多的农民从农村进入城市寻求就业和发展机会,农村劳动力就业开始走出封闭的乡村社会空间。在打工经济背景下,农民在农村人地关系紧张的压力下被迫进入城市寻求“生存机会”,以获得城市较高的打工收入为主要目的。这一时期农民的流动遵循着周期性的城乡往返规律。对于城乡往返的务工者来说,生产生活的重心还是家乡的乡村社会,遵循着家庭再生产的乡土逻辑。农民以在县城为主的家乡中小城镇购房为标志,越来越多的农民及其家庭开始走出乡土社会,“由乡入城”实现了农民生产生活空间的全面扩展,进入现代性的城市社会来组织家庭生产生活和劳动力再生产。
在中国长期以来“城乡分治”政策的影响下,城市和农村代表着两种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是两种不同的社会文化类型①。虽然农民长期的城乡流动,使农村与城市的关联互动更加频繁和紧密,但是城乡之间的差异和差距并没有从根本上消失。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相似,中国的城乡差距依然明显,城市与农村是“两个不同的世界”,城市和农村生活的组织方式不同。相对于传统农村的自然经济和自给自足的生活特征,城市的首要功能是经济,这也决定了城市是一个“经济联合体”,是一个“市场定居点”②。农民购房进入县城,从乡土性的农村社会进入市场化的城市社会,不仅意味着其生产生活的空间发生了转移,而且其生产生活组织方式也逐渐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传统农民与村庄和土地相结合的生产生活组织方式,在“由乡人城”之后发生根本性变化。这种转变不仅体现在空间层次,而且更主要体现在农民的就业、日常生活和社会交往关系等方面,传统的乡土组织逻辑逐渐被现代城市、市场的组织逻辑替代。
首先,进城农民的就业越来越深地嵌入城市劳动力市场之中。在以农业为主的乡村社会中,农民的生产劳动是通过自身的劳动力与土地结合实现的。农业生产是农民最根本的劳动力就业方式,土地是农民最主要甚至唯一的生计来源。打工经济兴起之后,农民家庭劳动力不断向城市转移务工,绝大部分的农户通过“半工半耕”的家庭劳动力分工模式,依然保持着与土地的联系。随着农民由乡入城,农民家庭劳动力就业方式和家庭经济来源也变得以城市非农就业和收入为主。这意味着农民与城市劳动力市场的结合更加紧密,嵌入以分工为基础的城市职业体系的程度不断提高。在我国城市工商业快速发展和市场经济制度确立的背景下,农民通过乡城流动的打工模式,促进了“全国统一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农民“落脚县城”之后,其就业实际上遵循着劳动力市场的组织方式和运作逻辑,通过“劳动力”与“市场”的结合,是进城农民劳动就业的主要组织方式。农民进城也意味着进入城市精细化的劳动分工体系中,他们的职业也变得专业化,而不是传统自给自足环境下的“综合性”生产,进城农民也只有通过从事一种职业来维持日常生活的运转①。农民与城市劳动力市场的结合能力和结合程度,从根本上影响了进城农民家庭经济发展能力,决定着他们能否实现在城镇体面安居的城镇化目标。
其次,农民进城之后其日常生活所需的公共服务资源和生活资料来源,越来越依赖政府和市场来提供,拉近了农民与国家和市场的距离。传统农业社会中生活的人们,依靠农业生产和家庭副业的结合,其生活实现了较高程度的自给自足,农民在乡村生活的货币化和市场化程度较低。进城农民日常生活需求的货币化和市场化程度快速提高,高度嵌入城市商品市场环境中。正如进城农民所言“在城里什么东西都要花钱买”,农民日常生活的物质需求依赖市场的提供,通过货币化的手段实现。这也对进城农民的就业和经济来源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为没有稳定的工作和较高的收入是没法在城市生活下去的。在乡村社会,农民生产生活所需的公共服务可以通过农村的邻里互助体系和村社集体组织来满足,农民与国家和市场的关联不强。随着国家制度改革和市场转型,农民流动性的兴起,一定程度上瓦解了乡村社会系统内部对农民生活的自我供给能力。尤其是在农民“由乡入城”之后,冲破了乡村社会系统的界限,进入了城市社会系统,对与生产生活相关的公共服务需求更加依赖国家和市场的供给。与农民生活直接相关的,除了城市便利的基础设施带来的生活便利性,对于中西部地区绝大部分进城农民来说,其进城生活最主要的还是为了子女能够享受城市优质的教育资源。正因如此,大部分进城农民的生活是围绕着小孩的教育需求展开的。可以说中西部地区农民的进城生活更为看重的是城市集聚的公共服务资源,尤其是教育资源,而从农村社会向城市空间的转移主要是为了获得享受城市公共服务的机会。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