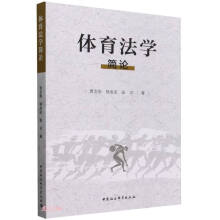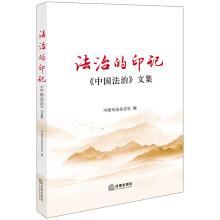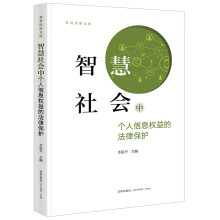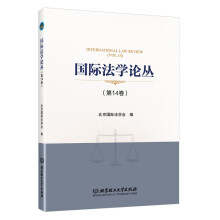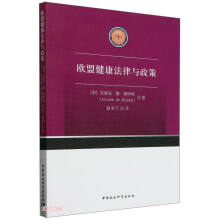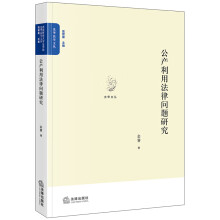《公共警告利害关系人权益保障研究》:
二 中国多元主体参与公共警告的困境
目前,中国公共警告的多元主体参与处于“弱势”和“无序”的状态,主要表现在风险信息来源狭窄、信息不对称、参与过程形式化、科学理性与社会理性冲突等方面。
(一)风险信息来源途径的狭窄
全面的信息采集是信息披露活动开展的重要基础之一。如果风险信息来源狭窄,就不易发现风险,不利于及时发布公共警告。为了有效预防消费事故的发生,日本广泛收集事故可能发生的信息并及时向消费者提供信息。一方面,国民生活中心主要是通过消费者网络来收集消费风险信息,该消费者网络与消费者中心相关的合作医院进行连接,是危害信息制度运营的基础。另一方面,地方消费生活中心是危害信息的另一个重要来源,它们是日本消费者保护的基层行政机构,处理消费者对商品或服务的不满,协助消费者的维权行为,其日常业务内容是商品检查测试。由于它们处于市场流通消费的前沿,所以能比较迅速地发现有危害的商品,及时收集可能存在或发生的风险信息,以弥补国民生活中心的风险信息收集能力的不足。日本注重加强食品安全信息的收集与交流,除了日常收集和沟通渠道,还使用了食品安全追溯系统、公布危险信息等。
目前,我国许多立法规定,行政机关在收集风险信息时大多采用报告制度,这容易导致风险信息在报告过程中的分散和失实,无法快速准确地进行汇集。如果仅仅依靠公共警告的发布主体收集风险信息,方式过于单一,容易漏掉风险线索,因此,需要扩大风险信息来源途径,吸收多元主体参与。公众处于风险的边缘,虽不能完全准确地识别风险,但往往可以提供风险的线索。例如,有必要充分重视公众在地震预报中的重要作用。
(二)信息不对称
目前,多元主体与发布主体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信息不对称,影响了多元主体有效参与公共警告。一些行政机关由于害怕麻烦或社会恐慌,往往不愿在做出公共警告决定之前主动披露风险信息,有时只避重就轻地披露部分信息,导致多元主体与发布主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降低了多元主体参与公共警告的质量。由于许多立法没有规定公共警告主体发布前的告知和说明理由的义务,利害关系人在公共警告发布前很难准确掌握有关信息,更无法行使程序权利。例如,中国《食品安全法》没有规定在发布公共警告前向特定利害关系人告知和说明理由的程序以及保障特定利害关系人陈述和申辩权利,容易导致公共警告决定出现错误。即使《食品药品安全监管信息公开管理办法》第18条规定了利害关系人的异议权,然而,该条款规定的是在公共警告发布后的异议权。这种事后异议的权利并不能完全弥补错误公共警告对利害关系人的侵害。例如,在“农夫山泉砒霜事件”中,海口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没有告知企业检查结果,没有保障其陈述和申辩权而直接发布了公共警告。
(三)参与的形式化
多元主体参与公共警告过程呈现形式化的特点,参与的深度和质量都不高。虽然有些立法规定了公共警告中的多元主体参与,例如,中国《食品安全法》第9条第2款赋予消费者协会的监督权,该法第12条赋予了任何组织和个人举报食品安全违法行为的权利。另外,《食品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都规定了通过风险评估专家委员会制度吸收专家参与。然而,总体来看,多元主体参与公共警告的立法规定不具有可操作性,导致多元主体参与公共警告过程呈现形式化的特点。首先,由于立法没有规定具体的参与规则、专家的遴选、监督等问题,导致多元主体在参与过程中容易被发布主体主导或操纵。其次,多元主体参与公共警告的程序性权利不足。例如,即使《食品安全法》第12条赋予个人举报食品安全违法行为,但这些规定比较笼统,对于公众参与的方式以及程序等问题没有明确规定。行政主体通常喜欢选择“听话”的专家和代表参加论证会,不重视多元主体的不同意见,导致公众参与积极性不高,最终,多元主体参与实际沦为了“走形式”或者变成了公众的“事后举报”。
(四)科学理性和社会理性的冲突
社会理性与科学理性经常发生冲突。社会理性并不完全接受科学理性的解释,甚至形成了普通公众倒逼专家的局面。例如,专家和公众对转基因食品是否安全存在分歧。专家认为,除非有确定证据证明转基因食品有害,否则就不能认为其不安全。而公众认为转基因食品不同于同类传统食品,应该采取风险预防措施。再如,PX项目引起了公众的担忧,但专家表示二甲苯(简称PX)毒性较低。另外,在康泰公司乙肝疫苗事件中,国家卫生计生委、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宣布停止使用康泰公司的重组乙型肝炎疫苗。正如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的副研究员钟凯指出,如果根据科学标准,没有必要停止接种疫苗。然而,风险管理不仅仅是科学问题。对于风险评估中专家委员会的结论与公众的意见不一致时究竟应该如何处理,中国立法对此并没有明确规定。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