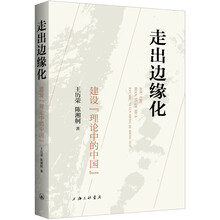(二)三方权益之间的关系
信息披露的作用机制是通过提供信息的方式来影响公众的决策,对上述三种权益的影响发生在同一过程之中,但侧重有所不同。对有毒害食品之警告,以警示公众规避风险为主要目的。对行政“黑名单”,则须区分情况,有些几乎以名誉制裁为唯一目标,有些还混合了风险警示的目的。
从理想的情况来说,这种目标侧重说(混合说)是不正确的。如果公众能正确理解和评价信息,并采取适度的抵制(规避)行动,那么负面信息披露引起的公众知情收益与违法人的名誉受损在量上是完全等价的。亦即,名誉惩罚效果大是公众需要采取更大的风险规避行动,名誉惩罚效果小是只需要较小的风险规避。例如,因性犯罪者的危险性,社会对其的排斥几乎是全方位的,这种更大的风险规避行动与其污名的严重性对应;拖欠税款则反映出履约能力与诚信程度低,社会排斥表现主要是经济交往减少,这种中等的抵制对应中等的污名。
总之,假设公众能正确评价信息,违法信息的名誉罚效果与该信息对公众的知情利益是正好相等的。如此推论,任何违法信息的披露,无论对特定人造成了多少名誉(人格)损害,都会被公众的知情利益所抵消。换句话说,除非涉及国家或商业秘密,任何负面信息披露都是正当的,不存在侵犯名誉权或隐私权(或其他人格权)一说,唯一要求是保证信息的真实性。那么,负面信息披露的问题可以简化为两个问题:一是通过正当程序(并不意味着一定需要相对人参与)保证披露信息的真实性,二是对错误信息披露提供救济。除此之外,不能对负面披露施加其他的法律限制。
但是,现实生活要复杂得多,有几种原因使得上述理想情况不成立。一是出于社会偏见、人类固有的认知缺陷、群体极化与从众心理、不完全的信息结构等因素,使得人们对违法(风险)信息的理解、评价和行动可能不适当,是过度的或不足的。二是关于特定人的违法信息可能被其他不法分子恶意使用,这可以归属为人们熟知的个人信息保护问题。三是行政机关也可能滥用权力,除开正当程序的限制,可能还需要来自法律保留原则的限制。
在这些情形下,公众知情利益、执法效率、特定人名誉损害就会发生不一致。例如,对社会公开卖淫嫖娼人员的违法信息对特定自然人的名誉损害很大,行政机关也能充分认识到这种损害。其配偶等利害关系人也许有知情利益,可向其限定披露,但对公众而言,避免风险的价值很少。①因此,从实际功能看,曝光主要是对色情交易潜在对象的威慑功能,这是典型的惩罚功能。另外,曝光可能造成“污名”的标签效应,即公众可能反应过度,被曝光者修正自我认知(即认为自己本质就是违法犯罪者),造成被曝光者回归社会困难,容易结成反社会的小团体。
标签效应在不同的违法类型中存在差异(曝光超速和嫖娼显然不一样),且其大小如何未得到学界公认。从根本上说,标签效应源自公众不能正确评价违法信息中的风险成分(正如许多人曾将乙肝病毒携带者和乙肝患者等同,以及对艾滋病毒感染者的过分恐惧),并在内心自动且长久地给违法人贴上了一个“累犯”标签,易将被曝光者的正常行动也解释成有害,并采取不必要的抵制行动。这些行动既不利于其自身,也不利于被贴上了“污名”标签的人,甚至造成更广泛的社会福利损失。如果公众能正确评价违法信息,披露对被曝光者造成的“损害”属于正常的社会评价降低,并不有损人性尊严。本书不具体讨论何种情况下披露自然人违法信息是适当的,这需要更多的社会科学研究,但足以指出,它可能面临惩罚过度的风险,反过来伤害了公共利益。
披露企业或其他组织的负面信息则与自然人大不相同。一是公众因交易需要,更有知情利益。但曝光卖淫嫖娼则不同,除了少数特定利害关系人,获知该信息对于社会关系缔结而言用处不大。二是几无标签效应与回归社会问题。自然人的人格和名誉是多方面的,包括个性、道德品行、工作能力等极其广泛的维度,一个方面被贴上了污名标签,人们很容易类推到其他维度,形成了对整个人的否定,但这种类推却难以验证和推翻。因此,对自然人的污名洗刷不易,容易造成“做什么事都是错的”,结成反社会的团体就很有吸引力了。但企业的违法信息则不同,主要是关于产品或服务中的违法或欺诈,一般不发生类推过广的问题,即使发生了也相对容易验证。因此,一般而言,披露自然人的违法信息可能具有超出公众知情利益需要的“额外”名誉惩罚效果,披露企业违法信息引发的抵制可以看成公众的合理规避,不构成“额外”名誉制裁。
基于上述道理,本书以为在信息公开法和隐私法上,只有自然人才有隐私,而企业没有隐私可言的做法是适当的(商业秘密是另一回事)。行政机关掌握的自然人违法信息也属于个人隐私信息,同样地,只有公共利益超过隐私利益时,披露自然人违法信息才是正当的。①例如在美国,《信息自由法》b款第7 (c)项规定,可以合理预期会构成对个人隐私权的无正当理由侵犯时,行政机关执行法律的记录和信息可以豁免公开。此处的“执行法律”是指保持法律不被破坏的行为,包括对违法行为的调查、追诉和防止的行为在内。“违法行为”的范围包括刑事违法、民事违法和违反行政法律法规在内。个人受到的纪律处分、刑事纪录等都构成隐私。②行政机关决定不公开隐私信息时,只需要证明,“可以合理预期”公开会产生对隐私权的无正当理由侵犯,而不需要达到确信的程度。③在许多案件中,法院基于利益衡量,判决违法信息中的个人身份信息不应当公开。例如,联邦调查局收集了超过2400万人的罪犯身份记录。在“司法部诉新闻自由记者委员会案”中,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公开这些记录“构成对个人隐私的无正当理由的侵犯”。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