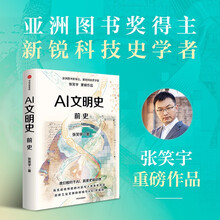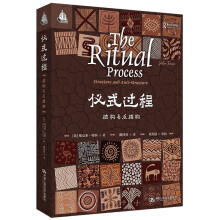《爱尔兰乡下人:一项人类学研究/汉译人类学名著丛书》:
可惜的是,面对我们的追问,洛克村已经没人记得阿瓦隆,而常青之地的传奇似乎也奄奄一息。我们向村里年长者打探西方的含义,听到的却是陷落的城堡和怪异海兽的故事。转而问及仙子和他们游走的小径时,先是遭到对方愤懑的一连串否认,谁会相信那种有失颜面的东西。之后,他们零敲碎打道来的是表现仙子魅力和魔力的轶事、传说和巧遇,既有善行也有恶作剧。待问到西屋里的家具,他们只是回答:那些物件就该摆在那里,仅此而已。看来,无人能追溯还原自古至今的延续;传统不仅在于具体细节,更在于总体感知。
于是,我们只剩下能够听到和看到的眼前。无论我们怎样变着法儿地问,结果都是碰壁,顶多是再听一遍那些模糊不清的笼统说法。村民的答复也变成因问而应的即兴发挥,根本不能反应出洛克村民真实的感受、想法和做法。
但事情还不至于希望全无。如果我们注重对现状的观察和询问,新的事实开始脱颖而出。我们发现,西屋在家里孩子成亲时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拟定的婚约文书中,西屋经常被指名要记录在案。两位老人,即新郎的父亲和母亲,明确要求把它留给自己。这样,在儿子结婚和农庄转交给他后,二老可以将特意保留的西屋供自己用。
顺着这条线索追问下去,更多的信息迎面而来。西屋是老两口将来要搬进去住的地方。这屋子是他们的。不得允许,家里的小辈们不敢人内。两位老人的气场充满全屋;家人对他们与对他俩入住的西屋一样,敬若神明。于此,我们进入了人类关系中行为和态度的新领域。虽然老两口退位下来,不再主导和拥有农庄,但他们的声誉和掌控并未随之而去。老人迈入了新的社会地位,而西屋与恭敬之间的关联恰好折射了这一更新。
新问题和新观察没有把我们引向追究史前时期或历史的前后延续,而是将我们领向更广泛更鲜活的寓意关联,体现了当今男女之间、老年人和青年人之间多彩的社会关系。新问题和新观察还引导我们认识到规则和习俗;有了它们,小农家庭的生活才有稳定的秩序。在这个例子里,洛克村的西屋或许只是远古传说阿瓦隆和常青之地残存的摇曳烛光。但确定的则是,西屋集中代表了一套社会价值体系,并且我们瞥到的还仅是它的冰山一角。就这样,西屋里的古老习俗给了我们前面提到的人类学新方法的第一个例子。在对乡村现实生活的探索中,我们没有走追溯文化传承过程的老路,而是转为对人类行为的方式进行研究。
我要举的第二个例子叫做“老头的诅咒”。这个例子听起来可能令人不悦,而且发生的机率微乎其微。但与前面“西屋”的故事一样,它能告诉我们,田野调查该从哪儿着手。老头的诅咒牵扯到一只眼睛的失明。乡里很多人认定,正是这个诅咒直接导致一个小伙子瞎了一只眼。出事的年轻人住在离洛克村不远的地方;而施咒的老头儿是个邻居。这么交待这档事算是最直截了当的陈述了。如果我们的兴趣只在收集民间的魔法致残事例,调查至此足矣。
咒术、黑魔法和“恶之眼”的邪祸后果,在人类学的文字记载里屡见不鲜。在爱尔兰的民间传说中也很常见。超自然的缘由会使人们受到各种伤害。比如,恶之眼的拥有者能致人枯萎、肢残、甚至丧命;神父的咒诀,即便据理而发,也能让满门兴旺的家庭毁于一旦,让不信教的人中风不起,或是致人双目失明;就连老翁老妇发出的刺耳咒骂,抑或讽刺诗人的韵律谣诵,都会带来类似的不幸遭遇。毒咒致残的传说和凯尔特神话一样悠久,流传至今。对它的信奉还远远超出爱尔兰的疆域。那不勒斯的渔民为对抗“恶之眼”的魔力,重彩漆涂他们出海的船只;巴尔干的女子为抵御邪恶咒语的侵袭,精心刺绣她们的罩裙;西非的巫师把掌控咒术的技法练得炉火纯青;我们宾夕法尼亚的荷裔“巫婆”则是此法的现代践行者。人类对诅咒应验的信奉,是无垠的魔法疆域的一部分。
如果我们满足于咒语故事收集者的直白陈述,便会心安理得地把年轻人的事交给他,一走了之。但是,深入追究一步,我们便会看到小伙子倒霉的整个情形。在可以对其评判的具体情节里观察咒语信奉是如何奏效的,能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种仍然相信诅咒应验的生活是怎么一回事。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