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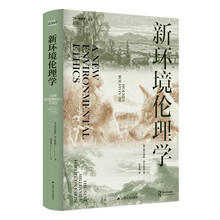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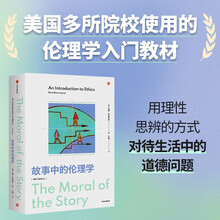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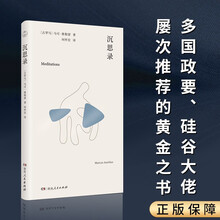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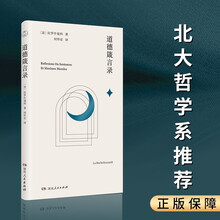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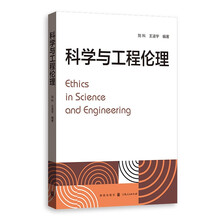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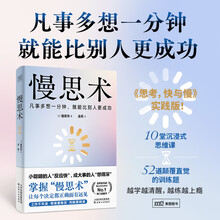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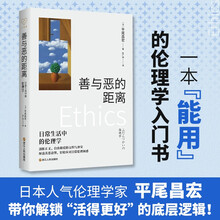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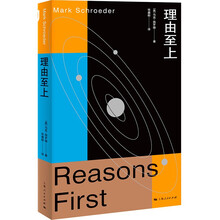
★1、三个层次,说透功利主义:
第一层:功利主义的定义是什么?快乐与摆脱痛苦是值得追求的两大人生目的,要么是我们的追求本身含有内在的快乐,要么就是因为它们属于增进快乐和防范痛苦的手段。
第二层:功利主义的原则和终极约束力是什么?促进整个人类的幸福是总体原则,与生俱来的道德感和对良知的判断力是终极的约束。
第三层:如何从功利角度理解正义?明确受侵害者有哪些权利被侵犯+惩罚侵害者的愿望,其实是功利主义出发的正义观。
★2、译者特别撰写1万字导读,4个方面抛砖引玉读经典:
介绍穆勒的教育经历
概述功利主义学说发展史;
梳理《功利主义》五个章节的内容逻辑
厘清《功利主义》翻译过程中的关键概念
★3、罗翔推荐,他自称被《功利主义》的三个观点深深影响:
一:快乐有高下之分,不要把幸福降格为简单的满足,否则就是对人格尊严的亵渎。
二:美德与幸福并不冲突,是实现幸福的一种手段。因为美德所做的自我牺牲,只有在促进幸福时才有意义。
三:正义是感性的力量,是利益权衡时的指导原则。
★4、正本清源,帮助人们理解“功利主义”这个对于当代人来说又熟悉又陌生的概念!
有一种无知的错误观点,认为那些支持用功利标准来检验是非的人是在一种狭隘的、纯属非正式的意义上使用“功利”一词,从而把功利与快乐对立了起来;对此,我们只需顺带提一下就行。至于在哲学上反对功利主义的人,要是把他们与那些怀有如此荒谬误解的人混为一谈,哪怕只是一时的混淆,我们也该向他们道歉才是;这种混淆之所以更显异常,是因为针对功利主义的另一种常见批评恰好相反,是指责功利主义认为一切都与快乐有关,并且是与最粗鄙的快乐有关。而且,正如一位才能出众的作家曾经尖锐指出的那样,同一类人(往往就是同一批人)还会指责功利主义理论“把‘功利’置于‘快乐’之前时毫不实用的枯燥乏味,而将‘快乐’置于‘功利’之前时又太过实用地耽于感官”。对这个问题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凡是支持功利理论的作家,从伊壁鸠鲁到边沁,都没有把功利理解为某种与快乐相对的东西,而是理解为快乐本身与免除痛苦;他们没有把“有用”与“令人愉悦”或“赏心悦目”对立起来,而是始终宣称,除了其他一些方面,“有用”就是指“令人愉悦”或“赏心悦目”。
然而,普通的人(包括普通作家在内)却总是陷入这种肤浅的错误,不仅表现在报纸杂志发表的文章里,而且表现在一些很有影响力和抱负不俗的著作中。他们揪住“功利”一词,尽管除了发音就对它一无所知,可还是习惯性地用它来表达“拒斥或忽视某些形式的快乐、美丽、装饰或娱乐”的意思。他们如此无知地误用这个词,目的不仅仅是为了贬抑,偶尔也是为了褒扬,仿佛它含有“超越轻浮和纯粹的当下之乐”的意思。可“功利”一词的这种反常用法,竟然是大众所知的唯一用法,而新一代人对该词含义的唯一概念,也是从这种用法中获得的。那些首次采用了“功利”一词,但多年来已经不再把它当作一个独特名目去使用的人,如果认为重新采用这个词就有望做出一定的贡献,把它从这种彻底的堕落状态中挽救出来,他们就会有充分的理由觉得自己必须那样去做了。
承认“功利”或“最大幸福原则”属于道德根基的信条的人,认为行为之所以正确,是因为它们有增进幸福的倾向,而行为之所以错误,则是因为它们有造成不幸的倾向。所谓的幸福,就是指快乐且没有痛苦;所谓的不幸,就是指痛苦且没有快乐。要想清晰地阐明这种理论所确立的道德标准,还有很多方面需要论述,尤其是痛苦与快乐两种观念中包含了哪些内容,以及这个问题在多大程度上允许人们去展开争论。不过,这样的补充说明并不会对道德理论所依据的人生理论产生影响——该理论认为,快乐与摆脱痛苦是值得追求的两大人生目的,而所有值得追求的东西(在功利主义理论和其他任何一种理论中,这些东西都不胜枚举)之所以值得追求,要么是因为它们本身含有内在的快乐,要么就是因为它们属于增进快乐和防范痛苦的手段。
然而,这样一种理论却在许多人心中激起了积习难改的反感,其中有的人还怀有最可敬的情感与意图。他们指出,认为人生的最高目的(像他们所说的那样)就是快乐——即没有比快乐更好、更高尚的追求对象了——的观点极其卑贱而低劣,是一种只配得上猪猡去拥有的信条;在很早以前,伊壁鸠鲁的信徒就被人们轻蔑地比作猪猡,而信奉这一学说的现代人,偶尔也会同样被德国、法国和英国的抨击者客客气气地比作猪猡呢。
受到这样的抨击时,伊壁鸠鲁学派往往回答道,用可耻的方式贬低人性的并不是他们,而是指责他们的人,因为这种谴责中含有一种假设,即除了猪猡享受的那些快乐,人类就不能拥有其他的快乐了。如果这种假设正确,那么他们的指责就是无法反驳的,但它也会由此变得不再是一种非难;因为假如快乐的源泉对人类和猪猡来说完全一样、毫无分别,那么对其中一方足够有益的生活准则,也会充分有益于另一方。把伊壁鸠鲁学派的生活比作禽兽的生活会令人觉得有辱人格,正是因为禽兽的快乐并不符合人类对幸福的概念。人类拥有种种比禽兽的欲求更加高尚的官能;一旦认识到这些官能,那么凡是不能满足这些官能的东西,我们都不会视之为幸福。的确,我并不认为伊壁鸠鲁学派从功利主义原则中推导出其重要理论体系时做得很完美。要想充分做到毫无瑕疵,他们还需要把斯多葛学派和基督教的许多基本原理包括在内才行。但是,如今我们所知的伊壁鸠鲁派生活理论中,却没有哪一种理论会不承认,理智、情感与想象以及道德情操方面的快乐所具有的价值要远高于纯粹的感官快乐。然而,我们必须承认,功利主义作家之所以通常认为精神快乐高于肉体愉悦,主要是因为精神快乐更加持久、更为安全、代价更低,等等——也就是说,在于前者具有的间接优势,而不在于它的内在本质。而且,在这些问题上,功利主义者已经充分证明了他们的论据;不过,他们原本是可以全然一致地采用另一种堪称层次更高的依据的。承认“某些类型的快乐要比其他快乐更值得追求和更加重要”这个事实,与功利原则完全一致。在评价其他所有事物时,我们会考虑到“质”和“量”两个方面,而在评价快乐时,却认为只需考虑“量”这一个方面,这无疑是一种很荒谬的观点。
假如有人发问,我说的快乐在“质”的方面具有差异是什么意思,或者仅仅就快乐而言,除了“量”更大以外,究竟是什么让一种快乐比另一种快乐更加可贵,那么,我给出的回答可能只有一个。在两种快乐当中,假如所有或几乎所有体验过二者的人都明确地偏好其中的一种,而不管他们是否觉得自己有道德义务去偏好它,那么,它就是更值得我们去追求的那种快乐。假如那些对两种快乐都相当熟悉的人认为其中之一远远优于另一种,因而更喜欢它,就算知道它会带来更多的不满足感也不改初衷,并且不会由于天性使得他们可以获得无论多大“量”的另一种快乐而放弃前者,那我们就完全有理由认为,这是因为受到偏爱的那种快乐在“质”的方面具有一种远远超过了“量”的优势,以至于相对而言,“量”就变得无足轻重了。
然而,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那些同等地熟悉并且能够同等地重视和享受两种快乐的人,确实会极其显著地偏好那种能够运用其高等官能的生活方式。很少有人会因为他们可以尽情获得禽兽之乐,而愿意变成低等动物。没有哪个聪明人会甘当傻瓜,没有哪个受过教育的人会愿意变成不学无术之徒,没有哪个有感情和良知的人会自私和卑鄙,哪怕有人说服他们,让他们相信傻瓜、蠢材或卑鄙无耻之徒比他们更满意自己的命运。他们不会为了能全面地满足自己与傻瓜、蠢材或卑鄙无耻之徒共同拥有的一切欲求,而去放弃他们拥有的,但傻瓜、蠢材或卑鄙无耻之徒没有的东西。就算他们想这样做,那也只会是在极端不幸的情况下:为了逃避极度的不幸,他们会甘愿用自己的命运去跟其他几乎任何一种命运交换,无论后者在他们自己看来有多么不值得向往。相比于一个能力较低的人来说,能力较高者需要获得更多的东西才能感到快乐;他们也许能够承受更加剧烈的痛苦,自然也会在更多的方面受到痛苦的影响。不过,尽管具有这些倾向,能力较高的人也绝对不可能真的希望自己沉沦到被他视为低级存在的状态中去。对于这种不情愿,我们随便怎么解释都可以。我们可以将它归因于自尊;这个词,被人们不加分别地用于人类拥有的一些最可敬和最可鄙的情感上。我们可以把它称为对自由和人格独立的热爱;这种热爱的感染力,正是斯多葛学派有效地灌输他们的学说的手段之一。我们可以将它归因于对权力的热爱或对刺激的热爱,这两个方面,确实都参与和促成了这种不情愿。不过,最恰当的说法应该是一种尊严感,人人都拥有这样或那样的尊严感,它与人们的高级官能成某种比例(但绝对不是一种精确的比例),而在自尊心强的人身上,它还是幸福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因此除非是暂时性的,否则的话,与尊严相矛盾的任何东西都不可能成为他们的追求目标。不论是谁,如果认为这种偏爱是以牺牲幸福为代价——即在差不多相同的情况下,高等生物并不比低等生物更加幸福——那就是混淆了幸福与满足这两个大相径庭的概念。无可争辩的是,享乐能力低下的人充分满足这些享乐欲望的可能性也最大,而一个天赋禀异的人却往往会觉得,他能够追求的任何一种幸福都不完美,就像整个世界的构成一样。但是,如果幸福的种种不完美之处只要还让人能够忍受,那么他就可以学着去忍受;至于那种完全是因为根本感受不到这些不完美之处所带来的善,所以确实没有意识到它们的人,他可不会去羡慕。做一个不满足的人,胜过做一头满足的猪;宁可做一个不满足的苏格拉底,也不要做一个满足的傻瓜。如果傻瓜或猪猡对此存有异议,那是因为他们只了解这个问题涉及自己的一面。而这种对比中的另一方,却是对问题的两面都很了解。
I 导读
001 第一章 总论
009 第二章 什么是功利主义
041 第三章 论功利原则的终极约束力
054 第四章 论功利原则的证明
065 第五章 论正义与功利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