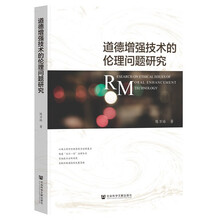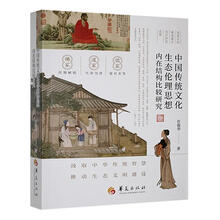《“纯粹恶的神话”之批判-(基于西方伦理学的视角)》:
受害者身份有时候是在恶行实施之前确立的。实际上的伤害尚未发生,而只是出于在记忆、预期乃至想象之中。但这些非现实因素的力量大得惊人,最终使得有些自认为是受害者的人主动发起攻击,从那个记忆中的、预期中的或想象中的受害者,摇身一变,成了现实中的施害者。考虑到冤冤相报的连环效应,每一个现实中的受害者,又反过来沉浸在过去受害的记忆之中,或者从过去和现实的状态作出未来仍会继续受害的预期,或者干脆在想象中加重这种受害的苦难形象,最终使得他们走上施害者的道路。对于受他们所害的一方来说,情况也是类似的。于是,所有的施害者都曾经是记忆中的、预期中的或想象中的受害者,同时又是现实中的施害者。时间的流逝并没有自然而然地弭平两方之间的怨恨或误会,而是使其陷入了一种积怨的陷阱之中,机会来到,新的伤害就会产生。
“受害者家属”这个说法是有条件的,并非所有的受害者都会让人想起其家属。在很大程度上,一个人不能选择自己的家庭和家属,他的家庭成员以及家属身份是被选择的——他作为一个家属总是某些人的家属,而这些人并不是他刻意选择要他们做自己家属的。家庭内部的恶,比如家庭暴力,家属本身就可能成为受害者。即便是家庭外部的恶,家属所扮演的角色在不同的文化和制度圈里有不同的表现。如果医疗、人身、财产等方面的社会保障制度健全,那么一个人在诸如疾病、车祸以及其他突发的灾难面前所受到的伤害或困难,对其家属的连累,在程度上要比那些相应的保障制度不健全甚至完全缺失的社会少得多。当然这种连累并不是纯粹的,因为家属也可能因为某个家庭成员的不幸——也是整个家庭的不幸——而获得物质上、社会上或精神上的种种补偿或抚恤。再者,在家庭责任感方面,不同的文化圈之间有一些微妙差别。家属的家庭责任感可以分担某个家庭成员之苦难,尽管并非任何苦难都能由家属共同承担,至少来自家属的心灵慰藉仍然是重要的,在宗教信仰慰藉相对比较淡化的家庭里尤其如此——对有些不信教并且无法享受健全的社会保障的家庭来说,家庭本身就是“天塌下来一起扛”的归宿,来自家人的支持鼓励就是他世俗意义上的“神佑”。
有些个体或群体给自己取“邪恶”的名字,主要为了渲染自己的力量。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成为强者,但我们又习惯于同情弱者而非强者的悲惨遭遇。强者的苦难故事往往能够起到正面的“励志”效果,仿佛只有弱者的苦难才是真正值得同情的悲惨境遇。受害者的形象与弱者联系在一起,一个强大的受害者意味着有足够的力量进行报复性惩罚,因此也不算是最值得同情的。同情应该给予那些遭受不公待遇却又无法为自己讨回公道的弱者。真正强大的人也不需要此类同情,他们可能鄙视弱者,认为这种被施舍的同情过于虚伪和残酷。所以你从强者身上看不出任何“纯粹恶的神话”,他们不相信这些神话,只相信自己的力量。当然他们也不是庸常之人,只有庸常之人才有庸常之恶。而在一个庸常的社会中,也轻易不能诞生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强者,相反,弱者才是主流:如果有必要,他们宁愿争相扮演那个“受害者”角色,也不愿或不敢做那个可能被视为“冷酷无情”的强者。
2010年4月,某地一个流浪汉被歹徒刺中,躺在血泊之中奄奄一息,起因是他刚刚对遭到行凶抢劫的女子见义勇为。曾有数十人从他身边走过,但几乎所有人都视若无睹,更无人施以援手。这件事情在网上曝光之后,人们为之震惊。但在心理学家看来,此类现象并不罕见,无非是为众所周知的“旁观者效应”增加了一个新的案例。心理学家们并不认为在突发事件中未能对陌生人出手相救的旁观者缺少某种个人品质,相反,影响他们选择的恰恰是身处群体之中这一外部条件。有研究表明,群体的规模越大,其中任何一个特定成员救人于危难之中的概率就越低。①这个“路人”群体具有典型的无结构、无组织特征,无结构的群体会引发一种责任分散(diffusion of responsibility):有其他旁观者在场会使我们不大可能去承担帮助的责任;如果群体中的每个人都被认为需要对私刑或其他的群体性行为负责,那么这种表面上“人人有责”的情况实际上就会成为“无人负责”。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