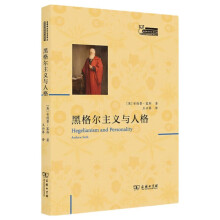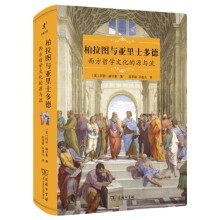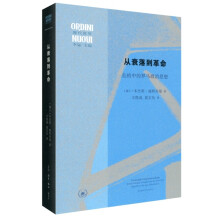《现象学导论七讲》:
这里让我们想到,“独白”如果要成为真正的独白,需要一些什么条件。关键还是我们应该怎么理解独白。独白只是胡塞尔讲的那个意义上,还是可能有一种更深意义上的独白?如何理解人的意识,这是这个问题再进一步的延伸。意识的本质从根本上是反思型的,还是说,意识的最根本的形态是非反思的?如果是非反思的话,那么自己对自己说话,说出真正的话来,自己跟自己下棋,就还是有可能的。当然下棋是一个更强的局面。但毕竟,如果一个人做某个事情时,可能并不在同时完全意识到他在做什么的话,那么实际上是留下了某种空间。以前讲到时间、空间有一种投射和保持,在这个“关注点”上应该是反思的。但即便这个关注点是被意识到的,毕竟在它不自觉地投射出的这种边缘意识和它不自觉地保持住的过去的边缘意识中,有一些是不被反思的,是以一种前反思的方式——或者叫下意识也好,叫边缘意识也好——据有它的。所以每个意识都有自己的非反思的边缘,而且按照某些说法,甚至可以说这种非反思的边缘恰恰是走在反思的意识之前的。如果情况是这样的话,那就为有意义的独白留下了可能。如果你经过训练,能够以某种巧妙的方式出入这种非反思的边缘境域的话,那在某种意义上你是可以进行独白的。因为这个地方已经不只是一个反思意识在主导局面了,而是这个反思意识带有另外的一些情境,或者在它的边缘情境之中,它可以对自己并不完全透明。这样,其中可以出现某种距离,这就是对话距离,甚至是独白对话。自己跟自己能拉开一定距离,这样你才能跟自己“说”。用后来萨特的话来说就是,自己想骗自己不是完全不可能的,某种情况下确实能骗。“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成了真理”,某种意义上也有道理。它重复太多了,就进入到边缘域里头来了,进入到你的下意识里。意识形态的灌输最后能让你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你不自觉地就进入到它这个框架里来了。或者你自己对自己说,说到一定程度,最后居然自己跟自己说起来了,好像有两个我在这里互相争论。我记得小时候写作文,经常写成这种局面,我在说服我怎样怎样,另一个我又在怎么说服我。其实要进入到这个所谓思想斗争的境界是不容易的。而且这个思想斗争如果要进行得非常原发、非常原本,那样就更不容易,但毕竟还是有可能的。而且既然胡塞尔自己都认为意识结构是带有边缘境域的,在这个意义上,他对于独白的看法并没有充分地体现出他自己后来发展出的这个意向性的结构。这一点上我倒是觉得茨威格的小说,在某种意义上更有真实性。
但是你也可以反过来,又找到某种有利于胡塞尔的说法。如果这个意识对自己不透明的话,最后形成了这种对话,形成了两个分裂的我,最后这个人毕竟疯了。这说明,意识如果对自己不透明的话,它就不是一个正常的、健康的意识了。是不是这样?某种程度上是这样,但也不必然,所以这是一个问题。如果茨威格的小说所描写的是唯一的可能,一个人把自己分裂为两个自我以后,他必然走向精神的崩溃,那么胡塞尔的这个讲法还有一定道理。意识对自己是透明的,它发生不透明说明它出了毛病,在一种病态的边缘的情境中被逼得做那些逆情背理之事。但是我们也可以设想,假如这个人处在这个情况下,他的旁边忽然出现了一个好心人,来训练他,在适当的时候让他中止这个游戏,在适当的时候又让他再次进入。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