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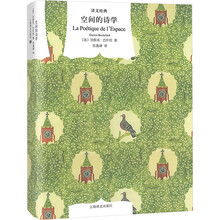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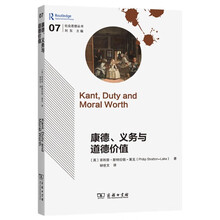







普罗提诺的影响力
普罗提诺在西方文化中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了阅读《九章集》的那些人的圈子。他的思想通过类似奥古斯丁和斐奇诺这样有影响力的媒介得以传播,从而确保了更为广泛的影响,它不仅影响了哲学史,还影响了宗教思想史、文学史,以及艺术史。神学家、作家和诗人在前文已经提及,并且在前文的章节(第九章第二节与第十章第二、三节)里还提到了普罗提诺思想对艺术理论、艺术活动以及神秘主义历史的重要性。
显然,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发生的诸多思想运动都以各种方式发掘了普罗提诺的思想。如果我们想要考察普罗提诺哲学在现代哲学反思背景下尤为有趣的某些方面,那么我们可以从本书前文部分已经讨论过的思想和理论中选择一些例子作为起始。以下的部分则不旨在做出全面的说明:它可以依据个人特定的兴趣和喜好来拓展和调整。
作为第一个例子,我要说的是普罗提诺思想中可知实在的内在化(参见前文第一章第六节)。在思考柏拉图主义的两个世界,即思考可感世界和可知世界时,普罗提诺引导我们去发现在灵魂和我们自身之中的可理知的存在。实在的基本结构和来源,须在我们的最内在本质中寻求。或者,正如普罗提诺可能更倾向于采用的措辞所说的那样(站在他们传统表达方式的立场上):世界就在灵魂之中,就像灵魂在理智之中而理智在太一之中一样。
这种关系有趣的一点是,普罗提诺在将这两个世界的区别(一开始)作为灵魂与身体的区别时,以极为清晰和严谨的方式阐述了灵魂与身体之间的区别(参见前文第一章)。在澄清这种差异时,他还对这两种实在之间如何相互联系进行了诸多讨论(参见前文第二章)。
而对于古代哲学很少讨论的领域,即人的主体性方面,普罗提诺也进行了讨论,有一定的创见。他提醒我们,在哲学探究中,不仅存在着被探究的对象,还有进行探究的人。我们想要了解世界,以便了解我们自身。普罗提诺首次引入一种关于自我的哲学,它包含多个层次,具有能动性,并根植于一种永久性的思想,这种思想因我们对外部之物的专注而成为无意识的(参见前文第十章)。当我们寻求洞察时,普罗提诺试图与我们的内在自身对话。他的话语具有一些直接的、个人性的亦即非正式的特质,这些特质具有普遍的吸引力:性别和文化差异(希腊人、外邦人)并不像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思想中那样重要。罗马帝国的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即由斯多亚学者倡导的宇宙公民身份,在普罗提诺那里变成了普遍超然的灵魂的姐妹情谊(参见IV. 3. 6. 10–14),我们所有人都从属于它。
在这里我们还可以加上普罗提诺对思想和语言局限性(参见前文第五章)的兴趣。他敏锐地意识到,对于人类所探究的某些实在而言,理性及其在语言之中的表达是如何受到限制的。与这种意识相匹配的,是对希腊语的开拓和完全个人化的使用,这突破了希腊语的限制,发明了新词,并在一些时候拓展出具有惊人的自由度的语法。
普罗提诺的某些学说以一种有趣的方式指向未来。从表面上看,他对世界的形而上学观点即灵魂组织世界似乎不可避免地过时了。然而,我们对世界的影响现在已经使得我们成为自然世界的组织者。我们正在成为普罗提诺式的灵魂:我们可以用智慧来管理事物,或是让自己受到无限制的、混沌的以及自我毁灭的欲望驱使。当然,普罗提诺不认为我们可以简单地发明一种可以成功引导生活的智慧:在他看来,我们必须从神圣理智之中获得智慧。然而,我们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即我们无法避免发展这种智慧的必要性,这是一种超越了性别、民族、种族和文化界限的智慧,并且在整体上与人类的本质相关。这种智慧并不会犯那种用一致性代替统一性的错误,也不像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观念那样只适用于本地区,而是将人性和一切本质视作一种多样性中的统一性,其中一个例子(但也许并不是理想的范例)是普罗提诺思想中的神圣理智在多样性中的统一。
普罗提诺的理智态度也是我们需要面对的一个挑战。他描述了他期望培养的一种哲学:“我们所追求的那种哲学……有淳朴、坦诚的特点,它的思路清晰而不混乱,它的风格庄重而不傲慢,它既充满自信和勇气,又富有理性,十分谨慎,小心翼翼。”(II. 9. 14. 37–43)普罗提诺的作品几乎都展现了这些品质。他表现出一种理智的严谨,即意识到了其自身的局限性,并不主张独断论,而是对事物有一种全面的视野,保持开放和灵活,以及对生命力的敏锐。
(李博涵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