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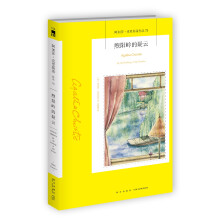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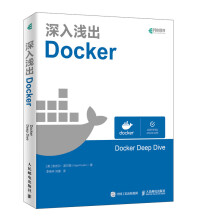






当大杉荣的自叙传在《改造》杂志连载、风靡东京的时候,年轻的诗人秋山清正在每天给内务大臣后藤新平家送报纸,后藤家的外孙鹤见俊辅刚刚出生不久,而大杉向后藤巧妙借取300日元的事迹已经传遍大街小巷,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毋庸置疑,大杉的人生经历深深影响了那一代人。
大杉荣一直都是人群中最闪耀的存在,从传播的政治思想到参与的社会运动,乃至其交游的友人与恋爱的对象,无一不引燃社会爆点。他刚愎任性,傲岸不逊,永远走在自由与反叛的第一线,活得轰轰烈烈,死亦得其所——在惨遭日本宪兵杀害后,志士为其复仇而实施了刺杀裕仁的“虎之门事件”。
大杉荣丝毫无惧将真实的自己袒露给大众,他以纪实体的文学笔法,将自己的人生不加掩饰的呈现——不良少年的青春回忆、勇于抗争的反叛精神、几次进出监狱的桀骜经历与荒唐离奇的多角恋情在文中一览无疑。美与真,只存在于乱调之中;大杉的自叙,永远鲜活。
六
我不知道这次处罚为何如此深刻地打击了我。我觉得这是我有生以来、恐怕也是绝后的一次重大打击,我真的非常后悔。三十天的禁足期,我几乎一直在默想中度过。我决心彻底改变之前的生活。
首先我戒了烟。然后,以前几乎一直是四处捣乱的休息时间,大半改成了在前院的植物园里度过。
学校的前院,一半是器械体操场,另一半是一个相当像样的植物园。有一个大的温室和一个小的温室。在两者之间,有一个我们称为“天文台”的设施矗立在中间。实际上在里面安装了诸如测量气温、气压、风力、降雨量等非常精巧的仪器和地震测量仪。
这只是一所上一些中学三四年级课程的初等学校,竟然有如此精密的设备,恐怕在此之前的其他地方都没有见到过。但是,这些设备似乎不是为学生所用的,而是为老师所用的。据说教博物和理化的老师,跟校长关系很好,在最初建造这所学校的时候,这位老师就设计了这个“天文台”。这位老师与一名年轻的助手,总是在超过这所学校级别的拥有先进设备的理化实验室和这所天文台里度过他们的时光,然而却从来没有教学生们如何使用这些设备。在我们离开这所学校之后,不知从哪里兴起了对这些设施的批评声音,结果这个天文台就卖给了师范学校和什么机构。
我在这座植物园里慢慢地行走,一边读着小小的白牌子上写着的这些植物的拉丁语学名和日文名,同时又不断地反思着自己此前的人生。
这一段深入的反省,不仅促使我痛改前非,而且将我引导到了另外的、其他的方向。
那就是,我究竟能不能忍受军人生活。听说在吉野事件发生以后,在军官会议上有人曾主张给我退学处分,后来由于接替北川大尉来到这里的同乡津田大尉和主管我们的吉田大尉的美言,我得以免于退学,实际上这时我已开始考虑,退学对我而言,是不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那些下士对我如同狗一般紧盯着地嗅闻,很多天来依然一直持续着,对我痛改前非的行为却是一点也没有察知。有时候,还能发现一点我的差错。我首先想到,我真的能够忍受这些下士对我的密切监视吗?我要认同他们是我的长官,我必须在他们的底下服从他们,我能做到吗?我对他们丝毫感觉不到尊敬和亲爱,却要服从他们的命令,这不是服从,而是盲从了。
当我意识到这是盲从以后,此前对那些军官和高年级学生的愤懑和不满,就不断地喷涌出来了。
我第一次想到了新发田的自由的空气。还想到自己小的时候,避开了学校的老师,避开了父母亲监视的目光,每天在练兵场玩耍的岁月。
我开始想要获得自由。
我这样的心情和想法,同时也被读书进一步地诱发出来。在学校里,除了学校发下来的教科书和参考书之外,严禁阅读其他的一切书籍。但是还是有各种各样的书籍被悄悄地带了进来。
有些人名已经记不清了,比如像大町桂月、盐井雨江这些当时国文科出身的新进文学士,还有像久保天随、国府犀东等汉文科出身的新进文学士,不断地发表模拟古文或是模拟汉文撰写的文章。我常常耽读于这些作品。
我在这里之所以举出盐井雨江这个人名,是因为在他的文章中,曾有一句:“人的花儿谢落的景色,真是有趣呀。”在当时我所读过的文章中至今仍然记得的,也就这一句了。到底有谁给了我怎样的影响,已经完全不记得了。
然而,在这些书里,恐怕流荡着一种幼稚却是自由的、奔放的浪漫主义情愫。
也许是受了这些读书的影响吧,我也从这个时候开始,尝试写一些类似拟古文的文章。这是进入三年级以后了,我写了一篇离宫拜观记,我记得一位名曰四宫宪章的汉文老师对此评论说:“不可谓不多才,文章不可谓不精巧,只是柔弱,军人不可作此文。”从我迄今还记得老师的具体评论这点来看,我对评论的前几句还是感到很得意的,而对后两句,心里还是感到很不满的吧。
二年级的时候,有一位国语老师,非常爱我的这个“才”。在某个下雪天的作文课上,他说,在这样的天气里进行练兵,既可说是“豪快”,也可说是什么什么,然后教了我们这什么什么的四字熟语。于是我就立即在作文中使用了这个熟语。
此后过了几天,我被学监叫了去,问我,你真的是这样想的吗?然后训斥我说,你若真的是这样想,也不可以这样写。后来我听说,国语老师也受到了训斥,说是不可教学生这样的词语。
我曾去国语老师的家里玩过一两次。老师对于这样的(此处删去七个字),老师因为是判任官,因而必须与曹长和军曹等一起吃饭,他对此不断地向我表示不满。
“你选择了一个好时机走了。我后来也被赶走了。你这边有什么合适的工作吗?”
此后大概过了五六年,蓦地在骏河台那里邂逅了老师,老师脸上现出了落寞的笑容,这样对我说。
那年夏天,我在训育(实科)上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十九点几分(满分是二十分),位列第一,专业课成绩十八点几分,第二名,操行的成绩是前所未有的十四点几分,倒数第一名,以平均成绩三十五六名的名次,变成了一个以前从没有过的阴郁的少年,回到了新发田。而且,这一阴郁,此后很长的一个时期里,一直伴随着我。
1 译者前言
3 最初的回忆
31 少年时代
53 不良少年
77 陆军幼年学校
105 新生活
127 母亲的回忆
157 狱中生活
203 叶山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