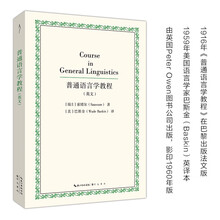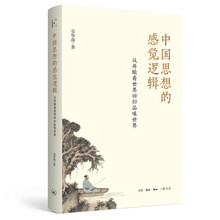作为青年黑格尔派最初成员的马克思、恩格斯都实实在在、认认真真地思考过这个问题。最早一次我认为是恩格斯1844年1月发表于《德法年鉴》上的《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文章中。恩格斯在这个文章中就讲到卡莱尔,我们知道卡莱尔是历史唯物主义英雄史观的代表人物,是辜鸿铭先生的老师,辜鸿铭先生在爱丁堡大学读硕士学位,他的导师就是卡莱尔。卡莱尔这些话跟辜鸿铭先生的观点非常接近:人们不再相信上帝了,社会失去了灵魂,开始出现精神危机,人们陷入利欲熏心、贪得无厌的地步,社会越来越世俗化。怎么办?卡莱尔对此非常担忧,希望找到一个新神,新的崇高和神圣的东西作为替代对象来补充上。原来基督教的上帝死后,在基督教上帝死后的位置上给他找一个替代品,这个替代品是劳动。
恩格斯就开始嘲笑卡莱尔,说上帝死了才导致人们没有灵魂、陷入空虚,这不但太肤浅,而且把问题说反了。卡莱尔在德国待过几年,没有学到德国哲学的精髓,只学了一点德国文学的皮毛。不是上帝死了之后才空虚,而是上帝一开始诞生就意味着空虚。因为按照青年黑格尔派的自我意识哲学,上帝是一个幻觉,象征着虚幻妄念。比如,费尔巴哈就说,上帝就是人的类本质的理想化表达。认识到上帝的本质是人,不信上帝了就是摆脱了妄念。恩格斯写这篇文章几个月之后才诞生尼采,更是接着费尔巴哈说道,上帝是最无能的人、一事无成的人所想象出来的一个幻觉,借助这个幻觉让上帝替自己来做自己做不到的事。所以,上帝之死就是人勇敢、成熟、壮大的象征。这是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讲到上帝之死。
马克思、恩格斯第二次思考上帝之死问题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我们知道《德意志意识形态》这本书2/3的篇幅是用来批评施蒂纳的,只有一小部分是批评费尔巴哈的。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批评费尔巴哈是批判施蒂纳的一个副产品。因为施蒂纳先是在他的1843年年底,1844年年初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中,首先批评了当时如日中天的费尔巴哈,而马克思、恩格斯当时还非常崇敬费尔巴哈。费尔巴哈一度是青年黑格尔派的领军人物,现在施蒂纳超过了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要超过施蒂纳,必须首先越过费尔巴哈。施蒂纳自以为在青年黑格尔派批判基督教杀死上帝的比赛中得了冠军,根据布朗的说法,马克思也大体接受。“斯蒂纳(Stirner)被描述为在这种发展的过程中走出最后一步的人,无论如何,马克思是这样理解的。”但这样说的前提是青年黑格尔派成员不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出版后,青年黑格尔派成员们都竞相写文章批评施蒂纳,可是写不出什么像样的文章,他们的文章最多十几页,多数不超过十页,施蒂纳看了以后大部分都不予理睬,因为没什么新意,这更增加了施蒂纳关于这帮家伙被我收拾掉了的自信。只是他没有想到,有两个年轻人在他的书的刺激之下,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提出了新的思想,写了一本《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书,超越了包括自己在内的青年黑格尔派。可惜《德意志意识形态》到1932年才出版,施蒂纳没有看到,所以他还是带着高度自信离开的这个世界,不曾知道自己很快就被超越了。
的确,按照施蒂纳的逻辑,费尔巴哈解构上帝就是把上帝视为人的本质的一个理想化,这样只是打发走了上帝,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人所固有的类本质,在施蒂纳看来仍然是一个带引号的、变相的“上帝”,虚幻的“神灵”。必须祛除一切神灵,才能告别上帝。在施蒂纳的逻辑里,人小时候把物质的东西当作一个偶像,拜物,人青少年时期崇拜一种精神偶像,这都是不成熟的表现。只有认识到物质偶像和精神偶像都不值得崇拜,世界上只有一种东西值得人敬拜,就是与众不同的自我(唯一者),人才成熟了。每个人降生到这个世界都是与众不同的,都有无限的奥秘,具有个性、唯一性,有无限奥秘,每个自我的发现和实现是每个人唯一值得认真对待的事情。这才算真正杀死上帝了。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