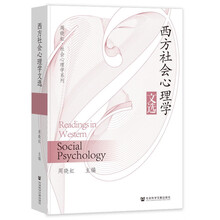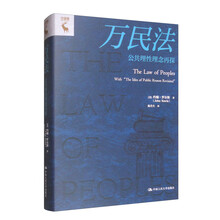《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第二版)/文化和传播译丛》:
这并不必然导致神圣性的终结;事实上,正如我所论证的,在消费文化中,神圣性可在有组织的宗教之外自我维持。然而,如果追随某些后现代理论家的看法,就会有威胁神圣性的趋势。例如,鲍德里亚(Baudrillard 1983a)提请人们注意在“电视就是世界”的社会里,信息、符号和图像的过载,这种过载是对我们将符号串联成叙事序列的能力的威胁。相反,我们从图像流的强烈表面体验中获得审美愉悦:我们并不寻求连贯持久的意义。那么,这将意味着象征的终结,因为符号可以承载消费文化的偶然和怪异的并置可以抛出的任何联想和意义的延伸。实际上,我们会走向文化的失序。但是,如果我们不管诸如“电视就是世界”这样的概念(最贴切的例子是“24小时不停地播放的单子式的MTV节目就是世界”),其中电视被设想为一种“会动的墙纸”,而关注看电视的实际行为,我们就会注意到公共和私人的崩溃。集体观看时尤为如此,观众远不是被动的,他们可能会积极地投入事件、场面和仪式的宗教性(religiosity)中,甚至可能盛装打扮,使观看本身也仪式化了(Dayan and Katz 1988: 162)。因此,一旦我们舍弃信息过载(信息的形式决定了信息的内容和接收)这样的概念,转而考虑具体的人的主动观看,那么社会生活的象征性和神圣性维度就可以得到维持。事实上,文化再生产的实践方面要求人们力图使符号稳定下来,成为具有实践一致性和象征维度的分类图式,而不像我所强调的那样,寻求逻辑和理性的一致性和合理性,这对符号专家的实践来说更为核心。
最后的问题是,消费文化和后现代主义如何与全球秩序相联系。通常认为,全球规模的消费文化,与美国控制世界经济秩序的力量的扩张相平行(Mattelart 1979)。在此,消费文化被认为注定要成为一种普遍的文化,它破坏了每个国家自己的民族文化。然而,对电视收视影响所作的研究,却强调国家差异在读取和解译信息时的重要性。实际上,电视节目中嵌入的信息只对被社会化的接受这些符码的人有意义,因此不同民族、不同社会阶层会通过不恰当的符码去观看国际流行电视节目。也可以说,我们在消费文化中提到的产生信息和符号过载的趋势,也会在内容层面上抵制任何一致的、整合的、普遍的、全球性信仰。然而,以前不为人知或只呈现为狭隘的刻板印象的“他者”和不同民族的图像的大量流行,可能会有效地帮助将他者和全球性环境的意识提上日程。
就后现代主义而言,由于失去了对支撑这种解释的元叙事的信心——在此可以想到萨义德关于东方主义的研究——“他者”不再有外来的或异域的刻板印象的感觉,使得从一个中心点或基础来解释不同文化或传统的权威产生了进一步的危机。这一危机正出现在整个社会科学的理论中,并与对全球情势的认知变化相联系。对他性、对从前被忽视或曾经感到威胁的不同文化的无序性的开放,本身就代表了国家间权力平衡的变化。寻求以他者自己的方式来了解他者,寻求窥视狭隘武断的刻板印象背后的东西,显示了文化方法论的解释学转向。这种迈向文化去分类化和长期维持的符号等级秩序的解构的运动,指向一个国家和文化之间相互依赖的环链被拉长和更密集交织的世界。例如在人类学中,后现代引发的对各种地方性知识体系的独特性和完整性的接受,已然跃上一个新的台阶,人类学研究对象不仅对人类学家的解释的权威性和有效性提出异议,而且寻求为自己发声。人类学家能讲述的只有他自己的体验(Friedman 1987)。这些变化发生在社会间层次,把学者和知识分子推向了多元文化主义的视角,而社会内层次的变化(部分我已经提到过)又加剧了这些变化,这一方面通过知识领域的通胀削弱了知识分子的权力,导致了更多的新知识分子的出现,以及占主导地位的知识分子定义符号等级秩序的权力的去垄断化;另一方面,消费者市场对新的文化中介入的符号产品的需求不断增加,以满足人们对新的文化体验和感觉的渴求。实际上,知识分子已降格为解释者的角色,对特殊性进行包装,无法提供有机会影响立法或实践的合法的普遍性知识(Bauman 1985)。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