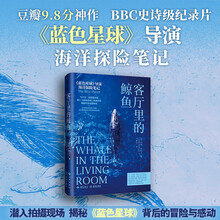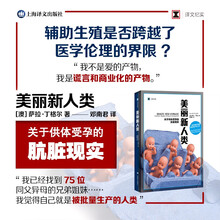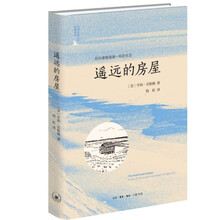这是个很老很老的故事:我有过一个朋友,我们分享一切,后来她死了,我们也分享了她的死亡。
一
我仍能看见她站在岸边,颈上围着毛巾,手里拿着锻炼后的那支烟——甜妞 和运动健将融为一体,她那划桨手的手臂与不知在何处找到的粉色泳衣,形成了一种颇具反抗意味的对比。那是1977年的夏天,卡罗琳和我决定交换运动:我给她上游泳课,她教我怎么划赛艇。这种安排解释了我为什么蜷在我最好朋友的赛艇里,看上去不像是划手,倒像是只喝醉了的蜘蛛,那艇最宽的地方也不过12英尺,窄得就跟针似的。我们在新罕布什尔州的乔克鲁阿湖,那是怀特山旁未受污染的1英里长水域。除了我们俩,只有我们的朋友汤姆目睹了我的此次壮举,他是跟我们一起来度假的。
“太棒了!”每次我徒劳无功地微微动一下,卡罗琳都会冲我喊。我紧紧捏住桨,攥得指节发白。卡罗琳37岁,已经有超过十年的划艇史;我差不多大她9岁,这辈子都在游泳。我发现自己具备抓住划桨要点的体力。可我多么想模仿卡罗琳,她的划桨动作精准得就像节拍器,我从未意识到光是坐在赛艇里,就如同要在漂浮的树叶上保持平衡那样不易。我怎么会让她说服我做这件事?
通常新手会在比卡罗琳的凡杜森号宽两倍也重两倍的船艇里学习。后来卡罗琳坦白说她等不及想看我翻船。但是当她站在水边,大声地冲我指挥,却带着一种不容辩驳的热情,充满了鼓励之意。我的成功稍纵即逝,她不如干脆用秒表计时。船桨是我仅有的支撑,我开始向水面倾斜,最后左摇右晃地维持在一个60度角的位置,这并非因为我有任何平衡感,而是因为我已经僵了。汤姆在码头捧腹大笑,我斜得越厉害,他笑得越大声。
“我要翻下去了!”我哭喊道。
“不,你不会的。”卡罗琳说,就像是输了比赛的教练般毫无笑意,“不,你不会的。把手放在一起,别动——不要看水,看着你的手。现在看着我。”她的话带来足够的慰藉和指引,我总算摆正了艇身。在跳出船艇扑向湖水之前,我好歹在平静的水面上划了五六下。几秒钟后,等我从水里出来,卡罗琳站在十码开外放声大笑,欣喜若狂地瞥了我一眼。
我们仨是8月去的乔克鲁阿。此前,汤姆登了一则夏季求租的广告:“三位作家带着狗,寻找靠近水和徒步小径的房子。”他的搜寻结果是一栋摇摇欲坠的19世纪农舍,往后几年,我们还会回来住。那地方被延绵起伏的草地环绕,拥有一切我们渴望的东西:宽敞空旷的房间里铺着带衬芯的老式床罩,还有手纺车;为野营者准备的厨房,外加一个巨大的石壁炉;透过高高的窗子可以眺望怀特山。几百码外就是湖。早上,有时是夜晚,卡罗琳和我会走到湖边,留下狗狗们透过前窗远望。她从湖的一头划向另一头,而我绕湖游泳。我是水獭,她是蜻蜓。我偶尔停下来,欣赏她的翱翔,来来回回足有六英里。有时她把船艇靠向湿地,仔细观察我在水中的翻转。那时我们已经做了两年朋友,我俩有种属于姐妹或青春少女间的好胜心——我们都希望拥有对方的过人技艺。
那里的黄金色调和它施予我们的单纯时光——河边漫步、野花、大黄派——都高于卡罗琳的期待:她觉得大多数度假都是不情不愿地到镇子外去。我只是稍具冒险精神,希望自己能像空降般开始夏日旅行,不用为狗或购买40磅食物而焦躁不安。卡罗琳和我都是独居的作家,我们都在一件事上难以妥协,那就是打乱常规:在剑桥的日常散步,我们共享或对比的锻炼方案,饮食、电话以及被称为“我们的小日子”的独立工作时间。“对巴黎的评价言过其实。”卡罗琳喜欢这样断言,有一部分原因是为了逗我发笑。一天夜里,她遇见我的一个朋友,他熟悉她的书,问她是不是大部分时间都在纽约度过。“开什么玩笑?”她说,“我甚至都没去过萨默维尔 。”我们依赖这种神圣不可侵犯的熟稔,离开镇子只是为了把旅行从清单上勾去,然后回到日常的喜怒哀愁中来。
我有一张照片,记录下了在乔克鲁阿的某个夏天。照片里的主角是我们俩的狗克莱门蒂娜和露西尔,她们在窗旁的椅子上望着户外,光线映衬出她们的轮廓。这是一幅经典的狗照片,捕捉到了那种警惕又不失忠诚的感觉:两条紧挨着的尾巴、两个尽忠职守的动物。过了好些年我才发现,在照片的中景里,透过窗子望向外面的田野,能辨认出两个微乎其微的人影——那是正从小山上下来的卡罗琳和我。我们一定是要去湖边,而那两条狗熟悉我们每日的路线,早已按时上岗。卡罗琳的摄影师男友莫雷利觉察到了这幅画面的美好,抓起了相机。
她死后一年,我看到了这张照片,它就像是画作里暗藏的线索——一座消失之后才会被发现的神秘花园。乔克鲁阿散发着恬静的光辉:我记得有天夜里,卡罗琳跟汤姆掰手腕差点就赢了他;那只把我赶上餐桌,惹得她在一旁大笑的耗子;我们设立的“最牛野营者”奖项(她总是赢)。我不愿再想起那些蚊子,那天卡罗琳生气了,因为我把她留在一艘移动缓慢的独木舟上,她独自划向雾中。如同大多数记忆都会被最后的章节涂上色彩,我的记忆真切地携带着伤痛的重量。关于悲伤,人们从未告诉过你,思念一个人是其中最简单的部分。
第一个夏天过后的五年里,我们一起划艇,并驾齐驱。我们都住得离查尔斯河不远。那是一片如迷宫般错综复杂的水域,蜿蜒九英里穿绕波士顿,从牛顿北边经过剑桥直到波士顿港,河道曲折迂回,水面平静无澜,是划桨手的圣地。卡罗琳身材矮小,却能压得住超过她体重的分量,我管她叫“野蛮妞”或“小野兽”。我们从相隔几英里远的船库把赛艇划出,我能在几百码外辨认出卡罗琳的划艇动作。我会在埃利奥特桥或哈佛边上的威克斯行人桥附近等她,准备连珠炮似的向她发问,关于体形、速度,还有把大拇指搁在哪儿。要是比我早出门几小时,她一回家就会火速发出没有标点的电子邮件:“水面平静快点出来。”从4月到11月,我们时而一起时而单独地划过了上百英里。在最初那两个夏季,她忍受着我关于划艇技术的电话轰炸。“我想谈谈推力。”我用几乎疯狂的紧张语气说。要不就是:“你知道人的脑袋有13磅重吗?”“嗯……哼……”她回答道。很快我就听见背景里传来一阵轻柔的咔嗒声——她又开始玩电脑纸牌游戏了,这相当于她在电话里打了个哈欠。一天临近结束时,我们一起遛狗,比较手掌和手指上的老茧(出色的划手历经战斗后的伤疤),就像两个小姑娘在比较晒后的肤色或是那种带着小吊坠的手链。过去和未来,她都是更好的划手,所以我接受她的自鸣得意,发誓在游泳池里还以颜色。某年圣诞节,我送给她一张20世纪40年代的照片:两个女划手在英国牛津划着双人赛艇。她把照片挂在床边的墙上,在一条镶框横幅的上方,横幅上写着:“热忱是有用的火种。”
这两样东西如今都挂在我的卧室里,挨着那幅狗照片。卡罗琳死于2002年6月初,那时她42岁,七周前确诊为四期肺癌。入院后的最初几周,她试图写下遗嘱。她说她想让我接手她的赛艇,就是那艘我用来学划艇的老凡杜森号,这么些年来,她就像对待心爱的马一样悉心照料它。她说这些时,我正坐在她的病床上,那是最初关于死亡的一次谈话——你知道即将发生什么,竭尽全力想杀出一条路。我告诉她我会接手那艘赛艇,但我必须遵循划手的传统,把她的名字刷在船头,也就是“卡罗琳·纳普”。“没门。”她说,眼中闪过与那天教我划艇时一样的光芒,“你得叫它‘野蛮妞’。”
***
悲伤宛如光谱,甚至能改变树木的色彩,在接触它之前,有一种盲目胆大的错误假设,也许会让我们跌跌撞撞地度过时日。人们总是认为,演出永远不会结束,或者说当那种失去真的降临,它会指向路的尽头,而不是中途。卡罗琳死时,我51岁。到了生命的这个阶段,参加过的葬礼已经足以让你熟谙《传道书》中的诗节。但得知卡罗琳生病的那天——医生用了些令人窒息的字眼,像是“我们会减轻她的痛苦”——我记得自己走在路上,4月里明亮的街道闪耀着生命的光彩,我因震惊而变得不谙世事,大声地自言自语:“你真的以为你能躲过去,不是吗?”
我是说也许我能逃脱那种残酷的、令人难以忍受的失去,它并不像吸毒、自杀、年老那样带着某种刻意或自然的退场标志。那些事我全都遇见过,总是有类似的悲剧媒介(要是他服用了锂就好了 ,要是他没有走私可卡因就好了),或某种无奈的接受(她活得挺长了)。但是没有一个我爱的人——我数遍了生命中必不可少的支柱——突然逝去,那么年轻,心中满是不愿离去的决心。没有人拿到过可怕的化验报告,掉头发,被告知安排好自己的后事。更重要的,不是卡罗琳,不是我最好的朋友、我的小妹妹。多年来她一直跟我开玩笑说再过几十年,等我老弱得没法烧饭,她会给我送汤喝。
从一开始,我们之间就有种无法言喻甚至玄妙的东西存在。不认识我们的人会误以为我们是姐妹或爱人,有时朋友们也会叫混我们的名字。卡罗琳死后一年,在我们曾经一起散步的水库鲜水湖,一个共同的朋友冲着我脱口而出“卡罗琳!”,接着她为了自己的口误泪流满面。友谊宣布了它的深厚,因为那些显而易见的情感,也因为我们或隐或显的相似之处。我们的生活在两条相呼应的轨迹上交错,这是最初的联系。找到卡罗琳就像刊登了一则个人广告——寻找只存在于幻想中的朋友,然后她出现在你家门口,却比你期望的更有趣、更精彩。分开时,我们各自都是惶恐的酒鬼、心怀抱负的作家、爱狗人士;一起时,我们便成了一个小小的集体。
我们有许多梦想,有的很可笑,都是那些打算享受奢侈时光的人共享的私密代码。其中一个是我们打算在西马萨诸塞州开编织中心,里面养着边境牧羊犬和威尔士柯基犬,因为我们那时都太老了,养不动体型巨大或不守规矩的家伙。我们坚信,边牧会训练柯基,而后者会变成我们希望的那种口袋狗。编织的念头源于我们没完没了的谈话中的一次,有关我们是否正确地活着——此类周而复始的对话涉及的主题从严肃的(写作、独处、孤单)到平凡的(虚度的光阴、都市生活的愚蠢、垃圾电视节目),不一而足。有一天,卡罗琳问我是否觉得她在重播剧《法律与秩序》上花了太多时间。“哦,别担心。”我对她说,“想想吧,如果我们活在200年前,就会玩玩纸牌或搞搞编织,而不是看电视,我们也会为那些担心。”长长的停顿。“什么是编织?”她胆怯地问,就好像那种古老的织花边手艺有什么了不得的。“编织”由此进入了私人词典,成了我们(也许还有别人)蹉跎岁月的暗语。
这一切犹如旧物堆里埋藏着的标记,在她死后,突然间被一阵痛苦的疾风卷挟着向我涌来:我尝试向认识我们的人解释编织中心是怎么回事,随即意识到那听上去多么可笑,这让我崩溃。当然,没人能真正理解编织中心,如同所有亲密关系的代码一样,它拒绝被翻译。而它之所以那么有趣,主要是因为它只属于我们俩。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