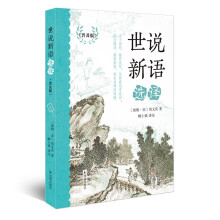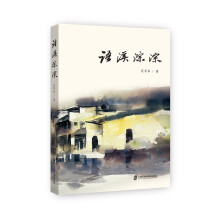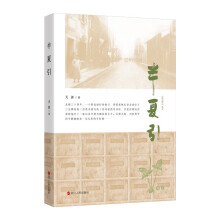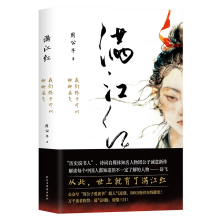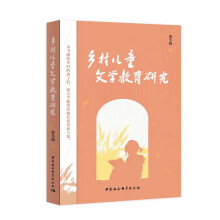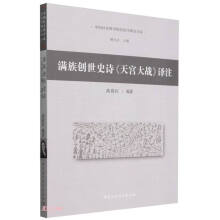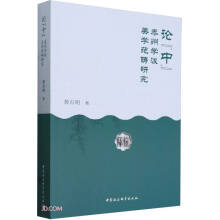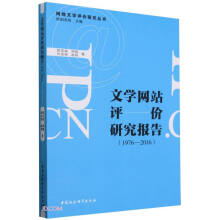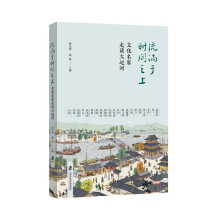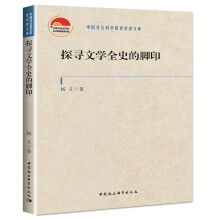《中国古代海洋文学史》:
在文学上,唐代的传奇小说具有巨大的文本进步意义。“中国小说,由于(唐)传奇的出现,终于脱离对史传的依附,获得了文体的独立。”所以唐代的涉海叙事,也带有了一种传奇的色彩。虽然与唐宋传奇话本小说中主要是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传奇不一样,但它们也呈现出一定的“海洋传奇”的特点。
这种“海洋传奇”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航海传奇”的初步书写。段成式《酉阳杂俎》描述的航行至新罗的两则叙事,就体现了这一点。虽然与西方海洋小说的“航海传奇”叙事相比,段成式的叙述重点并非“航海”本身,而是船员在海难后漂流至岛上后的遭遇。这似乎与西方海洋文学的航海叙事形成了鲜明的差异。美国学者玛格丽特·科恩在其著作《小说与海洋》中,专列有“航海异事与小说”一章。她写道:“现代小说之父丹尼尔·笛福熟知各类海洋书籍。他的私人图书馆藏有49卷航海旅行文学作品。他的写作也一直受到这类作品的启发。在《暴风雨:海陆暴风雨中的惊险异事与灾难集》(1704)一书中,笛福展示了海陆灾难中的天意难违,这让人想起詹姆士·简韦在《致友人》(1674)-书中加尔文主义式的船难描述。1725年笛福创作的想象小说就直接盗用了丹皮尔的纪实名作《新环球游记》的书名,只不过加了一个副标题‘沿着一条从未开发过的航线’。”在笛福等西方海洋小说作家中,航海、航线本身就是叙事的主体,而段成式等中国作家则把它当作一种叙事的缘起和背景,叙事的核心内容在于上岛后的种种奇异遭遇和经历,但它们毕竟也是一种中国式的“航海传奇”书写。
第二是对传奇性海洋生物的文学构建。海洋生物的传奇性源自于《山海经》。《山海经》中的大鱼、大蟹记叙并非纪实性的,而是夸张和变形的,这就为海洋生物的传奇性书写奠定了母题基础。汉魏时期的海洋文学中也有许多海洋生物的记叙,但是到了唐代,这种海洋生物题材成了海洋传奇书写的热门话题。戴孚《广异记》中就有神奇的《南海大鱼》和《南海大蟹》。段成式《酉阳杂俎》中虽然不乏《鲛鱼》《鲎》这样比较客观的海洋生物记载,但更多的是“秦皇鱼”“印鱼”和“海术”之类的志怪传奇性海洋生物勾勒。而杜光庭《录异记》中“南海中有山,高数千尺,两山相去十余里,有巨鱼相斗,髻鬣挂山,半山为之摧折”这样的描述,则更具传奇色彩了。唐人海洋传奇小说,除了传承自《山海经》外,也与距离它不远的汉魏志怪小说文学传统有关,所以它的“海洋传奇”很多时候具有志怪的意味。这在海洋生物的书写中显得尤为突出。
唐代海洋散文许多具有政治色彩。柳宗元《招海贾文》隐晦反映出朝廷上下对于海洋经济的矛盾态度,韩愈《南海神庙碑》也折射出朝廷对于面向海外的海洋国际贸易的某种态度,而陈子昂《禜海文》更是一种海洋军事行动的直接描述。
唐代的海洋赋文,意象瑰丽奇异,情感奋发向上,基本上都表达了对于海洋深厚的感情,作者们赋予海洋某些情感乃至政治和思想寄托,说明海洋已经成为唐朝赋家的重点抒情对象。
唐代的海洋诗歌,是古代海洋抒情文学高原之一。不但白居易、孟浩然、王维、李商隐等伟大诗人都有佳作,而且连唐太宗李世民也以一首《春日望海》,亲自参与了这个海洋大合唱。至于一般性的诗人,他们的海洋诗咏作品更是出现在初唐、盛唐、中唐和晚唐的整个时期。海洋诗风与唐朝国运也隐然相连。国运昌盛,海洋以蓬勃面貌入诗。局势动荡艰难,诗人们又纷纷想起精卫填海的故事,对精卫的坚毅和顽强赋予极高的评价。
总的来看,唐代的海洋政策是开放的,对于海洋贸易是支持的,所以反映在海洋文学上,对于海洋还是正面歌颂的比较多。这在海洋抒情里体现得特别明显。唐代的海赋和海洋诗歌,大多慷慨激昂,抒发出对于海洋磅礴力量的由衷赞叹。这种海洋歌颂和赞美,与整个唐朝蓬勃向上的时代气势,是完全一致的。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