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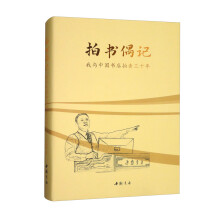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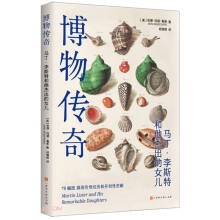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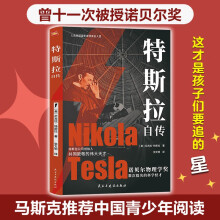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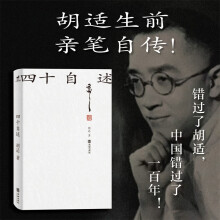
《药渣》:
护士小姐走进二〇五号病房。
橐,橐,橐,起先一阵步履声,接着我们眼前一亮——白色的她,一手挥着体温计,停在门前,似乎是惊奇地看了我们一转。
病房中,母亲坐在陪侍床上,祖母和四叔各坐在椅子上,弟弟和我站在一旁,正在相互细声闲谈(细声,为怕撞碎这儿的宁静),病床却是空空的。
那么——
“谁是病人呢?”她好像在问。
我走过去,她指着病床叫我躺下。正待躺下,她又止住了我,从床头掀起被单,——原来那不是被单,是用来盖的算是“单被”。
我脱了鞋,舒服地躺下了。呀,我没有料到就这么容易地入了笼。
体温计含在我嘴里,我再按着脉搏。
八月天气燥热。屋里倒还阴凉,这里有应有的和平清净,我的心却异样地怔忡。
一会儿,护士抽出体温计,迎着亮看。
“那,都好吗?”母亲关切地问。
“都正常。”她点点头,走出去。
母亲问我饿不饿,我要强地否认,肚子却虚得发慌,胃囊到食道像在压缩,直牵扯着使我咽下唾液,心脏像是因为没有食物垫住它,无主地忐忐忑忑,掌心沁出潮汗,浑身乏力。
从早起到现在二三点钟,记得只吃了两块饼干,还是母亲逼着我吃的,我不肯吃,分辩着那是性命“交关”的事。
“这孩子就是犟,”母亲数说着,“中饭叫他吃碗肉圆汤,他硬是怎么也不肯。”
我嚷着:“医生这么说的嘛!”
祖母说:“吃也要吃一点,挨到明天还有那么多的时候。”
四叔提议:“叫碗鸡汤吧,医院里有叫的。”
母亲问我要鸡汤不,又说:“不要把医生的话当圣旨,不要紧的。”
我赶紧摇头:“不!不!”求说:“让我就熬这一天,熬这一天,明天开好刀,多吃点好吧?”
我岔开话题:“像我这样的病人大概很少一一自己好好的走来,爬到床上来。”
“哎,”祖母说,“要不是你屁股上那么点累,不是和好好的人一样么!时好时坏的,闹到今朝,从这么点点大起,”祖母手下压着比划,“好了,把根除掉就好了,这回吃点小苦。菩萨保佑。”
房间里沉默下来,他们都看看我。
我看看眼前空白的天花板。过去的苦难,今日的焦虑,明天的希望和惊惶,零乱地、片段地争着涌出来,一时也分不出是什么感想,辨不出是什么滋味。剪不断,理也乱。
祖母和四叔要回去了,母亲也要回去洗澡。
祖母站起来:“你静着养息养息,没有事,闭上眼睛念念佛,念念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我随声响应。
四叔走到床前笑着向我说:“心里怕不怕?”看着他我笑笑,摇摇头。他问:“刘医生明早什么时候来?”“七点种,他说的。”“好,明天再来看你。”
“不要怕,也不要心急,”母亲安慰我。“这回好了,就好了,那随你怎么样子上天下地。一一留弟弟陪你。一一等会回来洗澡。一一过一会儿五姨母来。”
我静静地躺着,弟弟到走廊外四处去看看。
白色的床,白漆的家具,白得刺眼。墙壁则是不调和的暗黄色,整个房间呈狭长形,看得出是从一个大房间隔出来的。床东西向直置,物件向我两旁站开,右侧是药护柜、陪侍床、衣服及杂物橱;左边是在窗下的小方桌和两把木椅,以及在桌上的尚空着的小花瓶,和窗在同一个平面。在我脚那头的是通向几间病室共用的长凉台的门,这边门窗装绿的铁纱格,门一直过去,就是和衣橱在一线的另一扇门,通过它我躺着望得见外面冷冷的走廊和走廊边的楼梯口,我们从这门进出。
我这白色的床比普通的要高得多,钢丝弹簧软软的,非常适意,身子平整地浅浅陷下去,像睡在水面一样。盖了单被看起来我这人只有两个鼓起来的脚尖和一个头,如果人就是这样的倒很好玩。如果人没有躯体,人的病患大概只有脚气病和脑充血了,那么我睡在这里不是毫无意义了吗?我痴痴地想,眨眨眼睛,摇摇脚。只可惜“如果”非果,我不可能咬到丰满的肉食。
我静静地躺着。弟弟进来,他告诉我他看到了医院里手术室,那是很精致的一间,光洁的地板、门、墙,上下四处真的一尘不染。(干净得一尘也染不上?)手术台在正中,其上垂下一只大灯,此外是一些奇形怪状的医疗器械。那儿是医生和病魔的竞技场,多少人的生命在那儿被争夺,啊,明天,明天我也要去听候决断了!
如果说走进医院就是来到了生命的边缘,那边缘的边缘就是医院的手术室了。
还想下来走走,谁知鞋已被拿走了,只得静静地躺着。
进这医院我来过三次。头一次的时候,天,就似乎预兆不祥,大雨,街上水漫得没膝,满心仓惶地乘着黄包车去,被回说没空房间,再转回头。碰了壁,倒是碰开了心结,舒坦宽敞了。
……
自序
一、笼
二、前尘
三、生命的边缘
四、凯歌
五、阴影
六、暗潮
七、丕变
八、再受刀创
九.四面楚歌
十、曲折
十一、四叔死了
十二、“使徒”误我
十三、在病魔的牢狱中
十四、苦苦挣扎
十五、祖父逝世
十六、艰难的彳亍
十七、又一阵逆浪
十八、山穷水尽
十九、绝处逢生
二〇、余音袅袅
二一、不尽欲言
跋
附录